跨国文化交流总是乐于去发现对方的特异之处。在东、西方新的二元对立关系中,作为东方的中国似乎还是要扮演他者的特殊形象,才会引人,才会因为特殊而具有存在的理由和价值。作为强势文化的西方艺术在我们打开国门之后,已呈长驱直入的难遏之势,并在中国本土寻找到相对程度的认同与接受,中国已变为一种后现代文化生产的资源,一种与西方文化相异的代码,并将会成为大规模文化生产与消费的一部分。因此,中国当代艺术从总的状态与趋向上考察,仍处在那种西方式的被动的观看之中,处在一种“俯视”或“低视”的被选择之中。尽管中国当代艺术在西方频繁亮相,但其主办者及策划者由于在意识形态上的惯性和偏见,很难达到在相似与差异中我们与西方之间的真正沟通和平等的对话关系。由此导致了中国当代艺术家殚思竭虑地揣摸西方人的心理,塑造并展示所谓的“当代中国艺术的形象”。虽然中国当代本土的艺术家在自己的现时的地域空间中难以充分地展示,有其众所周知的原因,但也不可否认西方的“选妃”方式也是造成“中国当代艺术形象”符号变异的一种因素。鉴于此,策划并于1998年伊始举办的“生存痕迹”展览,其初衷就是希望中国的当代艺术在其居住地及生存空间进行“生存痕迹”的呈现与播散,在“仰视”的疲惫和惶恐中得到化解,生成确认出一种自为的、独立的、稳定的中国当代艺术形态。 以“生存痕迹”作为学术主题,主要考虑两方面的问题。其一,人的生存留下无数的痕迹,它们漫无边际地弥散于生存空间。从某种纯粹的意义上来说,艺术的生存方式就是人的精神痕迹的存在方式,时代性给予艺术以印痕。从艺术家的生存与创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各自的痕迹。痕迹的产生、装置、覆盖、遮蔽等等,表现的不是一种技艺,它导致的是一种艺术观念和艺术精神的呈现。一位严格意义上的艺术家正是通过其生存的痕迹、作品中的痕迹来进行人文关怀的探寻者。痕迹是相互指涉、相互映照的,痕迹的意义是从一些痕迹到另一些痕迹的转化与播散的过程中得到表达,其所能够表达的意义也就有了多种可能性。其二,“生存痕迹”是一个比较宽泛的名词,个人以往的生活经历、生活经验、与现实环境的关系,以及由此而萌生的趋势性文化潮流均可以概括其中。痕迹的多种可能性表达也为艺术家创作提供了多种选择的通道。作为策划人我们不愿将参展艺术家限定在一个狭隘的思路中,以避免他们的表达受到某种抑制或约束。 在对艺术家的选择上,我们邀请了90年代以来利用各种媒介进行实验的,比较活跃也相对成熟的11位艺术家参展。虽然由于经费的原因,在选择的范围上主要集中在北京地区,但他们仍具有一定代表性。即坚持对艺术的笃诚与敏锐,坚持创作中的文化意义、社会意义、艺术品格与利用多种媒介表达语言上的同步推进,并在中国当代艺术的转化过程中显示出较强的悟性能力和创造活力。他们在观念指向和语言方式上差异较大,但偏重于以观念切入日常生活,通过发现、置疑、阐述的不同立场和工作方式,一方面显示中国当代实验性艺术的多元与综合的特征,构成了其现存状态的一个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在充分体现每位艺术家个人取向和风格的前提下,通过观念和语言的不同去提示深层的、隐蔽的文化统一性与相对性,并为今后的交流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平等的对话语境。 由于中国当代实验性艺术在中国官方性的展览组织系统中,缺乏应有的位置,难以公开和相对不受限制地进行全面展示。因此,在展览场地的安排上,我们选择了地处北京东郊的一所私人的工厂车间和库房作为展览场地。试图将这一非正式的、非公开的场地有机地转化为实验艺术创作与展示的空间。通过城市与乡村的结合部,从地理概念的都市转移到乡村,从文化概念的中心转移至边缘。这既是中国当代实验艺术生存环境和现有状态的真实写照,又是对中国当代实验艺术家“就地创作”工作方式的某种认同与利用。而这种转移或转化也恰恰对应了中国当代社会可持续性发展及人们观念上处在一种急剧转型的变化状态——多种经济成份的共存及其造成不同生活方式的并列,导致的中国社会价值标准和价值取向的多样化。场地的有限选择和利用,使参展艺术家的创作与周边地理的、人文的环境形成转化并达到相对协调、默契的对话关系,即游离于中心的城市之外,以边缘化的立场进行本土性的“就地创作”。 立足于原生态的文化关注,是这次展览作品总的创作倾向,所呈现的创作姿态是融入了艺术家对自我生存体验和状态的叙述,是艺术家经过对现实社会的某一层面的亲身体验和主观介入,并利用行为与装置的方式所创造的一种事实与虚构相结合的综合景观,这既表现出了90年代中国社会经济和文化变迁所导致的生存与情感的当下状态,又是对“生存痕迹”这一学术主题的个人理解、认知和回应。 宋冬利用原工厂的职工食堂作为其作品的展示空间,将2500余斤大白菜,渍了12缸酸菜——以往北方人在冬季的主要食物,并在墙面上绘记了渍酸菜的传统方法、过程和食用的图解及文字说明。食堂的窗内架放着一台录相机和电视机,播放着宋冬渍酸菜的行为过程。开幕时,他又亲手烹制几锅酸菜白肉,供观者品尝。大白菜在北方人的生活中,尤其是在作为北京人的宋冬的心目中,有着特别的意味:它是中国计划经济和农业政策的直接产物。也许北京人不会忘记,几年前社会上将认购大白菜视为是一种爱国行为。如今大白菜的产销已经“平静到位”,但它在百姓日常生活和个人成长的经历中,随着时代的变迁打上了不同的烙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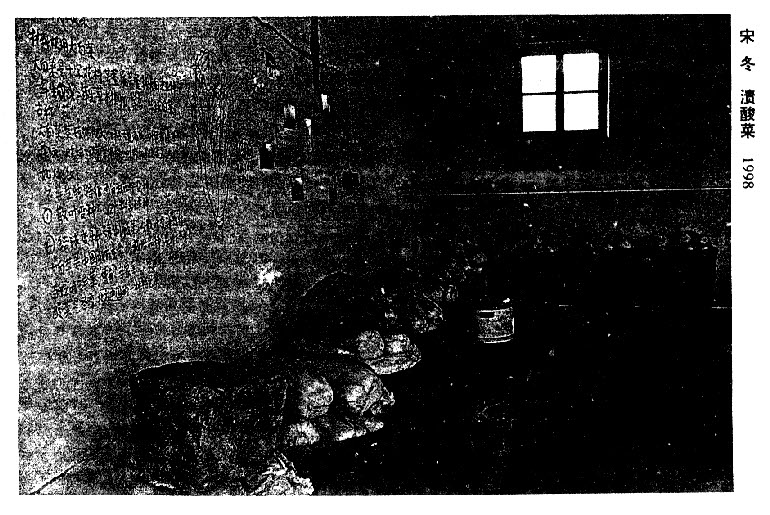
在展厅里,展望真实地模拟了一间学院式雕塑教学的车间,几十尊大大小小的石膏像摆放其中。这些令人熟悉的石膏模特儿,不禁使人联想起中国美术教育中的记忆片断。而观众在“只需5 分钟让你享受大师的荣耀,创造大师的作品”的感召与诱感下,通过实际的操作与介入,不仅抹平了观众与艺术家之间的界限,而且使这件题为《新艺术速成车间》的作品,与被接受被纳入的观众之间有了无限扩展的可能。或许真正的在场并不存在,波普式的解构主流艺术才是永恒的目的。而这种解构的结果,似乎又总是笼罩在西方文化参照系的语境中,苦苦挣扎而又在劫难逃。同样是虚置现实,蔡青的《耕种》依照原始自然的耕种方式,以极为认真投入的姿态,颇为荒诞地将几百枚钱币,播散在被犁开的土地之上,“种子”物化为金钱,种植、生长的形态转化为人对金钱的贪婪的“本相”。他所热衷表现的其实就是当今社会中人人都在为之垂涎、奋斗的欲望。看似荒诞不经的行为恰恰是当下生存状态的现实表达。与耕种收获有关的还有汪建伟的作品《膜》,他于1993年10月在川西平原实施了为期一年的《循环——种植》的工作,作为这一实验性作品的逻辑延续,他将收获的麦粒,用乳胶粘贴在接送观看这次展览的交通工具——中巴汽车的两侧玻璃上。当观者穿过城市,从农业部门口搭乘这辆带有汪建伟作品“痕迹”的中巴时,事实上就已经构成“循环——种植”的一部分。半透明的车窗,使观者对未知事物的要求有了一种虚幻的心理补偿,化解了太多的神秘感所造成的尴尬。由于在场的模糊和不可企及,人们只能在能指的扩散与延迟中寻找一时的意义与满足。这一方面从某种角度透视出中国当代艺术的现实处境;另一方面亦将实验的范围由知识结构拓展到社会环境、规划、行为等更为开放的空间。在汪建伟的作品由城市到乡村的线性穿行和展露的过程中,张德峰也利用城市与展览场地的路线,将从农业部至姚家园村北展览场地的6.4 公里路线分割成11个路段,标出米数的标版立于路旁。当观者沿着这一路线前来参观这个展览时,就已经构成了张德峰这个关于《距离》的作品的一部分,也就成为了城市与乡村,中心与边缘的一种“存在距离”,由此可以阐发出一种人文主义的忧虑——城市和乡村的距离以及这种距离感的即将消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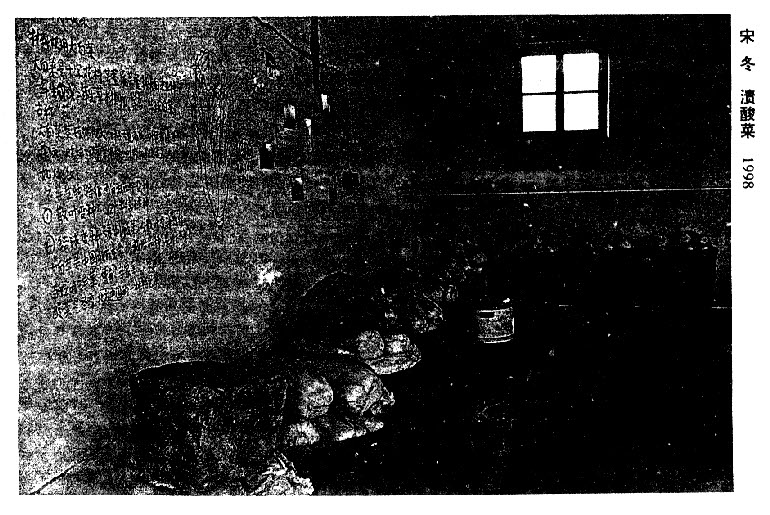 在展厅里,展望真实地模拟了一间学院式雕塑教学的车间,几十尊大大小小的石膏像摆放其中。这些令人熟悉的石膏模特儿,不禁使人联想起中国美术教育中的记忆片断。而观众在“只需5 分钟让你享受大师的荣耀,创造大师的作品”的感召与诱感下,通过实际的操作与介入,不仅抹平了观众与艺术家之间的界限,而且使这件题为《新艺术速成车间》的作品,与被接受被纳入的观众之间有了无限扩展的可能。或许真正的在场并不存在,波普式的解构主流艺术才是永恒的目的。而这种解构的结果,似乎又总是笼罩在西方文化参照系的语境中,苦苦挣扎而又在劫难逃。同样是虚置现实,蔡青的《耕种》依照原始自然的耕种方式,以极为认真投入的姿态,颇为荒诞地将几百枚钱币,播散在被犁开的土地之上,“种子”物化为金钱,种植、生长的形态转化为人对金钱的贪婪的“本相”。他所热衷表现的其实就是当今社会中人人都在为之垂涎、奋斗的欲望。看似荒诞不经的行为恰恰是当下生存状态的现实表达。与耕种收获有关的还有汪建伟的作品《膜》,他于1993年10月在川西平原实施了为期一年的《循环——种植》的工作,作为这一实验性作品的逻辑延续,他将收获的麦粒,用乳胶粘贴在接送观看这次展览的交通工具——中巴汽车的两侧玻璃上。当观者穿过城市,从农业部门口搭乘这辆带有汪建伟作品“痕迹”的中巴时,事实上就已经构成“循环——种植”的一部分。半透明的车窗,使观者对未知事物的要求有了一种虚幻的心理补偿,化解了太多的神秘感所造成的尴尬。由于在场的模糊和不可企及,人们只能在能指的扩散与延迟中寻找一时的意义与满足。这一方面从某种角度透视出中国当代艺术的现实处境;另一方面亦将实验的范围由知识结构拓展到社会环境、规划、行为等更为开放的空间。在汪建伟的作品由城市到乡村的线性穿行和展露的过程中,张德峰也利用城市与展览场地的路线,将从农业部至姚家园村北展览场地的6.4 公里路线分割成11个路段,标出米数的标版立于路旁。当观者沿着这一路线前来参观这个展览时,就已经构成了张德峰这个关于《距离》的作品的一部分,也就成为了城市与乡村,中心与边缘的一种“存在距离”,由此可以阐发出一种人文主义的忧虑——城市和乡村的距离以及这种距离感的即将消失。
在展厅里,展望真实地模拟了一间学院式雕塑教学的车间,几十尊大大小小的石膏像摆放其中。这些令人熟悉的石膏模特儿,不禁使人联想起中国美术教育中的记忆片断。而观众在“只需5 分钟让你享受大师的荣耀,创造大师的作品”的感召与诱感下,通过实际的操作与介入,不仅抹平了观众与艺术家之间的界限,而且使这件题为《新艺术速成车间》的作品,与被接受被纳入的观众之间有了无限扩展的可能。或许真正的在场并不存在,波普式的解构主流艺术才是永恒的目的。而这种解构的结果,似乎又总是笼罩在西方文化参照系的语境中,苦苦挣扎而又在劫难逃。同样是虚置现实,蔡青的《耕种》依照原始自然的耕种方式,以极为认真投入的姿态,颇为荒诞地将几百枚钱币,播散在被犁开的土地之上,“种子”物化为金钱,种植、生长的形态转化为人对金钱的贪婪的“本相”。他所热衷表现的其实就是当今社会中人人都在为之垂涎、奋斗的欲望。看似荒诞不经的行为恰恰是当下生存状态的现实表达。与耕种收获有关的还有汪建伟的作品《膜》,他于1993年10月在川西平原实施了为期一年的《循环——种植》的工作,作为这一实验性作品的逻辑延续,他将收获的麦粒,用乳胶粘贴在接送观看这次展览的交通工具——中巴汽车的两侧玻璃上。当观者穿过城市,从农业部门口搭乘这辆带有汪建伟作品“痕迹”的中巴时,事实上就已经构成“循环——种植”的一部分。半透明的车窗,使观者对未知事物的要求有了一种虚幻的心理补偿,化解了太多的神秘感所造成的尴尬。由于在场的模糊和不可企及,人们只能在能指的扩散与延迟中寻找一时的意义与满足。这一方面从某种角度透视出中国当代艺术的现实处境;另一方面亦将实验的范围由知识结构拓展到社会环境、规划、行为等更为开放的空间。在汪建伟的作品由城市到乡村的线性穿行和展露的过程中,张德峰也利用城市与展览场地的路线,将从农业部至姚家园村北展览场地的6.4 公里路线分割成11个路段,标出米数的标版立于路旁。当观者沿着这一路线前来参观这个展览时,就已经构成了张德峰这个关于《距离》的作品的一部分,也就成为了城市与乡村,中心与边缘的一种“存在距离”,由此可以阐发出一种人文主义的忧虑——城市和乡村的距离以及这种距离感的即将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