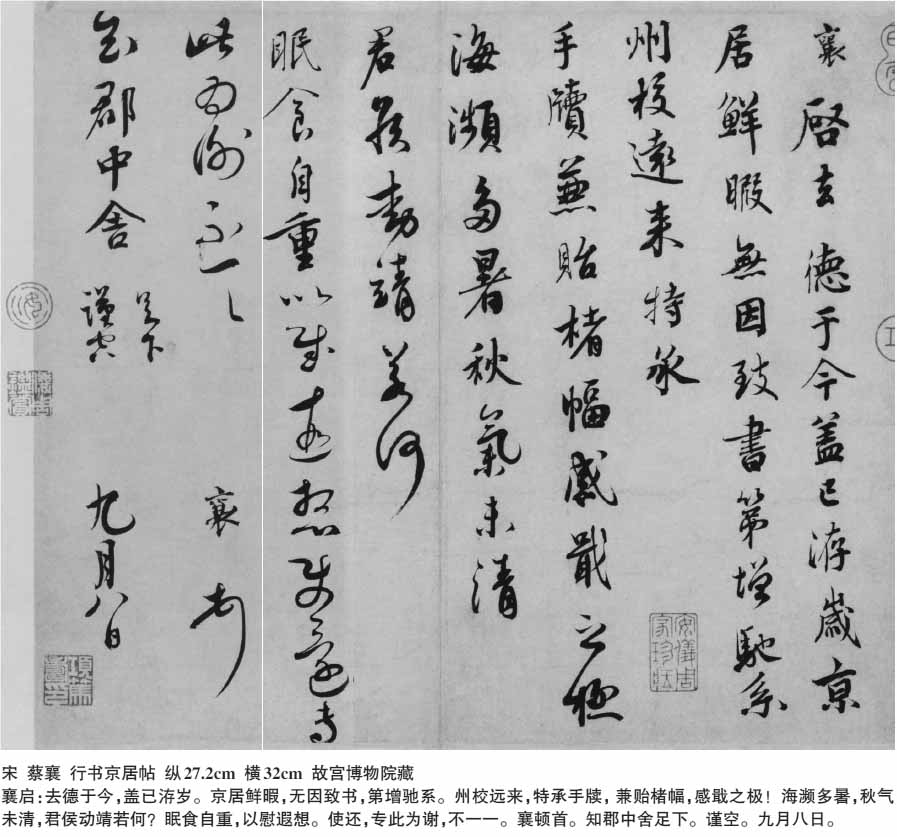云南省图书馆机构用户,欢迎您!
蔡襄是书法史上的一个关键性人物,他是北宋书法衰落和繁荣间的一道分水岭。继欧阳修之后,苏轼高度推崇蔡襄,称其为『本朝第一』。本文认为,苏轼对蔡襄的推崇,是由于其书法审美观与蔡襄书法实践的契合,尤其看重蔡襄书法中所体现的法度,这也说明苏轼书学思想在『尚意』之外,也有『尚法』的一面。从蔡襄开始,宋代书法回归法度,承接正脉,使书法发展走上了正途,为苏、黄、米的突破提供了铺垫和准备,这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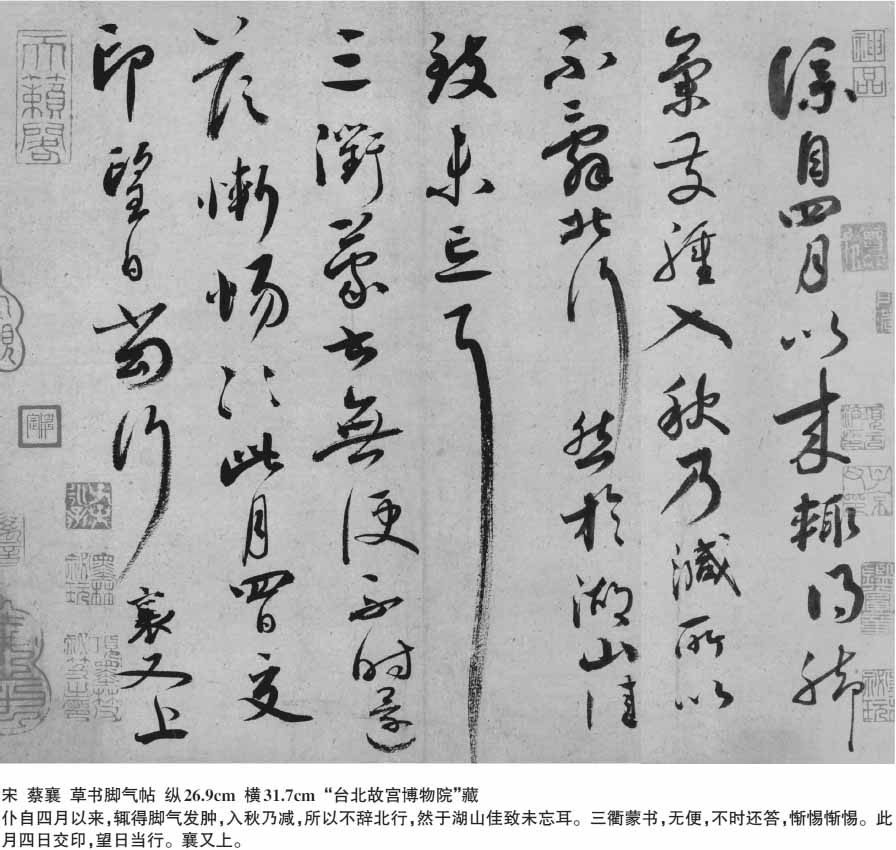 如此不厌其烦地反复重申,若仅目为谙于世故的随声附和,则东坡也未免『演得太过』了,更何况『(论者)多以为不然,然仆终守此说也』,语气中已透露出捍卫己见的近乎固执之态,若世故者,恐怕不易为此言也。 综观东坡论书,从不肯轻易盲从附和别人的意见,若涉及批评,虽口气往往委婉,常顾左右而言他,但绝不至于作违心的虚誉,若是赞扬,也是恰到好处,断无肉麻的吹捧,我们不妨也引几例为证。 《东坡题跋》卷四第四则《题〈遗教经〉》: 仆尝见欧阳文忠公云:『《遗教经》非逸少笔。』以其言观之,信若不妄。然自逸少在时,小儿乱真,自不解辨,况数百年后传刻之余,而欲必其真伪,难矣。顾笔画精稳,自可为师法。[13]
如此不厌其烦地反复重申,若仅目为谙于世故的随声附和,则东坡也未免『演得太过』了,更何况『(论者)多以为不然,然仆终守此说也』,语气中已透露出捍卫己见的近乎固执之态,若世故者,恐怕不易为此言也。 综观东坡论书,从不肯轻易盲从附和别人的意见,若涉及批评,虽口气往往委婉,常顾左右而言他,但绝不至于作违心的虚誉,若是赞扬,也是恰到好处,断无肉麻的吹捧,我们不妨也引几例为证。 《东坡题跋》卷四第四则《题〈遗教经〉》: 仆尝见欧阳文忠公云:『《遗教经》非逸少笔。』以其言观之,信若不妄。然自逸少在时,小儿乱真,自不解辨,况数百年后传刻之余,而欲必其真伪,难矣。顾笔画精稳,自可为师法。[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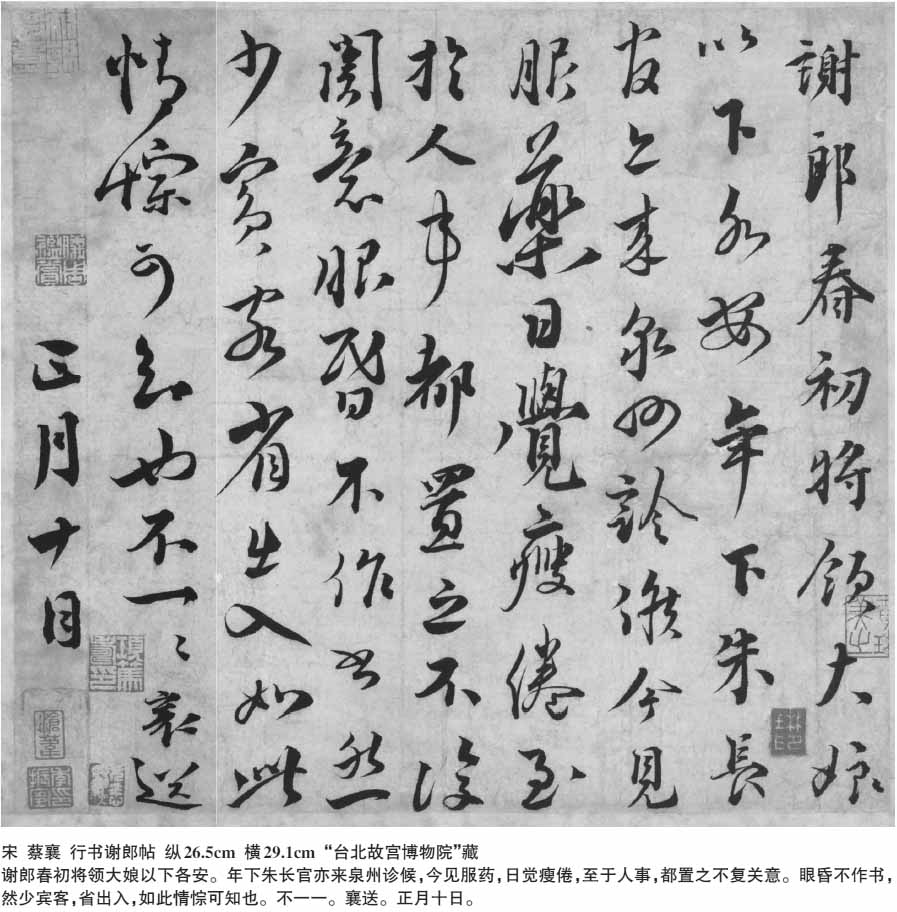 显然,苏轼在这里并不赞成欧阳修『《遗教经》非逸少笔』的断言,甚至有以其为真的倾向,但碍于情面没有公开反对,作了『阳奉阴违』的处置,但至少说明苏轼对于欧阳修的观点并非一一不假思索地全盘接受,而是保持了思想上的独立。 又,同上第六十则《跋钱君倚书〈遗教经〉》: 人貌有好丑,而君子小人之态不可掩也;言有辩讷,而君子小人之气不可欺也;书有工拙,而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乱也。钱公虽不学书,然观其书,知其为挺然忠信礼义人也。轼在杭州,与其子世雄为僚,因得观其所书佛《遗教经》刻石,峭峙有不回之势。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讱。』今君倚之书,盖讱云。[14]
显然,苏轼在这里并不赞成欧阳修『《遗教经》非逸少笔』的断言,甚至有以其为真的倾向,但碍于情面没有公开反对,作了『阳奉阴违』的处置,但至少说明苏轼对于欧阳修的观点并非一一不假思索地全盘接受,而是保持了思想上的独立。 又,同上第六十则《跋钱君倚书〈遗教经〉》: 人貌有好丑,而君子小人之态不可掩也;言有辩讷,而君子小人之气不可欺也;书有工拙,而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乱也。钱公虽不学书,然观其书,知其为挺然忠信礼义人也。轼在杭州,与其子世雄为僚,因得观其所书佛《遗教经》刻石,峭峙有不回之势。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讱。』今君倚之书,盖讱云。[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