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图书馆机构用户,欢迎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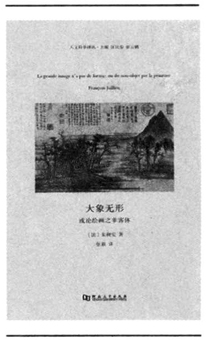 “诗歌,尤其是山水画(自其开端以来,即公元四世纪至五世纪的顾恺之、宗炳)直接关联于中国思想的观念,尤其是道家观念。”③如果一个中国学者从道家思想(老子、庄子)理解中国山水画,或阐释中国山水画论,这不过是从源思想阐释次生文本的惯常思路。徐复观的《中国艺术精神》一书在取材、思路上与《大象无形》的相似性,也足以说明朱利安从道家思想讨论中国画论,或者从山水画论讨论道家思想的思路不足为奇。苏立文(Michael Sullivan)《中国艺术史》一书的开篇也多少道出朱利安有关山水画的基本想法:“一个民族的起源传说……表达了中国人一个亘古的观点:人不是创造的终极成就,人在世间万物的规则中只占据了一个相对而言无关紧要的位置……与壮观瑰丽的世界和作为‘道’的表现的山川、风云、树木、花草相比,人实在是微不足道的。其他任何文明都没有如此强调自然的形态和模式,以及人的恭顺回应。”④那么,说到《大象无形》的另一面,也就是朱利安惯常的借道中国反思欧洲的思路,究竟又有什么特别之处? 这里需要提到的是郝大维、安乐哲的《通过孔子而思》一书,它的题目即与朱利安的方法论不谋而合。这部著作出版于1987年,这足以说明朱利安的方法并不新颖。虽然郝大维、安乐哲并没有朱利安那种迂回曲折、从中国回到欧洲的心思,但他们的研究首先要面对的,正是儒家思想与形而上学之间的明显差异。事实上,这是研究中国思想的西方学者无法回避的:“因为,通过反思孔子之‘思’的意义以及它与哲学的关系,会让我们考虑到一个极具相关性的问题——或许,今天,盎格鲁—欧洲哲学最急需探讨的哲学问题,就是哲学学科的特性及其在整个文化中的地位。”⑤这里便出现了一个问题:在涉及中国思想的汉学领域,由中国思想所引发的有关西方形而上学的反思如此普遍,它能够作为一种独特的方法被使用吗?在《通过孔子而思》一书的开头,作者提出了几个悖常(即与形而上学成见完全不同的)假定,试图为儒家思想勾勒一个基本框架,并特别指出这一基本框架是属于特定知识系统中的成员建构哲学对话的基础。它包括三点:“内在宇宙论”“反向性概念”以及“传统:作为诠释语境”。前两点分别是孔子的现象本体论和儒家对“任何有害的二元对立”⑥的戒绝。这两点和朱利安所说的中国思想对西方形而上学基础的撼动完全一致。不同之处在于,中西思想的差异只是郝大维、安乐哲为自己解读《论语》所写的序曲,以便使西方读者能够多少摆脱其哲学成见和惯性思维,对朱利安而言,中西思想的差异却是他的核心论域,他对这些差异的描述和分析系统而深入,简言之,朱利安所做的正是比较哲学的工作。 一、中国山水画论的后现代主义阐释 语言占据了朱利安工作的核心,对原文的翻译以及由此而来的阐释,总会使译文和原文所涉及的两种语言都受到强烈的冲击,尤其是他所翻译和阐释的文本是《老子》。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出朱利安为阐释道家思想所做的语言上的努力,他几乎是以法语创造了另一套语言,这种语言竭力避免西方形而上学的痕迹,比如以“cohérence”来翻译“望之无形,揆之有理”中的“理”,而不是用西方哲学中现成的“rason”,用“丰盛性”(consistence)来替代“essence”(本质),以“不分明”(l'indistinct)、“本根”(le foncier)、“未分化基底”(Fonds indifférencié)等术语来阐发“道”,以严谨性效果、调适性来说明“道”的运行方式。他始终警惕语言的怠惰,比如反对不加反思地使用“欧洲思想”“中国思想”这类词,对已有的《老子》法文译文中所出现的本体论化、希腊化或者轻易含混的处理也毫不留情。他认定必须在译文中凸显原文本身极致的矛盾色彩,如果将其中的矛盾弱化,“这种舍难求易的做法(lectio facilior),不仅是极端迂腐的,不仅把一切可以引发思考的东西统统当成雷区加以清扫,而且它同样在整段文字的行文上造成颇为奇怪的漏洞”⑦。毫无疑问,这是比较哲学的特定框架带给他的习惯和好处。《大象无形》一书的出版,对于中西画论比较研究最大的影响,可能就是终结各种相关著作对于“再现”“表现”的滥用:“今天的中国评注者,似乎受了欧洲‘摹仿说’(mimésis)的影响,甚至对后者不加分析地接受下来。”⑧事实上,这种滥用不仅见于国内学者编辑的历代中国画论,也见于汉学家所著的中国艺术史中。
“诗歌,尤其是山水画(自其开端以来,即公元四世纪至五世纪的顾恺之、宗炳)直接关联于中国思想的观念,尤其是道家观念。”③如果一个中国学者从道家思想(老子、庄子)理解中国山水画,或阐释中国山水画论,这不过是从源思想阐释次生文本的惯常思路。徐复观的《中国艺术精神》一书在取材、思路上与《大象无形》的相似性,也足以说明朱利安从道家思想讨论中国画论,或者从山水画论讨论道家思想的思路不足为奇。苏立文(Michael Sullivan)《中国艺术史》一书的开篇也多少道出朱利安有关山水画的基本想法:“一个民族的起源传说……表达了中国人一个亘古的观点:人不是创造的终极成就,人在世间万物的规则中只占据了一个相对而言无关紧要的位置……与壮观瑰丽的世界和作为‘道’的表现的山川、风云、树木、花草相比,人实在是微不足道的。其他任何文明都没有如此强调自然的形态和模式,以及人的恭顺回应。”④那么,说到《大象无形》的另一面,也就是朱利安惯常的借道中国反思欧洲的思路,究竟又有什么特别之处? 这里需要提到的是郝大维、安乐哲的《通过孔子而思》一书,它的题目即与朱利安的方法论不谋而合。这部著作出版于1987年,这足以说明朱利安的方法并不新颖。虽然郝大维、安乐哲并没有朱利安那种迂回曲折、从中国回到欧洲的心思,但他们的研究首先要面对的,正是儒家思想与形而上学之间的明显差异。事实上,这是研究中国思想的西方学者无法回避的:“因为,通过反思孔子之‘思’的意义以及它与哲学的关系,会让我们考虑到一个极具相关性的问题——或许,今天,盎格鲁—欧洲哲学最急需探讨的哲学问题,就是哲学学科的特性及其在整个文化中的地位。”⑤这里便出现了一个问题:在涉及中国思想的汉学领域,由中国思想所引发的有关西方形而上学的反思如此普遍,它能够作为一种独特的方法被使用吗?在《通过孔子而思》一书的开头,作者提出了几个悖常(即与形而上学成见完全不同的)假定,试图为儒家思想勾勒一个基本框架,并特别指出这一基本框架是属于特定知识系统中的成员建构哲学对话的基础。它包括三点:“内在宇宙论”“反向性概念”以及“传统:作为诠释语境”。前两点分别是孔子的现象本体论和儒家对“任何有害的二元对立”⑥的戒绝。这两点和朱利安所说的中国思想对西方形而上学基础的撼动完全一致。不同之处在于,中西思想的差异只是郝大维、安乐哲为自己解读《论语》所写的序曲,以便使西方读者能够多少摆脱其哲学成见和惯性思维,对朱利安而言,中西思想的差异却是他的核心论域,他对这些差异的描述和分析系统而深入,简言之,朱利安所做的正是比较哲学的工作。 一、中国山水画论的后现代主义阐释 语言占据了朱利安工作的核心,对原文的翻译以及由此而来的阐释,总会使译文和原文所涉及的两种语言都受到强烈的冲击,尤其是他所翻译和阐释的文本是《老子》。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出朱利安为阐释道家思想所做的语言上的努力,他几乎是以法语创造了另一套语言,这种语言竭力避免西方形而上学的痕迹,比如以“cohérence”来翻译“望之无形,揆之有理”中的“理”,而不是用西方哲学中现成的“rason”,用“丰盛性”(consistence)来替代“essence”(本质),以“不分明”(l'indistinct)、“本根”(le foncier)、“未分化基底”(Fonds indifférencié)等术语来阐发“道”,以严谨性效果、调适性来说明“道”的运行方式。他始终警惕语言的怠惰,比如反对不加反思地使用“欧洲思想”“中国思想”这类词,对已有的《老子》法文译文中所出现的本体论化、希腊化或者轻易含混的处理也毫不留情。他认定必须在译文中凸显原文本身极致的矛盾色彩,如果将其中的矛盾弱化,“这种舍难求易的做法(lectio facilior),不仅是极端迂腐的,不仅把一切可以引发思考的东西统统当成雷区加以清扫,而且它同样在整段文字的行文上造成颇为奇怪的漏洞”⑦。毫无疑问,这是比较哲学的特定框架带给他的习惯和好处。《大象无形》一书的出版,对于中西画论比较研究最大的影响,可能就是终结各种相关著作对于“再现”“表现”的滥用:“今天的中国评注者,似乎受了欧洲‘摹仿说’(mimésis)的影响,甚至对后者不加分析地接受下来。”⑧事实上,这种滥用不仅见于国内学者编辑的历代中国画论,也见于汉学家所著的中国艺术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