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图书馆机构用户,欢迎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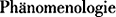 ,Buddihismus,Konfuzianismus”,譯著有《邏輯研究》([德]胡塞爾)《內時間意識現象學》([德]胡塞爾)《倫理學中的形式主義與質料的價值倫理學》([德]馬克斯·舍勒)等。
,Buddihismus,Konfuzianismus”,譯著有《邏輯研究》([德]胡塞爾)《內時間意識現象學》([德]胡塞爾)《倫理學中的形式主義與質料的價值倫理學》([德]馬克斯·舍勒)等。胡塞爾與他的學生、同時也是“反納粹哲學家”希爾德勃蘭特在價值倫理學方面的思考各有特色,並且相互影響。對於胡塞爾來說,價值領域的情況是與經驗領域和觀念領域的情況相似的。在其戰前的倫理學與價值論講座中,他強調價值的規律性和價值的客觀性,並將對價值的發現和把握理解爲一種特殊的認知活動。他提出的“價值認定”的概念影響了希爾德勃蘭特和舍勒的價值倫理學思考。胡塞爾所提出的邏輯學與價值論之間的平行性在希爾德勃蘭特這裏得到了繼承,而且在這兩者之間的奠基關係也在胡塞爾意義上而非在舍勒的意義上得到確定。可是,一旦將價值本身視爲客體,情況就會變得複雜起來,甚至結論也會變得矛盾起來。而且,接下來還會面臨這樣的問題:這種客體是自在存在意義土的客體,還是交互主體意義上的客體的問题,如此等等。或許應當提出一種非本體論的、但仍然是現象學的價值論解釋的可能性:對象衹有一個,它在感知中自身被給予,同時還必然會被認之爲真,但同時也可以被認之爲有價值。這是兩種執態模式,或者也可以說是兩種認定模態:存在設定模態與價值設定模態。在感知中,前者具有必然性,後者衹具有可能性。即是說,在感知一個事物時,“我”必定會將它認之爲存在的,但可能也會將它認之爲有價值的。這種認定,應當就是伴隨在感知過程中的存在意識和價值意識,即大乘佛學中的“唯識學”所說的自證分,它伴隨“見分—相分”,但本身不是“見分—相分”。
 ,1870-1941)、莫里茲·蓋格爾(M.Geiger,1880-1937)、馬克斯·舍勒(M.Scheler,1874-1928)等人學習。從一開始,他便受到慕尼黑現象學家的影響,尤其是來自舍勒的影響。 希爾德勃蘭特與胡塞爾(E.G.A.Husserl,1859-1938)發生關聯,最初是蓋格爾在1907年3月27日寫給胡塞爾的信中報告一次學術活動時,順便提到了希爾德勃蘭特:“而後是一位十七歲的大學生希爾德勃蘭特(雕塑家的兒子)報告藝術作品中的素材——一個不衹是對他這個年齡而言的輝煌成就。”(Hua Brief.Ⅱ,89)一年多以後,通過利普斯的幾位學生的建議和介紹,希爾德勃蘭特於1909年夏季學期從慕尼黑轉到哥廷根學習,試圖日後在胡塞爾指導下完成博士論文考試。 關於那時的希爾德勃蘭特,蓋格爾在1909年4月2日致胡塞爾的信中做了詳細的介紹和推薦: 您可能已經通過萊納赫和康拉德知道,年輕的希爾德勃蘭特——這位無疑是我們慕尼黑最有才華的年輕哲學生——下學期要到哥廷根來。我還想向您再次特別推薦他,並且還提出一個與此相關的請求:恰恰在這樣一個如此有才華的年輕人那裏有一個加倍的危險:他可能會踏上一條歧途。他現在極度地神經質,這一點也表現爲:凡是他感興趣的一切,他都無法遏制。這也是我將他驅離慕尼黑的原因。他在這裏有無窮無盡的社交活動刺激,他無法抗拒它們。這已足以能夠摧毀一個神經質的年輕人了。另一方面,他帶着如此的激情投入到哲學問題中,以至於我必須费盡全部心力來阻止他不要在他恰好思考的個別問題上過度勞累地工作。因此,我竭力地阻止了他在學會裏做一個報告,也阻止了他在我的討論課上做一個專題評論。——他首先最需要做的不是在哲學問題中的深化,而是對事實知識的獲取。他可以說是在缺乏事實基礎的情況下做哲學。他還沒有受過工作訓練,而是像一頭公牛衝向一塊紅布一樣撲向哲學問題。因此,也許他最好是仔細地學習一下數學和物理,而不是那麼多的哲學。所以,我請您先違背他的心願,阻止他做專題評論。您不必擔心在哲學中的些許退步會將他帶離正軌。我從未見過有人像勾勾·希爾德勃蘭特①那樣對所有那些不“相信”現象學、絕對價值以及如此等等的人抱有如此輕蔑的態度。此外,我堅信,這位生機勃勃、麻利活潑的青年人會讓您感到開心喜悅的。② 希爾德勃蘭特來到哥廷根後,隨胡塞爾學習了兩年時間。在此期間,他主要受胡塞爾當時的助手、已經在哥廷根擔任私人教師的阿道夫·萊納赫(A.B.P.Reinach,1883-1917)的指導。看起來,胡塞爾並未接受蓋格爾的建議而阻止希爾德勃蘭特在學會作報告。相反,按照希爾德勃蘭特在自傳中的說法,他在1911年夏季學期,還因爲兩次“哥廷根哲學學會”的出色報告而擔任了這個學會的主席。③而這個學會,實際上就是現象學的“哥廷根學派”的實際組成。而在此期間,由於其第二次的“婚姻醜聞”,舍勒不得不於1910年放棄其私人講師的工作,離開慕尼黑大學。此時,希爾德勃蘭特也在哥廷根。通過他的中介,舍勒受胡塞爾邀請,自1910年夏季學期起,在哥廷根爲胡塞爾的學生做一些校園之外的定期講座。④這種講座,一直延續到希爾德勃蘭特於1912年完成博士考試回到慕尼黑,以及埃迪·施泰因(E.Stein,1891-1942)1913年來到哥廷根之後。希爾德勃蘭特將他與舍勒在第二學期結束時的交往,視爲在此生活期間最重要的事件。⑤看起來,希爾德勃蘭特在慕尼黑和哥廷根聽過的舍勒的課程要多於胡塞爾的課程;而且,在現象學運動中,現象學倫理學的方向的確也是由舍勒最早開啟的。所以,也就不難理解,埃迪·施泰因在後來的回憶錄中所述:“年輕的現象學家們受舍勒的影響很大;有些人——如希爾德勃蘭特和克萊門斯——注重他甚於注重胡塞爾。”⑥ 1912年,希爾德勃蘭特完成了他的博士論文《行動內的倫常載體》⑦,並於當年11月6日通過考試。此前,胡塞爾於7月30日所撰“迪特里希·希爾德勃蘭特⑧博士論文評語”中寫道: 我滿懷喜悅地閱讀了這部博士論文。我幾乎想要說: 阿道夫·希爾德勃蘭特的天賦作爲哲學天賦遺傳給了他的兒子,即本書的作者。在這部著作中,的確表現出一種罕見的才華:從現象學直覺的深處中汲取,對被直觀之物進行敏銳的分析,並且以最嚴格的方法對它進行概念的把握。他的現象學研究在這裏完全服務於重大的哲學問題,並且它事實上也導向對它們的解決。儘管在現象學的方法和問題域中,個別的思想系列受到了我的以及與我親近的年輕研究者們(舍勒、普凡德爾、萊納赫)的講座和著述的規定,但作者從未表現出有拘束效仿的特徵。他作爲獨立的思者走自己的路,並且開啟了多重的新視角。藉此,像康德那樣歷史上的重大思想構成也得到了新的昭示。構成他的論題的,是那些圍繞着對不同倫理價值質性及其載體進行區分的基本問題。至此爲止的倫理學,通常無法勝任那些原本從屬於價值謂項的不同載體的雜多性,而相應的現象學起源分析一直付之闕如。作者致力於填補這一重大缺失,指明與此缺失相關的各個現象學層次,並且以分析的方式做出澄清。在這個一直逼近到最終基礎的努力中,他已經遠遠超出了倫理現象的領域,而且他敢於深入到一門普遍意識現象學一般的最深刻問題之中,且有所成就。然而,就最重要的方面而言,他的真正強項以及他的顯著而原創的結果還是在情感領域中、在第二部分的第三至八章的分析中得到實現的,並且通過一種對情感意識及其對象相關項之雜多形態的空前諳熟知識而令人驚異不已。根據以上所述,我衹能爲此重要的研究申請“傑出作品”(opus eximium)的成績。(Hua Brief.III,125f.)
,1870-1941)、莫里茲·蓋格爾(M.Geiger,1880-1937)、馬克斯·舍勒(M.Scheler,1874-1928)等人學習。從一開始,他便受到慕尼黑現象學家的影響,尤其是來自舍勒的影響。 希爾德勃蘭特與胡塞爾(E.G.A.Husserl,1859-1938)發生關聯,最初是蓋格爾在1907年3月27日寫給胡塞爾的信中報告一次學術活動時,順便提到了希爾德勃蘭特:“而後是一位十七歲的大學生希爾德勃蘭特(雕塑家的兒子)報告藝術作品中的素材——一個不衹是對他這個年齡而言的輝煌成就。”(Hua Brief.Ⅱ,89)一年多以後,通過利普斯的幾位學生的建議和介紹,希爾德勃蘭特於1909年夏季學期從慕尼黑轉到哥廷根學習,試圖日後在胡塞爾指導下完成博士論文考試。 關於那時的希爾德勃蘭特,蓋格爾在1909年4月2日致胡塞爾的信中做了詳細的介紹和推薦: 您可能已經通過萊納赫和康拉德知道,年輕的希爾德勃蘭特——這位無疑是我們慕尼黑最有才華的年輕哲學生——下學期要到哥廷根來。我還想向您再次特別推薦他,並且還提出一個與此相關的請求:恰恰在這樣一個如此有才華的年輕人那裏有一個加倍的危險:他可能會踏上一條歧途。他現在極度地神經質,這一點也表現爲:凡是他感興趣的一切,他都無法遏制。這也是我將他驅離慕尼黑的原因。他在這裏有無窮無盡的社交活動刺激,他無法抗拒它們。這已足以能夠摧毀一個神經質的年輕人了。另一方面,他帶着如此的激情投入到哲學問題中,以至於我必須费盡全部心力來阻止他不要在他恰好思考的個別問題上過度勞累地工作。因此,我竭力地阻止了他在學會裏做一個報告,也阻止了他在我的討論課上做一個專題評論。——他首先最需要做的不是在哲學問題中的深化,而是對事實知識的獲取。他可以說是在缺乏事實基礎的情況下做哲學。他還沒有受過工作訓練,而是像一頭公牛衝向一塊紅布一樣撲向哲學問題。因此,也許他最好是仔細地學習一下數學和物理,而不是那麼多的哲學。所以,我請您先違背他的心願,阻止他做專題評論。您不必擔心在哲學中的些許退步會將他帶離正軌。我從未見過有人像勾勾·希爾德勃蘭特①那樣對所有那些不“相信”現象學、絕對價值以及如此等等的人抱有如此輕蔑的態度。此外,我堅信,這位生機勃勃、麻利活潑的青年人會讓您感到開心喜悅的。② 希爾德勃蘭特來到哥廷根後,隨胡塞爾學習了兩年時間。在此期間,他主要受胡塞爾當時的助手、已經在哥廷根擔任私人教師的阿道夫·萊納赫(A.B.P.Reinach,1883-1917)的指導。看起來,胡塞爾並未接受蓋格爾的建議而阻止希爾德勃蘭特在學會作報告。相反,按照希爾德勃蘭特在自傳中的說法,他在1911年夏季學期,還因爲兩次“哥廷根哲學學會”的出色報告而擔任了這個學會的主席。③而這個學會,實際上就是現象學的“哥廷根學派”的實際組成。而在此期間,由於其第二次的“婚姻醜聞”,舍勒不得不於1910年放棄其私人講師的工作,離開慕尼黑大學。此時,希爾德勃蘭特也在哥廷根。通過他的中介,舍勒受胡塞爾邀請,自1910年夏季學期起,在哥廷根爲胡塞爾的學生做一些校園之外的定期講座。④這種講座,一直延續到希爾德勃蘭特於1912年完成博士考試回到慕尼黑,以及埃迪·施泰因(E.Stein,1891-1942)1913年來到哥廷根之後。希爾德勃蘭特將他與舍勒在第二學期結束時的交往,視爲在此生活期間最重要的事件。⑤看起來,希爾德勃蘭特在慕尼黑和哥廷根聽過的舍勒的課程要多於胡塞爾的課程;而且,在現象學運動中,現象學倫理學的方向的確也是由舍勒最早開啟的。所以,也就不難理解,埃迪·施泰因在後來的回憶錄中所述:“年輕的現象學家們受舍勒的影響很大;有些人——如希爾德勃蘭特和克萊門斯——注重他甚於注重胡塞爾。”⑥ 1912年,希爾德勃蘭特完成了他的博士論文《行動內的倫常載體》⑦,並於當年11月6日通過考試。此前,胡塞爾於7月30日所撰“迪特里希·希爾德勃蘭特⑧博士論文評語”中寫道: 我滿懷喜悅地閱讀了這部博士論文。我幾乎想要說: 阿道夫·希爾德勃蘭特的天賦作爲哲學天賦遺傳給了他的兒子,即本書的作者。在這部著作中,的確表現出一種罕見的才華:從現象學直覺的深處中汲取,對被直觀之物進行敏銳的分析,並且以最嚴格的方法對它進行概念的把握。他的現象學研究在這裏完全服務於重大的哲學問題,並且它事實上也導向對它們的解決。儘管在現象學的方法和問題域中,個別的思想系列受到了我的以及與我親近的年輕研究者們(舍勒、普凡德爾、萊納赫)的講座和著述的規定,但作者從未表現出有拘束效仿的特徵。他作爲獨立的思者走自己的路,並且開啟了多重的新視角。藉此,像康德那樣歷史上的重大思想構成也得到了新的昭示。構成他的論題的,是那些圍繞着對不同倫理價值質性及其載體進行區分的基本問題。至此爲止的倫理學,通常無法勝任那些原本從屬於價值謂項的不同載體的雜多性,而相應的現象學起源分析一直付之闕如。作者致力於填補這一重大缺失,指明與此缺失相關的各個現象學層次,並且以分析的方式做出澄清。在這個一直逼近到最終基礎的努力中,他已經遠遠超出了倫理現象的領域,而且他敢於深入到一門普遍意識現象學一般的最深刻問題之中,且有所成就。然而,就最重要的方面而言,他的真正強項以及他的顯著而原創的結果還是在情感領域中、在第二部分的第三至八章的分析中得到實現的,並且通過一種對情感意識及其對象相關項之雜多形態的空前諳熟知識而令人驚異不已。根據以上所述,我衹能爲此重要的研究申請“傑出作品”(opus eximium)的成績。(Hua Brief.III,125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