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图书馆机构用户,欢迎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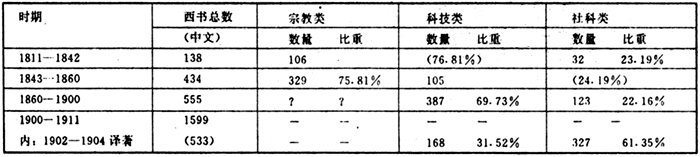 如果说,近代西书的出版种数,前人已作过相当的目录学方面的工作,那么,揭示这个几乎是汗牛充栋的书库的基本内容,则是熊著所要担负的更为艰巨的任务。这不仅是由于内容庞杂,判明其历史文化价值不易,而且还需要研究者自身具备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以及历史学方面广博的知识。仅仅是这些图书搜集之困难、阅读量之巨大,也足以令人生畏。例如,熊月之先生仔细地阅读了《察世俗每月统纪传》、《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等罕见的报刊,并介绍了其主要的内容,对于19世纪出版的天文、地理、生物、数学、物理、化学、医学等重要西学译著,作者并不满足于引用中国科学技术史方面的已有成果,而直接研读原书,指出其外文原著,中译本的版本沿革,当时中国科学家和学者对各书的评价等等,充分体现了历史学专著的特色,为了搜寻、阅读这批书刊,熊先生不仅充分利用了国内图书馆、大专院校和科研机关的藏书,而且利用了美国、英国国家图书馆和大学收藏的文献档案。这批文献档案经作者首次向中国学术界披露,不仅使这部著作本身增添了学术价值,而且体现了国际交流对于中国学术进步的促进作用。 二 西学东渐,作为一种文化传播现象,必然涉及传播学领域的一些特殊问题,如传播客体、传播者、传播媒介、受众(传播对象)、传播效果等等。如何在历史学研究中运用传播学原理,《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的作者进行了可贵的探索。 所谓传播客体,是指信息在未经传播之前内容或状态。传播客体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到达受众,必然经过传播者、传播媒介的层层过滤和消化以后才能到达受众。而受众对于接受的信息也只能在各自特定的文化、社会和历史的背景下进行选择、理解和消化;较早的受众又可能成为再传播者,经过本体文化受众的不断反刍,才能吸收异体文化的信息。这种被受众吸收了的信息与传播客体本身信息质与量也不可能是相同的。可见,探讨和描述西学东渐,无疑是一项繁琐、细致和复杂的工作。 在西学东渐过程中,作为西方文化的传播者西方传教士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作者花了相当的篇幅论述了如傅兰雅、李提摩太、林乐知等著名传教士的生平事迹,对于乌礼逊、米怜、郭实腊、裨治文、理雅各、麦都思、合信、卢公明、伟烈亚力……等一大批教士的传播活动也给予了比较充分的叙述。作者在肯定了19世纪中叶以后的西方传教士享有不平等条约庇护的前提下,着重刻划了他们欧洲中心主义的文化优越心态,作为传教士的使命,各人的经历知识结构和中国受众在不同历史时期信息需要的变化是如何决定其对传播内容选择的。例如墨海书馆创办人麦都思之成为晚清出版界的巨子,得益于他早年充当印刷工学徒的经历。而傅兰雅热心于中国的教育事业,既然受到父辈的影响,也由于他在英国受过系统的师范教育。李提摩太为了用科学知识赢得中国知识分子,发愤自修自然科学知识。当中国维新思想和运动兴起之时,又加强了维新变法书籍的出版和宣传。纵观全书,读者不难得到这样一个印象,在19世纪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中,虽然不乏有赤裸裸的侵略者,单纯的布道者,但不能否认,确实有由传教士转变为西学的热情传播者,他们真诚地希望中国进步、强大。他们具有值得尊敬的人格和献身精神,他们的缺点更多地是由于自身的历史局限性,而不是所谓作为“侵略者”的劣根性。 早期西学书籍的翻译,一般都采取西译中述的方式,即由外国学者用粗通的中文口译西书意思,中国合作者润色加工,条理成文。中国合作者只能通过外国学者的口述来了解西书内容,并且在中国文化的立场上接受、理解其内容,这是西学东渐不得不经历的困难而又痛苦的过程。在科学技术领域,有象李善兰、徐寿、华蘅芳、徐建寅这样杰出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专家合作,不仅成功地实现了中西科学成就的对接,而且能比较准确地介绍西方更先进的科学技术成就。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有相当部分的知识无法为中国传统文化所容纳和吸收,甚至是截然对立的。因此,早期西学译著中,哲学社会科学类图书相对较少,而且舛误较多,不仅由于当时中国人的文化选择,也是因为缺乏这方面的译才使然。熊月之先生认为,这是长久封闭而又被动开放的中国走向世界的必然产物,也是一种过渡时期的现象。到19世纪末,随着中国政治改革运动的展开,对于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需要日益强烈,通过留学和新式教育培养的精通西学的人材日益增加,西学大量涌入的时代便到来了。这种历史的、透彻的分析是令人信服的。 在清末的西学传播过程中,学校、报馆和出版机构的作用是巨大的。但对西学东渐的研究,不同于教育史、新闻史和出版史的研究。熊著采取了典型分析的方法。在学校方面,着重研究了教会学校,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格致书院;在报馆方面,着重研究了《万国公报》和《格致汇编》等;在出版机构方面,着重研究了墨海书馆、华花圣经书房、广学会、美华书馆、益智书会、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等。作者通过个案研究,揭示了各类传播机构在西学东渐过程中既相辅相成而又不同的作用。教育机构重在西学人材的培养,报刊具有普及、迅速、及时和有针对性的特点,而出版机构由于组织性强、人材多、经费多、发行渠道广,注意西学传播的系统性。
如果说,近代西书的出版种数,前人已作过相当的目录学方面的工作,那么,揭示这个几乎是汗牛充栋的书库的基本内容,则是熊著所要担负的更为艰巨的任务。这不仅是由于内容庞杂,判明其历史文化价值不易,而且还需要研究者自身具备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以及历史学方面广博的知识。仅仅是这些图书搜集之困难、阅读量之巨大,也足以令人生畏。例如,熊月之先生仔细地阅读了《察世俗每月统纪传》、《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等罕见的报刊,并介绍了其主要的内容,对于19世纪出版的天文、地理、生物、数学、物理、化学、医学等重要西学译著,作者并不满足于引用中国科学技术史方面的已有成果,而直接研读原书,指出其外文原著,中译本的版本沿革,当时中国科学家和学者对各书的评价等等,充分体现了历史学专著的特色,为了搜寻、阅读这批书刊,熊先生不仅充分利用了国内图书馆、大专院校和科研机关的藏书,而且利用了美国、英国国家图书馆和大学收藏的文献档案。这批文献档案经作者首次向中国学术界披露,不仅使这部著作本身增添了学术价值,而且体现了国际交流对于中国学术进步的促进作用。 二 西学东渐,作为一种文化传播现象,必然涉及传播学领域的一些特殊问题,如传播客体、传播者、传播媒介、受众(传播对象)、传播效果等等。如何在历史学研究中运用传播学原理,《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的作者进行了可贵的探索。 所谓传播客体,是指信息在未经传播之前内容或状态。传播客体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到达受众,必然经过传播者、传播媒介的层层过滤和消化以后才能到达受众。而受众对于接受的信息也只能在各自特定的文化、社会和历史的背景下进行选择、理解和消化;较早的受众又可能成为再传播者,经过本体文化受众的不断反刍,才能吸收异体文化的信息。这种被受众吸收了的信息与传播客体本身信息质与量也不可能是相同的。可见,探讨和描述西学东渐,无疑是一项繁琐、细致和复杂的工作。 在西学东渐过程中,作为西方文化的传播者西方传教士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作者花了相当的篇幅论述了如傅兰雅、李提摩太、林乐知等著名传教士的生平事迹,对于乌礼逊、米怜、郭实腊、裨治文、理雅各、麦都思、合信、卢公明、伟烈亚力……等一大批教士的传播活动也给予了比较充分的叙述。作者在肯定了19世纪中叶以后的西方传教士享有不平等条约庇护的前提下,着重刻划了他们欧洲中心主义的文化优越心态,作为传教士的使命,各人的经历知识结构和中国受众在不同历史时期信息需要的变化是如何决定其对传播内容选择的。例如墨海书馆创办人麦都思之成为晚清出版界的巨子,得益于他早年充当印刷工学徒的经历。而傅兰雅热心于中国的教育事业,既然受到父辈的影响,也由于他在英国受过系统的师范教育。李提摩太为了用科学知识赢得中国知识分子,发愤自修自然科学知识。当中国维新思想和运动兴起之时,又加强了维新变法书籍的出版和宣传。纵观全书,读者不难得到这样一个印象,在19世纪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中,虽然不乏有赤裸裸的侵略者,单纯的布道者,但不能否认,确实有由传教士转变为西学的热情传播者,他们真诚地希望中国进步、强大。他们具有值得尊敬的人格和献身精神,他们的缺点更多地是由于自身的历史局限性,而不是所谓作为“侵略者”的劣根性。 早期西学书籍的翻译,一般都采取西译中述的方式,即由外国学者用粗通的中文口译西书意思,中国合作者润色加工,条理成文。中国合作者只能通过外国学者的口述来了解西书内容,并且在中国文化的立场上接受、理解其内容,这是西学东渐不得不经历的困难而又痛苦的过程。在科学技术领域,有象李善兰、徐寿、华蘅芳、徐建寅这样杰出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专家合作,不仅成功地实现了中西科学成就的对接,而且能比较准确地介绍西方更先进的科学技术成就。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有相当部分的知识无法为中国传统文化所容纳和吸收,甚至是截然对立的。因此,早期西学译著中,哲学社会科学类图书相对较少,而且舛误较多,不仅由于当时中国人的文化选择,也是因为缺乏这方面的译才使然。熊月之先生认为,这是长久封闭而又被动开放的中国走向世界的必然产物,也是一种过渡时期的现象。到19世纪末,随着中国政治改革运动的展开,对于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需要日益强烈,通过留学和新式教育培养的精通西学的人材日益增加,西学大量涌入的时代便到来了。这种历史的、透彻的分析是令人信服的。 在清末的西学传播过程中,学校、报馆和出版机构的作用是巨大的。但对西学东渐的研究,不同于教育史、新闻史和出版史的研究。熊著采取了典型分析的方法。在学校方面,着重研究了教会学校,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格致书院;在报馆方面,着重研究了《万国公报》和《格致汇编》等;在出版机构方面,着重研究了墨海书馆、华花圣经书房、广学会、美华书馆、益智书会、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等。作者通过个案研究,揭示了各类传播机构在西学东渐过程中既相辅相成而又不同的作用。教育机构重在西学人材的培养,报刊具有普及、迅速、及时和有针对性的特点,而出版机构由于组织性强、人材多、经费多、发行渠道广,注意西学传播的系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