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2011)06-004-010 13世纪的欧洲知识界曾经发生过一场争论,焦点是:地理志——尤指地图反映客观世界和文字反映客观世界哪一个更准确?这场争论事实上反映了一个时代的重大变革——经过漫长的中世纪,人们对世界的了解逐渐从宗教羁绊中解脱出来,随着“地理大发现”,一个“新世界”呈现在人类的眼前;人们发现,以往用文字书写反映世界的方式不能完整表达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无法反映新的知识革命,于是,地图志前所未有地引起人们的重视。学者甚至宣称要给予地图比文字更优先的地位,至少要一视同仁。[1]虽然,这是一场没有胜负的争论,却反映出社会变革所带来的表述范式的特殊意义。哥伦布、麦哲伦探险、“五月花号”的欧洲移民、“三角贸易”、库克船长对太平洋岛屿的“发现”等事件,促使人们从地理的角度对人类传统的思维和表述方式进行反思。而地图志以一种全新的方式看待、认识和表述世界;同时,这场争论对地理科学也具有方法论的奠基作用。 今天,当我们重拾这一被忽略和淡忘的历史争论时,我们认识到地理曾经是一个革命性因素,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地理学科。在我国,地理学科是在“五四”前后才从西方引进的,[2]2与我国古代地理在知识体系上未能圆满对接,问题出现了:中国是否存在地理科学?中国的地理谱系和表述范式与西方的地理学科如何在研究中整合?这些都需要我们做出回答,而人类学的视野和方法值得尝试。 一、地方的地理政治表述 在中国,最具典型的地理概念是“地方”,但其政治指喻远大于地理意义。“地方”是一个具有巨大包容性的概念体系,主要有以下几种意思:1.认知性二元对峙。“天圆/地方”的结构形成了认知和感知世界的特殊模式,这种古老的认知模式对华夏文明有着发生学意义,即使在今天,我们仍可在诸多文化表述惯习上看到这一模式的痕迹。比如许多纪念和祭祀性建筑的主旨设想和主体都贯彻“天圆—地方”的理念(如华夏始祖黄帝陵祭祀殿堂)。我国古代遗址、遗产、文物中的符号、造型也是“方圆”形制(如文物“琮”)。2.行政区划和管理体制。“中央/地方”形成了一套特有的政治管理体系,它既是帝国疆域形貌,也形成了中国传统“一点四方”的行政区划——“一点”为中,中心、中央、中原、中州,乃至中国、中华皆缘此而出,“四方”为“东西南北”方位,不啻为一个政治地理学的形象注疏。3.地域和范围。强调帝王和“国家—家国”疆域的广大,《管子·地势》有云:“桀、纣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地方甚大”。4.地缘管理和地方首长。“地方”既可指某一特殊的可计量区域,也指特定地区内的管理体系和“地方官”,所以,“地方”间或指称地方的管理者。5.语用的多义性。在语言使用上,“地方”一般指某一个具体的地理范围,作名词,但它亦可用于形容词、副词甚至动词,如“地,方××里”等。 中国有着丰富的地理志,也有着悠久的地理知识谱系,包括知识分类、地理叙事和重大的地理工程;然而,中国却没有地理科学——指地理学的独立学科,但并不意味着中国人没有地理知识,没有自己的地理价值系统,没有自己的地理观。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国家—家国”与“天下”观、“一点四方”方位律制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天下体系”。[3]就“华夏秩序”而言,“地理”带有想象色彩;一方面,它历史地表现出符合帝国“有土无疆”的天下抱负;另一方面,地理成了中国式知识建构的叙事学传统——“实从理用”。钱穆在《古史地理论丛》一书的开章篇“周初地理考”说:“周人起于晋,而旧误以为在秦,故言周初地理者纷岐无定说。”[4]中国古代地理之误有三:1.来自于对地理客观上的无知。2.对于“华夏中心”和“大一统”的坚持与固守。3.过分相信史籍的记录,尤其是司马迁的《史记》。梁漱溟先生公然称:“司马迁《史记》多不可信。”[5]以笔者之见,根本原因是以现代西方自然地理的知识体制观照中国古代的政治地理形制所产生的隔阂和误解。 我国的地理表述的另一个特点是:人群与地缘的结合成为区分“我群/他群”的一道识别边界。“华夷之辨”(区域和方位人群)嵌入华夏传统叙事中最为重要的历史认同。中国式的“地方”为人类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有实感的依据;其中被学界称之为“乡土社会”的尤有特色。乡土社会的根本属性是土地。依笔者管见,要理解中国乡土社会的本质特点,“社”与“祖”为两个关键词。前者表示人与土地“捆绑关系”的发生形貌;它历史地延伸出社稷、社会、社群、社祭等。后者则表明土地人群在生殖、生产、传承观念上的期盼和行为上的照相;它延伸出祖国、祖宗、祖庙、祖产等土地伦理的意群构造。而这一根本属性与“地方人群”紧密结合,形成重要的历史结构,也是所谓“地方性力量”的根本动力。因此,要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明,“地方”是一把钥匙,中华文明的千年史就是地方的文明史;而诸如“中央/地方”等都是在此之上建立起来的政治、历史、人群和地缘的关系链条。 西方则不同。在古希腊的文字里面,Ethics[即后来作为“人种(学)”、“人类(学)”、“民族(学)”、“族群”等词汇的原始词根]被亚里士多德用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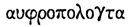
,意指“人的言说”和“人的待遇”。人类学一词从一开始便具有叙述的意义,具有人类心理和体质两方面的意涵。[6]人类学研究的视野与其说是“人类的”,还不如说是“民族”和“族群”的叙事,因为确认人类的基本单位为民族与族群,族群(人群共同体);无怪乎人类学家在做田野调查的时候非常重视分析单位,如民族、族群以及它们的历史空间和居落形态——村落、社区之间的同质性与异质性的选择。不过,从学科性质看,西方的地理谱系有自己的叙事传统——“理从实来”。“西学东渐”使两种知识和叙事传统相遇,并成了近代科学的“中国式变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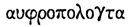 ,意指“人的言说”和“人的待遇”。人类学一词从一开始便具有叙述的意义,具有人类心理和体质两方面的意涵。[6]人类学研究的视野与其说是“人类的”,还不如说是“民族”和“族群”的叙事,因为确认人类的基本单位为民族与族群,族群(人群共同体);无怪乎人类学家在做田野调查的时候非常重视分析单位,如民族、族群以及它们的历史空间和居落形态——村落、社区之间的同质性与异质性的选择。不过,从学科性质看,西方的地理谱系有自己的叙事传统——“理从实来”。“西学东渐”使两种知识和叙事传统相遇,并成了近代科学的“中国式变体”。
,意指“人的言说”和“人的待遇”。人类学一词从一开始便具有叙述的意义,具有人类心理和体质两方面的意涵。[6]人类学研究的视野与其说是“人类的”,还不如说是“民族”和“族群”的叙事,因为确认人类的基本单位为民族与族群,族群(人群共同体);无怪乎人类学家在做田野调查的时候非常重视分析单位,如民族、族群以及它们的历史空间和居落形态——村落、社区之间的同质性与异质性的选择。不过,从学科性质看,西方的地理谱系有自己的叙事传统——“理从实来”。“西学东渐”使两种知识和叙事传统相遇,并成了近代科学的“中国式变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