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图书馆机构用户,欢迎您!
 传明陈继儒达摩渡江图
传明陈继儒达摩渡江图  明孙克弘达摩渡江图 中国古代的一些书画作品,在流传的过程中,由于某些政治或经济方面的原因,常有把原作者的名款隐去,而人为地变成佚名或他人作品的情况。这对于古代书画的收藏和研究,都是需要澄清的问题。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达摩渡江图》轴,历来被认为是明代陈继儒的作品。但从题材及绘画的技巧等方面来考察,它都不太可能出自陈继儒的手笔,而很可能是一件割掉了原作者名款的托名之作。 《达摩渡江图》,纸本设色,纵103.8、横28.5厘米。画面描绘达摩朱衣赤足,脚踩芦苇渡江情形。上部有陈继儒题:“一苇渡江,九年面壁,开口露门,广群生泽。眉公。”下钤“陈氏继儒”朱文方印。另有:“鬻饭头”、“曾为梦安李氏收藏”、“阿閦鞞室供养”朱文鉴藏印三方。画幅本身没有作者的名款。前人将此画归在陈继儒的名下,可能是因为画上有陈题的缘故。 从艺术的角度考察,整个画幅的内容虽极简单,却极具特色。画中达摩短而硬的须发,紧蹙眉头下的一双环眼,表现了明显的种族特点。微仰的头部,紧闭的双唇,又凸现出人物性格中对“某种信仰坚定姿态”的主题。画面设色单纯明快,线条简练富于表现力。诸如此类,都说明作品应出自一位有熟练绘画技巧画家的手笔。而陈继儒在绘画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是一个典型的文人画家,并不擅长人物画,也缺少职业画家的艺术技巧。 陈继儒(1558—1639),字仲醇,一字眉公,号靡公,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幼颖异,能文章,很为同郡大学士徐阶器重。长为诸生,与董其昌齐名。二十九岁时,取儒衣冠尽焚弃之,结庐在昆山之阳,后隐居在东佘山。一生布衣,专心研究学问,编书著述,于诸子百家靡不精讨。工诗文,虽短翰小词均极风致。善书法,得苏米神韵。陈继儒文艺方面的成就,很为时人所重。三吴名士争与为友,黄道周在给皇帝的上疏中也有:“志向高雅,博学多通,不如继儒”之语。
明孙克弘达摩渡江图 中国古代的一些书画作品,在流传的过程中,由于某些政治或经济方面的原因,常有把原作者的名款隐去,而人为地变成佚名或他人作品的情况。这对于古代书画的收藏和研究,都是需要澄清的问题。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达摩渡江图》轴,历来被认为是明代陈继儒的作品。但从题材及绘画的技巧等方面来考察,它都不太可能出自陈继儒的手笔,而很可能是一件割掉了原作者名款的托名之作。 《达摩渡江图》,纸本设色,纵103.8、横28.5厘米。画面描绘达摩朱衣赤足,脚踩芦苇渡江情形。上部有陈继儒题:“一苇渡江,九年面壁,开口露门,广群生泽。眉公。”下钤“陈氏继儒”朱文方印。另有:“鬻饭头”、“曾为梦安李氏收藏”、“阿閦鞞室供养”朱文鉴藏印三方。画幅本身没有作者的名款。前人将此画归在陈继儒的名下,可能是因为画上有陈题的缘故。 从艺术的角度考察,整个画幅的内容虽极简单,却极具特色。画中达摩短而硬的须发,紧蹙眉头下的一双环眼,表现了明显的种族特点。微仰的头部,紧闭的双唇,又凸现出人物性格中对“某种信仰坚定姿态”的主题。画面设色单纯明快,线条简练富于表现力。诸如此类,都说明作品应出自一位有熟练绘画技巧画家的手笔。而陈继儒在绘画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是一个典型的文人画家,并不擅长人物画,也缺少职业画家的艺术技巧。 陈继儒(1558—1639),字仲醇,一字眉公,号靡公,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幼颖异,能文章,很为同郡大学士徐阶器重。长为诸生,与董其昌齐名。二十九岁时,取儒衣冠尽焚弃之,结庐在昆山之阳,后隐居在东佘山。一生布衣,专心研究学问,编书著述,于诸子百家靡不精讨。工诗文,虽短翰小词均极风致。善书法,得苏米神韵。陈继儒文艺方面的成就,很为时人所重。三吴名士争与为友,黄道周在给皇帝的上疏中也有:“志向高雅,博学多通,不如继儒”之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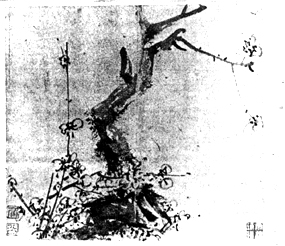 明陈继儒墨梅 关于陈继儒绘画的成就和造诣,画史上多有记载:“善写水墨梅花,即其制创,无不堪垂后世也。”(《图绘宝鉴·续纂·卷一》)“画山水涉笔草草,苍老秀逸,不落吴下画师恬俗魔境。”(《明画录·卷四》)从现在存世的陈氏作品来看,大致也是上述所记的墨梅、山水两类作品。一般认为墨梅一类的作品,多属于陈氏的亲笔,数量较多,风格较为一致,多取卷、册的形式,轴式较少。所作墨梅往往不太注重枝干的肌理描绘,多以倔强生拙的笔法画出,枝干曲折的地方,棱角较多。这个特点与其书法的笔法非常一致,气格遒朗苍逸,是典型的文人墨戏遣兴式作品。
明陈继儒墨梅 关于陈继儒绘画的成就和造诣,画史上多有记载:“善写水墨梅花,即其制创,无不堪垂后世也。”(《图绘宝鉴·续纂·卷一》)“画山水涉笔草草,苍老秀逸,不落吴下画师恬俗魔境。”(《明画录·卷四》)从现在存世的陈氏作品来看,大致也是上述所记的墨梅、山水两类作品。一般认为墨梅一类的作品,多属于陈氏的亲笔,数量较多,风格较为一致,多取卷、册的形式,轴式较少。所作墨梅往往不太注重枝干的肌理描绘,多以倔强生拙的笔法画出,枝干曲折的地方,棱角较多。这个特点与其书法的笔法非常一致,气格遒朗苍逸,是典型的文人墨戏遣兴式作品。  明陈继儒款印 至于山水画一类,情况比较复杂,风格面貌较多,笔法也各有差异。共同的特点是职业画家的技巧都比较明显,工能而淹润,与墨梅的笔法、格调毫无共通之处。徐邦达先生认为这些作品大都属当时苏松一带的画家赵左、沈士充等人代作。他进一步指出:“看样子陈氏根本不会画山水,所以陈款的山水画,尽出他人之手。”(徐邦达:《古书画考辨》下册) 在理论方面,陈继儒与董其昌的艺术见解最为接近,是董氏“南北宗”理论的有力支持者。陈、董二人友谊最深。各方面的学养、艺术造诣最为接近,经常在一起论书论画,共同游览、访友,议论如出一口。有的研究者甚至认为“南北宗的创立和传播,是他们(董陈)共同的功劳”。陈氏的一些言论,也表明了崇尚南宗文人画的倾向。他曾说:“儒家作画,如范鸱夷(蠡)三致千金,意不在此,聊示伎俩。又如陶元亮(潜)入远公社,意不在禅,小破俗耳。若色色相当,便与富翁俗僧无异。”董其昌对陈继儒的作画态度也作过描述:“眉公胸中素具一丘壑,虽草草泼墨,而一种苍者之气,岂落吴下画师恬俗魔境。” 通过上述介绍,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陈继儒在绘画理论和实践方面,表现了典型的文人画倾向和趣味。创作题材比较狭窄,只局限在墨梅一隅,山水画多为他人代作,更没有擅长人物画的记载。因此,从题材和技巧二方面,都可以说明《达摩渡江图》不可能出自陈继儒的亲笔。 在排除了《达摩渡江图》为陈氏画作之后,该图究竟出自何人的手笔,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晚明时期,在文人士大夫之间,“禅悦”之风十分盛行,影响了当时绘画的题材取向,达摩作为中土禅宗的始祖,多见于当时画家的创作中。陈继儒的画家朋友中,擅长画宗教人物的就有好几位,陈氏也很喜欢在他们的作品上题字、作偈语,《达摩渡江图》应是这类作品中的一件。就画作的风格特点而言,与孙克弘、宋旭同类题材的作品都比较接近,笔者认为孙克弘作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孙克弘(1533—1611)字允执,号雪居,和陈继儒同为华亭人,曾官汉阳太守。工书,善画山水、花卉、竹石、仙佛像。其绘画的特点是工谨、写意风格的作品兼擅,技法也在行、隶之间。孙氏现存的一些宗教人物作品,如《寒山拾得像》、《达摩渡江图》都有陈继儒的题字,说明二人艺事交往的密切。其中《达摩渡江图》无论在内容和笔墨形式上均与故宫收藏的同名作品如出一辙。
明陈继儒款印 至于山水画一类,情况比较复杂,风格面貌较多,笔法也各有差异。共同的特点是职业画家的技巧都比较明显,工能而淹润,与墨梅的笔法、格调毫无共通之处。徐邦达先生认为这些作品大都属当时苏松一带的画家赵左、沈士充等人代作。他进一步指出:“看样子陈氏根本不会画山水,所以陈款的山水画,尽出他人之手。”(徐邦达:《古书画考辨》下册) 在理论方面,陈继儒与董其昌的艺术见解最为接近,是董氏“南北宗”理论的有力支持者。陈、董二人友谊最深。各方面的学养、艺术造诣最为接近,经常在一起论书论画,共同游览、访友,议论如出一口。有的研究者甚至认为“南北宗的创立和传播,是他们(董陈)共同的功劳”。陈氏的一些言论,也表明了崇尚南宗文人画的倾向。他曾说:“儒家作画,如范鸱夷(蠡)三致千金,意不在此,聊示伎俩。又如陶元亮(潜)入远公社,意不在禅,小破俗耳。若色色相当,便与富翁俗僧无异。”董其昌对陈继儒的作画态度也作过描述:“眉公胸中素具一丘壑,虽草草泼墨,而一种苍者之气,岂落吴下画师恬俗魔境。” 通过上述介绍,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陈继儒在绘画理论和实践方面,表现了典型的文人画倾向和趣味。创作题材比较狭窄,只局限在墨梅一隅,山水画多为他人代作,更没有擅长人物画的记载。因此,从题材和技巧二方面,都可以说明《达摩渡江图》不可能出自陈继儒的亲笔。 在排除了《达摩渡江图》为陈氏画作之后,该图究竟出自何人的手笔,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晚明时期,在文人士大夫之间,“禅悦”之风十分盛行,影响了当时绘画的题材取向,达摩作为中土禅宗的始祖,多见于当时画家的创作中。陈继儒的画家朋友中,擅长画宗教人物的就有好几位,陈氏也很喜欢在他们的作品上题字、作偈语,《达摩渡江图》应是这类作品中的一件。就画作的风格特点而言,与孙克弘、宋旭同类题材的作品都比较接近,笔者认为孙克弘作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孙克弘(1533—1611)字允执,号雪居,和陈继儒同为华亭人,曾官汉阳太守。工书,善画山水、花卉、竹石、仙佛像。其绘画的特点是工谨、写意风格的作品兼擅,技法也在行、隶之间。孙氏现存的一些宗教人物作品,如《寒山拾得像》、《达摩渡江图》都有陈继儒的题字,说明二人艺事交往的密切。其中《达摩渡江图》无论在内容和笔墨形式上均与故宫收藏的同名作品如出一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