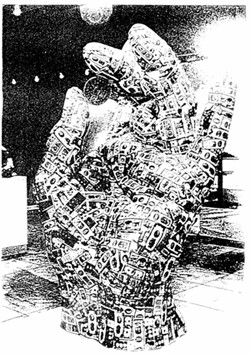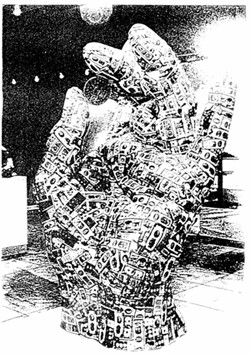艺术家的文化身份 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中,文化身份有着特定的意识形态的含义。这是因为任何一种身份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必定是某个特定社会身份系统中的一分子。它的意义取决于它与这个身份系统中其它部分的关系。而文化身份系统是和政治社会制度、文化结构、历史传统等等因素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文化身份是一种意识形态性的定位,是具体阶级、阶层、群体、职业的结构标志,反映了阿尔都塞所说的统治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体之间的召唤关系。 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艺术家对自我身份的确认不是自己自由意志的体现,而是政府指派的,具有强烈的“阶级”与“血统”特征。艺术家的“我”,是一个在国家意识形态秩序中已被排定了的分子(如工、农、商、学、兵,知识分子是臭老九),这个秩序已经替他回答了“我是谁”这个问题。在艺术“思想”和艺术“立场”上与政治意识形态保持高度的一致性,就是他确定身份的标志。作为艺术家,他自己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完全不存在的,或者是全然无关紧要的。如果他拒绝这个秩序为他预先设置的回答和早已派定的身份,他就会沦入一种实质的死亡(右派或反革命)——被剥夺了艺术身份的死亡。 80年代,在改革开放的社会情境中,政治话语长期规定的“阶级分析”对自我身份的确认逐渐失去了阐释能力,一些具有现代意识的艺术家开始追求自己的“我”的身份,不仅认认真真地想要知道“我是谁”,而且有意识地去建构这个“我”的身份,企望突破现成大秩序的禁锢,去设置“我”自己。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社会的来临,中国艺术家的社会身份认同开始出现前所未有的建构性、流动性和变化性,也就是说,具有某种前所未有的“自由性”。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出现了“体制内”的画家(在大专院校、美协、画院等政府单位任职,拿政府津贴,享受各种政府福利的艺术工作者)与“体制外”的画家(没有稳定的社会工作和工资收入,没有各种政府福利,靠出售自己的作品和其他收入来维系生活,具有流动性特征,处于官方主流话语“边缘”的职业艺术家)。这两种艺术身份的出现,是身份建构性、流动性和变化性的一种突出表现。也是身份认同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换的一个必然现象。 都普利斯(P.du Preez)在《身份的政治》一书中曾指出,政治确立和维护某种身份系统,是为了使社会的某一部分比其余的部分获得较优越的地位。一方面,政治力量(民族的、国家的、党派的等等)要为它的主要或全部成员争取比其它群体更优越的地位;另一方面,在同一政治群体中,某些身份又比其它身份更优越。体制内艺术家作为这种身份政治的一种表现,“我”的身份与政治政治意识形态对社会的控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与政府意识形态的高度一致性仍然是他们确定和维持身份系统的主要力量。这就决定了他们的艺术创作,无论是在题材的选择还是在语言的表现上,都要符合政府意识形态的主旋律。而政府为了鼓励他们的合作,使他们更能与政府同心同德,更好地为自己所主张的政治意识形态服务,也给这些艺术家某种程度的社会特权和社会地位,给予其政治、经济、文化的社会身份,并将其与职称、职位、住房、稳定的工资收入联系在一起,有意识地运用身份来满足他们的自尊原则。尽管这些艺术家仍然处于权力的边缘,自我身份的建构仍然框范在一定的意识形态的范围之内,艺术创作在一定程度仍受政治中心话语霸权“不自由性”的限制,但他们所处的政府体制内的社会身份,保障了他们在艺术世界中占据主流的位置。教授、一级美术师等头衔使他们在大众心目中具有权威的效应,有着广泛的社会认同的心理趋势,也使他们的作品在市场流通过程中可以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贡布里希在《名利场逻辑》一文中将一个人与社会制度的各种联系(如国家、政府、市场等集合体)视之为“情境逻辑”。这种情境逻辑的作用,使体制内艺术家自觉自愿地与政府政治意识形态合作,以主流艺术家的身份,保证自己顺利地在名利场中获取到某种利益。故而,体制内的艺术家在身份权力的感觉上往往比体制外的艺术家呈现出更多的优越感。 体制外艺术家的身份较为复杂。围绕这部分“职业艺术家”身份的讨论,我们要追问以下两个基本问题:第一,作为“职业艺术家”,他们逸出现存的国家艺术体制的应有意义及实际真相与结果到底如何?第二,在既存的国家艺术体制尚且强大的背景之下,其所享受的自由能有多少? 从艺术的自律性来说,应当承认,艺术家对于高度整一化的国家体制的疏离在某种意义上是实现艺术自律的重要条件,艺术创作只有真正由“国家”意识转入“社会”意识才有可能形成艺术上的真正自由。因此,当下中国的“职业艺术家”逸出体制便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但在实际上,这些“职业艺术家”逸出体制的动因是非常复杂的。有一部分艺术家自愿选择边缘地位,是出于对中心政治意识形态语话霸权的疏离,是一种对自我精神存在状态的根本调整。他们的作品更多地表现为对人的自身、人的生存状态、对艺术自身的一种更为激进的追问与思索,艺术表现形式常常具有实验性。因此,他们的创作往往被称之为先锋艺术或前卫艺术,他们的这种前卫性或先锋性往往是“他者”的眼光,即西方的价值标准和审美理念的产物,在脱离政府现行体制,追求艺术自由性的表皮下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呈现出一种对西方意识形态的媚俗。实际上,他们的文化策略是一种身份策略,是以西方中心主义来为自我身份的建构增势。他们自我增势的基本策略不是对政府意识形态的中心地位直接质疑和挑战,而是把政府和自己放到同样的“弱势”地位上,利用了一个无所不在的、神秘莫测的“西方”,通过强调另一种中心/边缘(西方/东方)的冲突来为自己增势。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政治波普,90年代末的一些血腥的行为艺术等等。他们强化自己游离于政府意识形态中心话语的“另类”角色效应,这种角色效应给他们带来了名利的双重受益。首先,他们的行为符合了西方政治意识形态的某种需要,符合了“西方价值”的某种准绳。由于西方政治意识形态的“青睐”,相对于中国政府体制内的艺术家而言,他们的作品在西方更有市场。反过来,由于国内太急于中国艺术“走向世界”,他们在国外的“成功”,也使其身份在国内愈为彰显。其次,这种西方的“青睐”使一部分职业艺术家实现了他们的“经济自立”,买车买房,有自己的市场经济人,成为国内的艺术新贵。这种状况实质上已成为他们艺术自律主张的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