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图书馆机构用户,欢迎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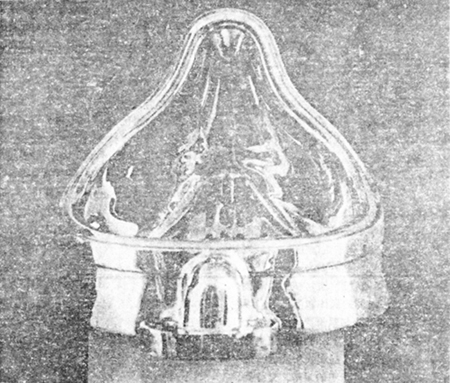 “泉”(杜桑之后)1981-87年 谢里·莱文 80年代初期,一些被认为是新表现主义的艺术家,如朱利安·施纳贝尔在某种程度上已不再美化所使用的物体。他使物体非神秘化,除去了它包含的大部分政治和社会意义,否定它的魅力甚至降低它的趣味,用一种新的、不造作的品行取代了早期物体的才智和奇想。象《海洋》(1981)就是一个代表性的例子,施纳贝尔将陶瓷碎片分散放置;就如对观众的一次袭击,尽管它们是未加工的,但这些作用于一个抽象画面之上的碎瓷片,在某种程度上使人联想到波洛克那些引人注意的、无所不在的意象。象许多追随波洛克的艺术家一样,施纳贝尔似乎不仅被这些意象,而且尤其被倾泻颜料的过程和材料所呈现的立体效果所吸引。他更新了类似于劳申伯和约翰斯的形式关系,将搬用的物体与油画底面相对照(强烈与柔和的对比)、物体的堆积与大面积的色彩块面相对比。这件富于动势的作品,通过碎瓷片与画面的对比,使一块位于画面底部、与观众脚部平行的浮木产生在水中波动的效果。在这里,与这一时期的许多作品一样,拾来的或搬用的物体不再一定是象征的,也不通过与其他物体或形象的结合来增加其感染力。因此,施纳贝尔并置物体的手法就瓦解了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力求寻找的那种艺术与隐喻关系的一般术语。他主张代之以一种更新的、渐增的比喻,叙述或不叙述的,只是基于艺术家对物体的选择。 和许多后来的表现主义艺术家一样,施纳贝尔直接地借助于历史。但与同时期的欧洲艺术家安塞尔姆·基弗不一样,后者的作品既有宏大的历史场面,又包含着对当今主要的重大问题的审视;而前者对历史的搬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典型的美国式的:他建立一种涉及历史事件的方式时缺乏欧洲同伴对历史的共鸣。对历史的天然直觉伴随着对层层相叠的时代的认识,即使在最极端的欧洲前卫派那儿都是最根本的观念。相反,施纳贝尔强调一种恢宏的观念和一种介于冲突双方之间的物质性。在他的作品中,文化和历史轻而易举地介入了现实,并带有一种压倒一切的,常常是不设防的、诡诈的直接性。 70年代后期,一些英国的雕塑家;如著名的托尼·克拉格开始把废弃物的形式转入极少主义的框架中。他创作的给人深刻印象的、形式统一的作品,常常是用色彩丰富的废塑料碎片,通过将其放置于墙面或地面进行排列组合来完成的。他借助那些各种各样的局部创作的形象,是象征的,也是抽象的,都富于一种让人联想到波普艺术的幽默。从这些集合物中,他分析出许多形状,把它们简化和扩大为强有力的雕塑形式。虽然这些后来完成的作品的每一部分都是独立存在的雕塑,但其形状都与他早期作品中的局部、普通物体的碎片有关。他借助于这个本质上为平面的形式创造了一个立体空间。他的这件作品的更大意义是他那种抓住了拾来物体的本质和赋予它的原型以一种不同平常的地位,而使它被永久纪念和推崇的才能,同时又没有失去他最初观念中必要的诙谐成分。于是,克拉格掌握了一种几乎是不可能的技艺——将即使是最重要的极少主义形式视为微不足道。
“泉”(杜桑之后)1981-87年 谢里·莱文 80年代初期,一些被认为是新表现主义的艺术家,如朱利安·施纳贝尔在某种程度上已不再美化所使用的物体。他使物体非神秘化,除去了它包含的大部分政治和社会意义,否定它的魅力甚至降低它的趣味,用一种新的、不造作的品行取代了早期物体的才智和奇想。象《海洋》(1981)就是一个代表性的例子,施纳贝尔将陶瓷碎片分散放置;就如对观众的一次袭击,尽管它们是未加工的,但这些作用于一个抽象画面之上的碎瓷片,在某种程度上使人联想到波洛克那些引人注意的、无所不在的意象。象许多追随波洛克的艺术家一样,施纳贝尔似乎不仅被这些意象,而且尤其被倾泻颜料的过程和材料所呈现的立体效果所吸引。他更新了类似于劳申伯和约翰斯的形式关系,将搬用的物体与油画底面相对照(强烈与柔和的对比)、物体的堆积与大面积的色彩块面相对比。这件富于动势的作品,通过碎瓷片与画面的对比,使一块位于画面底部、与观众脚部平行的浮木产生在水中波动的效果。在这里,与这一时期的许多作品一样,拾来的或搬用的物体不再一定是象征的,也不通过与其他物体或形象的结合来增加其感染力。因此,施纳贝尔并置物体的手法就瓦解了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力求寻找的那种艺术与隐喻关系的一般术语。他主张代之以一种更新的、渐增的比喻,叙述或不叙述的,只是基于艺术家对物体的选择。 和许多后来的表现主义艺术家一样,施纳贝尔直接地借助于历史。但与同时期的欧洲艺术家安塞尔姆·基弗不一样,后者的作品既有宏大的历史场面,又包含着对当今主要的重大问题的审视;而前者对历史的搬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典型的美国式的:他建立一种涉及历史事件的方式时缺乏欧洲同伴对历史的共鸣。对历史的天然直觉伴随着对层层相叠的时代的认识,即使在最极端的欧洲前卫派那儿都是最根本的观念。相反,施纳贝尔强调一种恢宏的观念和一种介于冲突双方之间的物质性。在他的作品中,文化和历史轻而易举地介入了现实,并带有一种压倒一切的,常常是不设防的、诡诈的直接性。 70年代后期,一些英国的雕塑家;如著名的托尼·克拉格开始把废弃物的形式转入极少主义的框架中。他创作的给人深刻印象的、形式统一的作品,常常是用色彩丰富的废塑料碎片,通过将其放置于墙面或地面进行排列组合来完成的。他借助那些各种各样的局部创作的形象,是象征的,也是抽象的,都富于一种让人联想到波普艺术的幽默。从这些集合物中,他分析出许多形状,把它们简化和扩大为强有力的雕塑形式。虽然这些后来完成的作品的每一部分都是独立存在的雕塑,但其形状都与他早期作品中的局部、普通物体的碎片有关。他借助于这个本质上为平面的形式创造了一个立体空间。他的这件作品的更大意义是他那种抓住了拾来物体的本质和赋予它的原型以一种不同平常的地位,而使它被永久纪念和推崇的才能,同时又没有失去他最初观念中必要的诙谐成分。于是,克拉格掌握了一种几乎是不可能的技艺——将即使是最重要的极少主义形式视为微不足道。  进化的恐惧 1988-89年 戴维·沃杰纳罗威奇 与新观念主义有关的艺术家也同样把形式因素重新引入所搬用的物体中,他们回到60年代对用户至上主义及大众媒介物的迷恋中,物体压倒了一切。或从大众文化中选取主题,而且关注于标准化的商品模式中的现有物体。例如,杰夫·库恩斯就在诸如《新型的、可变换的真空吸尘器,新型的谢尔顿干湿双层过滤器》(1981-87)中,使用了庸俗浅薄的媒体和演示了广泛蔓延的用户至上主义的观点。他赞同沃霍尔赋予产品永久纪念意义的观点,但与沃霍尔创作的无主题的人像不同,他的焦点是观众对社会过度行为的副产品——操作、自我膨胀和虚伪的关注。他对个别物体和其包装的选择来自广告中的策略。交替吸收了绘画及雕塑上的形式因素。
进化的恐惧 1988-89年 戴维·沃杰纳罗威奇 与新观念主义有关的艺术家也同样把形式因素重新引入所搬用的物体中,他们回到60年代对用户至上主义及大众媒介物的迷恋中,物体压倒了一切。或从大众文化中选取主题,而且关注于标准化的商品模式中的现有物体。例如,杰夫·库恩斯就在诸如《新型的、可变换的真空吸尘器,新型的谢尔顿干湿双层过滤器》(1981-87)中,使用了庸俗浅薄的媒体和演示了广泛蔓延的用户至上主义的观点。他赞同沃霍尔赋予产品永久纪念意义的观点,但与沃霍尔创作的无主题的人像不同,他的焦点是观众对社会过度行为的副产品——操作、自我膨胀和虚伪的关注。他对个别物体和其包装的选择来自广告中的策略。交替吸收了绘画及雕塑上的形式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