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图书馆机构用户,欢迎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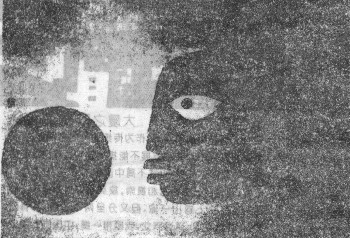 日、月、人/肖惠祥 传统中国画发展到杨州八怪、上海画派以及近现代的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等,除了在题材上不断有新的拓展之外,观念和笔墨大体依旧。传统仍是画家们孜孜以求的东西。故有的批评家管他们叫延续型大师,也有的往好里说:借古开今。事实告诉我们,传统的博大精深,消解了不少曾初露端倪的革命性,滋长了类似徐悲鸿用素描体系改良中国画笔墨的折衷性实践。然而,就是这样放脚式的改革,徐悲鸿还要挨顶着“摧残中国画”的帽子遭到传统捍卫者的猛烈抨击。时过境迁,中国画的面貌何止渗入素描因素,现如今许多旁门左道的观念、材料、风格、手法均大胆与中国画融和,传统的“笔精墨妙”、“书卷之气”也掩映其中,成了一家之木。它的独尊地位消失了。这就给中国画一方面带来喜悦,另一方面也带来尴尬。说喜悦,它给中国画的改革提示了多种新的可能,面貌也随之丰富;说尴尬,中国画的画种范围由此更难以界定。因而,在此新的情境下,我把这种虽延用传统中国画的工具材料,但又远离了中国画的笔墨特质甚至相对传统而言已面目全非的绘画叫“异样中国画”,试图将它纳入中国画的范围加以评介。 仅就语言而言,这种相异于传统的中国画,一开始基本是以色彩与素描两种倾向为主的融和样式出现。林风眠凭借他良好的油画色彩修养,在传统的观念与手法里游刃有余;徐悲鸿和蒋兆和则把素描的明暗体系用以改造传统人物画,复兴了曾一度冷落的国画人物画的热情,也别开天地。不过,步子跨得较大又能蕴含中国人文精神以及现代艺术神采的,应该说是林风眠,他的这种探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孤芳自赏,还曾一度遭到批判。现在这种寂寞已变为热闹,林风眠式的水粉重彩、斗方形制的样式启发了一大茬人。可能是由于色彩与笔墨的对立而导致彼此互补的缘故,林风眠的这种浓涂厚抹的异样中国画的表现手法,近十年来已演化为许多子手法(或者叫旁系手法),一时间成为中国画标新立异、革故鼎新的表率之一。不过,对林风眠艺术较为熟悉的苏天赐曾有一个观点,认为林风眠用传统国画的工具材料以及某些手法画的风景、静物,实际上是当作油画来画的,但却透出浓郁的中国艺术的情韵。黄永玉则有些相反。他的大胆调皮与过人的才气,自不待言,尤其对高丽纸画中的不规范工具、材料的随意使用,有不可低估的影响。他变异中国传统文人画的那种放肆程度是空前的,不论是工具上还是情调上,他在让你感到艺术应该能够标志当代特征的同时,绝对没有忘记传达一个中国文人的情怀,换句话说就是既有现代感又有书卷气。总之,林、黄两先生的画,代表着同一方面的两种类型,一个粗帅浓丽,一个野逸典雅;一个西学为用,一个中学为体;一个重规矩,一个野路子。 中国画的线条与墨色相对西画来说,有一个完善的体系,以致多数有志于创意新国画的画家都希望万变不离其宗,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可如今,随着实验性绘画的勃兴,那些立足现代进行创新的画家也逐步显出成果。传统的“三远”透视、规矩的“十八描”以及“墨分五彩”已不再是离不开的“宗”,相反画家愿意用那些表面传统形式以外的审美观念,把握中国人的审美情感,并且愿意在自己的作品中展现出能够象征当代的艺术风采。肖惠祥与邵飞是同属于装饰风格的两种类型。一种洋气,一种天真。肖惠祥利用排笔与宣纸的特性,掌握水墨形状的干净透明效果,在随意与经营、笔墨与非笔墨之间走空档,表面是画水墨,实际是暗渡陈仓,表现国画的现代形式转换。邵飞的大孩子世界,吸收民间艺术中类似剪纸、泥塑玩具的造型趣味,当然也少不了康定斯基的抽象图式,丝毫没有中国画的笔墨形式,更没有书卷气味,但中国民间艺术的情味却浓得化不开。这种稚拙型的还有一位丁立人先生。这位丁先生年岁也不太大,可在画中对戏的痴迷程度和返朴归真的拙劲不亚于一些同类的老先生。他用水粉重彩,妙鉴敦煌壁画中的一些涂绘手法,显得大智若愚,虽说形式上已远离了一般概念中的中国画,但受过中国艺术浸染的人,还是能从其它方面感受到中国画的亲切。 现在都时兴讲融和,而且融和的范围、分寸也越来越大。异样中国画就是一种融和。它给既成事实的中国画造成另一种或几种陌生的事实,也许你见了会感到一阵轻松,但不见得高兴,也许你觉得是一种释放,可又担心太离谱,这本身就是一种价值。毕竟他的活蹦乱跳、冲击规矩给中国画的探索提示了多种新的可能性,而且有可能形成新规矩,作为传统的一部分而存在。一种艺术形式的积淀和发展不能排斥这种运作方式。但究竟融和到何种程度,才不离中国画的分寸,没人可以告诉,只有自己去感觉和摸索。象吴冠中的油画与国画在语言手法上同出一辙,但又分呈两个轱辘,各有归宿。实在是高明。话说到此,我顺带一提:中国画的创新有融和,也有单一。单一可使画家练就深功夫、大本领,不投机取巧。过去的任伯年、齐白石以及现在正火着的“新文人画”(其中较优秀的画家)即是这种路子,他们的创新在于不以“异样”为代价。
日、月、人/肖惠祥 传统中国画发展到杨州八怪、上海画派以及近现代的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等,除了在题材上不断有新的拓展之外,观念和笔墨大体依旧。传统仍是画家们孜孜以求的东西。故有的批评家管他们叫延续型大师,也有的往好里说:借古开今。事实告诉我们,传统的博大精深,消解了不少曾初露端倪的革命性,滋长了类似徐悲鸿用素描体系改良中国画笔墨的折衷性实践。然而,就是这样放脚式的改革,徐悲鸿还要挨顶着“摧残中国画”的帽子遭到传统捍卫者的猛烈抨击。时过境迁,中国画的面貌何止渗入素描因素,现如今许多旁门左道的观念、材料、风格、手法均大胆与中国画融和,传统的“笔精墨妙”、“书卷之气”也掩映其中,成了一家之木。它的独尊地位消失了。这就给中国画一方面带来喜悦,另一方面也带来尴尬。说喜悦,它给中国画的改革提示了多种新的可能,面貌也随之丰富;说尴尬,中国画的画种范围由此更难以界定。因而,在此新的情境下,我把这种虽延用传统中国画的工具材料,但又远离了中国画的笔墨特质甚至相对传统而言已面目全非的绘画叫“异样中国画”,试图将它纳入中国画的范围加以评介。 仅就语言而言,这种相异于传统的中国画,一开始基本是以色彩与素描两种倾向为主的融和样式出现。林风眠凭借他良好的油画色彩修养,在传统的观念与手法里游刃有余;徐悲鸿和蒋兆和则把素描的明暗体系用以改造传统人物画,复兴了曾一度冷落的国画人物画的热情,也别开天地。不过,步子跨得较大又能蕴含中国人文精神以及现代艺术神采的,应该说是林风眠,他的这种探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孤芳自赏,还曾一度遭到批判。现在这种寂寞已变为热闹,林风眠式的水粉重彩、斗方形制的样式启发了一大茬人。可能是由于色彩与笔墨的对立而导致彼此互补的缘故,林风眠的这种浓涂厚抹的异样中国画的表现手法,近十年来已演化为许多子手法(或者叫旁系手法),一时间成为中国画标新立异、革故鼎新的表率之一。不过,对林风眠艺术较为熟悉的苏天赐曾有一个观点,认为林风眠用传统国画的工具材料以及某些手法画的风景、静物,实际上是当作油画来画的,但却透出浓郁的中国艺术的情韵。黄永玉则有些相反。他的大胆调皮与过人的才气,自不待言,尤其对高丽纸画中的不规范工具、材料的随意使用,有不可低估的影响。他变异中国传统文人画的那种放肆程度是空前的,不论是工具上还是情调上,他在让你感到艺术应该能够标志当代特征的同时,绝对没有忘记传达一个中国文人的情怀,换句话说就是既有现代感又有书卷气。总之,林、黄两先生的画,代表着同一方面的两种类型,一个粗帅浓丽,一个野逸典雅;一个西学为用,一个中学为体;一个重规矩,一个野路子。 中国画的线条与墨色相对西画来说,有一个完善的体系,以致多数有志于创意新国画的画家都希望万变不离其宗,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可如今,随着实验性绘画的勃兴,那些立足现代进行创新的画家也逐步显出成果。传统的“三远”透视、规矩的“十八描”以及“墨分五彩”已不再是离不开的“宗”,相反画家愿意用那些表面传统形式以外的审美观念,把握中国人的审美情感,并且愿意在自己的作品中展现出能够象征当代的艺术风采。肖惠祥与邵飞是同属于装饰风格的两种类型。一种洋气,一种天真。肖惠祥利用排笔与宣纸的特性,掌握水墨形状的干净透明效果,在随意与经营、笔墨与非笔墨之间走空档,表面是画水墨,实际是暗渡陈仓,表现国画的现代形式转换。邵飞的大孩子世界,吸收民间艺术中类似剪纸、泥塑玩具的造型趣味,当然也少不了康定斯基的抽象图式,丝毫没有中国画的笔墨形式,更没有书卷气味,但中国民间艺术的情味却浓得化不开。这种稚拙型的还有一位丁立人先生。这位丁先生年岁也不太大,可在画中对戏的痴迷程度和返朴归真的拙劲不亚于一些同类的老先生。他用水粉重彩,妙鉴敦煌壁画中的一些涂绘手法,显得大智若愚,虽说形式上已远离了一般概念中的中国画,但受过中国艺术浸染的人,还是能从其它方面感受到中国画的亲切。 现在都时兴讲融和,而且融和的范围、分寸也越来越大。异样中国画就是一种融和。它给既成事实的中国画造成另一种或几种陌生的事实,也许你见了会感到一阵轻松,但不见得高兴,也许你觉得是一种释放,可又担心太离谱,这本身就是一种价值。毕竟他的活蹦乱跳、冲击规矩给中国画的探索提示了多种新的可能性,而且有可能形成新规矩,作为传统的一部分而存在。一种艺术形式的积淀和发展不能排斥这种运作方式。但究竟融和到何种程度,才不离中国画的分寸,没人可以告诉,只有自己去感觉和摸索。象吴冠中的油画与国画在语言手法上同出一辙,但又分呈两个轱辘,各有归宿。实在是高明。话说到此,我顺带一提:中国画的创新有融和,也有单一。单一可使画家练就深功夫、大本领,不投机取巧。过去的任伯年、齐白石以及现在正火着的“新文人画”(其中较优秀的画家)即是这种路子,他们的创新在于不以“异样”为代价。  大厦之影/彦涵
大厦之影/彦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