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图书馆机构用户,欢迎您!
民族化方法谱系的形成,经历了较长的借鉴和修正过程。如果将民族化作为中国电影理论建构的方法选项,必须充分考虑跨国(境)工业、艺术本质主义、欧洲中心主义和反理论趋势对民族化方法的“污染”,确立更有效的研究路径。这要求我们既要进行知识考古,在重返历史、重释经典中,唤醒其中埋藏的民族话语;又要着眼于理论的“旅行”性,在不泛化、简化民族性的前提下,进行电影学与其他学科、中国理论和外国理论的对话比较,将古典理论的“同化”与外国理论的“调和”结合起来,在一个更广的视野内,总结中国电影多层次的“民族心理地图”。
 1922年,吉加·维尔托夫(Dziga Vertov)通过“三人小组”(The Council of Three)的声明,阐释了后来广为人知的“电影眼”(Kino-Eye)观念:“选取一个人最强壮、灵巧的手,另一个人最敏捷、有型的腿,第三个人最美丽和富有表现力的头——通过蒙太奇,我创造了一个崭新、完美的人。我是电影眼。我是机械眼。我,一台机器,向你展示只有我能看到的世界。”[1]1933年春天,鲁迅在应约为上海天马书店《创作的经验》撰写的文章中说:“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2] 这两段相隔11年的话涵义相差无几,但前者被视为“蒙太奇”思想,后者被看作“典型化”理论。知识穿越历史的纵深和地理的藩篱,所发生的这种“变异”现象,在各个学科领域比比皆是。需要追问的是:两个相近的概念究竟应该被视为哪个民族的精神遗产?新概念较之旧概念是改弦更张,还是简单的“拿来主义”?从一个术语到另一个术语、一个学说到另一个学说,这个“创新”过程究竟是典范的转移还是理论的旅行?这既涉及我们对理论生产“革命”还是“修正”的界定,也关乎民族化可否作为理论创新正确方向的判断。
1922年,吉加·维尔托夫(Dziga Vertov)通过“三人小组”(The Council of Three)的声明,阐释了后来广为人知的“电影眼”(Kino-Eye)观念:“选取一个人最强壮、灵巧的手,另一个人最敏捷、有型的腿,第三个人最美丽和富有表现力的头——通过蒙太奇,我创造了一个崭新、完美的人。我是电影眼。我是机械眼。我,一台机器,向你展示只有我能看到的世界。”[1]1933年春天,鲁迅在应约为上海天马书店《创作的经验》撰写的文章中说:“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2] 这两段相隔11年的话涵义相差无几,但前者被视为“蒙太奇”思想,后者被看作“典型化”理论。知识穿越历史的纵深和地理的藩篱,所发生的这种“变异”现象,在各个学科领域比比皆是。需要追问的是:两个相近的概念究竟应该被视为哪个民族的精神遗产?新概念较之旧概念是改弦更张,还是简单的“拿来主义”?从一个术语到另一个术语、一个学说到另一个学说,这个“创新”过程究竟是典范的转移还是理论的旅行?这既涉及我们对理论生产“革命”还是“修正”的界定,也关乎民族化可否作为理论创新正确方向的判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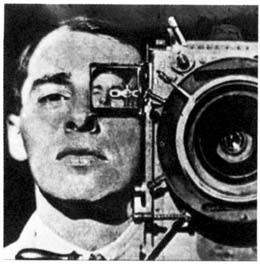 图1 苏联导演吉加·维尔托夫
图1 苏联导演吉加·维尔托夫  图2 中国作家鲁迅 一、民族化作为方法论选项 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的方法论,其理论谱系的形成常常经历漫长的模仿、借鉴和矫正过程,涵盖概念的创制、方法的演绎和框架的建构诸要素,是一个关于话语、思维和体系演变的非线性叙事。电影理论研究以本体论为核心,宗旨是引导、扩展我们对电影本性的理解,但这种理解受制于电影的媒介技术状况和地缘政治语境,是“媒介特异性”(Medium Specificity)和“文化特异性”(Cultural Specificity)两种核心冲动综合推动的结果。[3]我们不妨通过重新梳理电影理论史,让方法论层面的民族主义(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的功能与脉络更加清晰可辨。 媒介特异性是电影理论研究的起点。电影史无可避免地涉及电影与其他艺术(媒介)的竞争性定位,电影通过保存优势、淘汰劣势的自然演化机制,在历史进化中顺时应势,逐渐形成自己的质性特征。早期电影理论的重心,即区分电影与其他艺术的差异,完成电影作为一门独立艺术的合法性论证,这使20世纪20年代之前的理论带有鲜明的描述性特征和“投机性”色彩。路易·德吕克(Louis Delluc)的“上镜头性”(Photogénie)、亚历山大·阿斯楚克(Alexandre Astruc)的“摄影机笔”(Caméra-stylo)、维尔托夫的“电影眼”(Kino-Eye)、雨果·闵斯特伯格(Hugo Münsterberg)的“影戏”(Photoplay)和“电影思想论”(Cinema is Analogous to Thought)、库里肖夫(Kuleshov)的“蒙太奇”(Montage)等,以不同概念回应电影的感知过程、技术效果和表意潜力,确立了以美学和大众心理学为电影认识论的研究框架。之后约四十年间,不少艺术家对电影的媒介特异性论述作出了一系列修正,包括: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Pier Paolo Pasolini)的“流素”(也译作“流述”Rhème)、亨利·卡蒂埃·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的“期遇”(Rencontre)、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的“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安德烈·塔尔科夫斯基(Andrei Tarkovski)的“雕刻时间”(Time,Duration and Nature)等[4]。这些概念混杂着创作者的实践经验和媒介想象,目的是参与论辩、丰富认识,但理论模式均带有一定的实验色彩。20世纪60年代后,因为对挖掘电影的哲学和政治含义抱有浓厚兴趣,观众在整个电影话语链中的位置和功能受到理论家的格外关注,角色、观众、虚构、缝合、认同成为电影研究的基本概念,意识形态、权力、主体性等宏大理论开始介入电影理论生产。这是一个融合了现象学、美学、心理学、符号学和政治学的理论化时期,“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电影理论范式,是拉康的精神分析、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和罗兰巴特符号学的结合”[5]。虽然克里斯蒂安·麦茨(Christian Metz)、让·路易·博德里(Jean-Louis Baudry)、劳拉·穆尔维(Laura Mulvey)、让·皮埃尔·乌达尔(Jean-pierre Oudart)、诺埃尔·卡罗尔(Noel Carroll)等声名大噪的理论家各衔一派,但多以媒介特异性探索为中心,倾向于认为电影是一个包含从图像到观众的复杂运动,观众的心理效应是电影认知和传播的基础。
图2 中国作家鲁迅 一、民族化作为方法论选项 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的方法论,其理论谱系的形成常常经历漫长的模仿、借鉴和矫正过程,涵盖概念的创制、方法的演绎和框架的建构诸要素,是一个关于话语、思维和体系演变的非线性叙事。电影理论研究以本体论为核心,宗旨是引导、扩展我们对电影本性的理解,但这种理解受制于电影的媒介技术状况和地缘政治语境,是“媒介特异性”(Medium Specificity)和“文化特异性”(Cultural Specificity)两种核心冲动综合推动的结果。[3]我们不妨通过重新梳理电影理论史,让方法论层面的民族主义(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的功能与脉络更加清晰可辨。 媒介特异性是电影理论研究的起点。电影史无可避免地涉及电影与其他艺术(媒介)的竞争性定位,电影通过保存优势、淘汰劣势的自然演化机制,在历史进化中顺时应势,逐渐形成自己的质性特征。早期电影理论的重心,即区分电影与其他艺术的差异,完成电影作为一门独立艺术的合法性论证,这使20世纪20年代之前的理论带有鲜明的描述性特征和“投机性”色彩。路易·德吕克(Louis Delluc)的“上镜头性”(Photogénie)、亚历山大·阿斯楚克(Alexandre Astruc)的“摄影机笔”(Caméra-stylo)、维尔托夫的“电影眼”(Kino-Eye)、雨果·闵斯特伯格(Hugo Münsterberg)的“影戏”(Photoplay)和“电影思想论”(Cinema is Analogous to Thought)、库里肖夫(Kuleshov)的“蒙太奇”(Montage)等,以不同概念回应电影的感知过程、技术效果和表意潜力,确立了以美学和大众心理学为电影认识论的研究框架。之后约四十年间,不少艺术家对电影的媒介特异性论述作出了一系列修正,包括: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Pier Paolo Pasolini)的“流素”(也译作“流述”Rhème)、亨利·卡蒂埃·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的“期遇”(Rencontre)、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的“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安德烈·塔尔科夫斯基(Andrei Tarkovski)的“雕刻时间”(Time,Duration and Nature)等[4]。这些概念混杂着创作者的实践经验和媒介想象,目的是参与论辩、丰富认识,但理论模式均带有一定的实验色彩。20世纪60年代后,因为对挖掘电影的哲学和政治含义抱有浓厚兴趣,观众在整个电影话语链中的位置和功能受到理论家的格外关注,角色、观众、虚构、缝合、认同成为电影研究的基本概念,意识形态、权力、主体性等宏大理论开始介入电影理论生产。这是一个融合了现象学、美学、心理学、符号学和政治学的理论化时期,“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电影理论范式,是拉康的精神分析、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和罗兰巴特符号学的结合”[5]。虽然克里斯蒂安·麦茨(Christian Metz)、让·路易·博德里(Jean-Louis Baudry)、劳拉·穆尔维(Laura Mulvey)、让·皮埃尔·乌达尔(Jean-pierre Oudart)、诺埃尔·卡罗尔(Noel Carroll)等声名大噪的理论家各衔一派,但多以媒介特异性探索为中心,倾向于认为电影是一个包含从图像到观众的复杂运动,观众的心理效应是电影认知和传播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