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克拉考尔的“羊皮书” 迄今为止,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的《电影的本性——物质现实的复原》(Theory of Film:The Redemption of Physical Reality,以下简称《电影的本性》)仍是电影理论史上一部地位尴尬的著作。一方面,它自1960年出版后不久就被奉为经典,是涉足电影研究的人文学者无法绕过的巅峰之作;另一方面,它虽然被无数次地、反反复复地阅读,却几乎没有人能够读懂。“物质存在”“生活流”“摄影机-现实”“风吹树叶,自成波浪”等说法为人们所耳熟能详,但是内在于克拉考尔著作的何谓“现实”的理论难题,不是被过于轻忽地纳入既有的现实主义来吸收,就是被草率地当作无法自洽的概念缺陷而抛弃。就连克拉考尔的挚友阿多诺都讥刺他这方面的思想是一种“天真的现实主义”①,这在很长时间里几乎成为对他的一种定评②。 这一局面在相当程度上是由《电影的本性》中不稳定的“现实”概念造成的。表面上看,这部著作的写作目标和基本内容很直接明了,克拉考尔说,“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是深入考察照相性质的影片的真正本性”,“电影按其本质来说是照相的一次外延,因而也跟照相手段一样,跟我们的周围世界有一种显而易见的近亲性。当影片纪录和揭示物质现实时,它才成为名副其实的影片”③。克拉考尔不仅排斥电影的一切形式化实践,甚至认为电影史上的绝大部分作品都因为或多或少的人为干预特征而损害了“摄影机-现实”的非艺术品质。因此,克拉考尔是从电影的内容而非形式出发,尝试去建立一种“实体的美学”,由于照相与世界的这种近亲性,电影的本性即由作为其拍摄对象的内容所决定,电影几乎等同于它所记录和揭示的物质现实。 然而,克拉考尔之所谓“现实”并不像表面呈现的这样简单。在整部《电影的本性》中,到底何为“现实”,其实语焉不详,或者说始终存在两种不同的理解方向。一方面,它似乎被当作不言自明、无可争辩的事实存在而接受;另一方面,在与克拉考尔的真正思考连接得更为深刻的地方,它却又因为历史本身造成人类生活既有现实的毁灭和堕落而遭到拒绝。也就是说,《电影的本性》之所谓“现实”,在哲学的层面上,是有着明确的现象学视域作为理论支撑的“生活世界”(Lebenswelt)的物质现实;而在历史的层面上,又紧密关联着19世纪末以来“西方的没落”、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带给人类的空前浩劫。如果不能认识到克拉考尔是在“奥斯维辛之后”人类文明的绝境中写下这部著作的,就无法真正理解他所说的“物质现实的复原”(这里的“复原”一词为redemption,实即带有强烈宗教意味的“救赎”)究竟意味何在。《电影的本性》诚然是一部电影理论的恢弘巨著,然而若仅在电影研究的界限之内来阅读,恐怕永远无法抵达它的真义:克拉考尔的确自始至终都在谈论电影,但这是作为彼岸受到召唤的电影,而此岸的现实及其历史则被悬置。 事实上,克拉考尔的《电影的本性》只能被当作一部思想著作来阅读,它所提出的命题关乎历史,关乎电影媒介的本体论与他那个时代的人们所身处的历史维度之间的根本联系,而现实的存废就位于这一根本联系的关节处。这样一项任务与其说是体现于它所论述的内容(电影),不如说是由它的整个书写形式所决定的,准确地说,是由它的书写策略(借由“摄影机—现实”来实现的耦合)所决定的。针对《电影的本性》的这种书写策略,米里亚姆·汉森(Miriam Hansen)给出的定位颇具参考价值。她指出,克拉考尔的这部著作带有一种根本的“羊皮书性质”(palimpsestic quality)④,它不能仅仅通过其自身获得理解,而是必须被放置到庞杂的互文关联和时代语境中重读,唯其如此,才能使它不再只是作为一段过往“历史”的陈迹被束之高阁,而重新成为“我们自己的历史的一部分”⑤。汉森格外强调,《电影的本性》并不是一次成书的文本,反复书写、修订、增删使这部著作最终变成了一个体量庞大的超文本,最终付印的文字和那些被划掉、抹去的痕迹共同构成一次次复杂的难题性的展开。面对这部著作,我们不能仅限于在那些已然凝固、静止的表述中去提取意义,因为这里没有真正的一次性给定的答案,而是不得不去探寻那些从印刷的文本中消失的内容——那些被放逐出去的幽灵般的存在,最终会以某种不可预期的方式归来,到那时,由那些幽灵消失处的空白所决定、所书写的《电影的本性》,也将以一个全新的面貌回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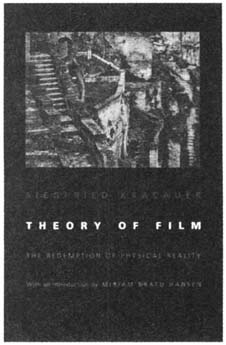
克拉考尔《电影的本性》书影 如果沿着汉森提示的“羊皮书”式的理解路径,我们不难发现,第一个提出应对《电影的本性》一书进行跨跃式阅读的,实际上就是克拉考尔本人。他在晚年不期然间觉悟到,关于“照相的方法”的讨论几乎成为贯穿他毕生思考的一条重要线索。作为思想著作的《电影的本性》,必须在与克拉考尔的身后遗作《历史:终结前的最终事》(History:The Last Thing Before the Last,1969)的对照阅读中,才能真正显现出它的意义和价值所在。而且,在克拉考尔个人的著作序列里面,《电影的本性》的核心关切也可以一直追溯到他的早期著述。在《历史:终结前的最终事》开篇,克拉考尔便坦陈: 近来我突然发现对历史的兴趣实际产生于我在《电影的本性》一书中试图思考与挖掘的一些观点。……某一瞬间我认识到,历史与摄影媒介、历史现实与摄影机现实之间存在很多相似之处。后来,我不经意间重读自己《论摄影》的小文,发现自己在20世纪20年代的这篇文章里就已经对历史主义和摄影进行了比较,这让我非常震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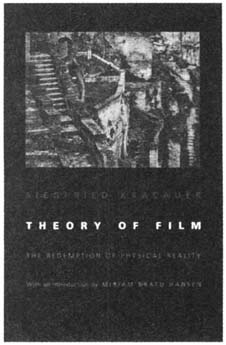 克拉考尔《电影的本性》书影 如果沿着汉森提示的“羊皮书”式的理解路径,我们不难发现,第一个提出应对《电影的本性》一书进行跨跃式阅读的,实际上就是克拉考尔本人。他在晚年不期然间觉悟到,关于“照相的方法”的讨论几乎成为贯穿他毕生思考的一条重要线索。作为思想著作的《电影的本性》,必须在与克拉考尔的身后遗作《历史:终结前的最终事》(History:The Last Thing Before the Last,1969)的对照阅读中,才能真正显现出它的意义和价值所在。而且,在克拉考尔个人的著作序列里面,《电影的本性》的核心关切也可以一直追溯到他的早期著述。在《历史:终结前的最终事》开篇,克拉考尔便坦陈: 近来我突然发现对历史的兴趣实际产生于我在《电影的本性》一书中试图思考与挖掘的一些观点。……某一瞬间我认识到,历史与摄影媒介、历史现实与摄影机现实之间存在很多相似之处。后来,我不经意间重读自己《论摄影》的小文,发现自己在20世纪20年代的这篇文章里就已经对历史主义和摄影进行了比较,这让我非常震惊。
克拉考尔《电影的本性》书影 如果沿着汉森提示的“羊皮书”式的理解路径,我们不难发现,第一个提出应对《电影的本性》一书进行跨跃式阅读的,实际上就是克拉考尔本人。他在晚年不期然间觉悟到,关于“照相的方法”的讨论几乎成为贯穿他毕生思考的一条重要线索。作为思想著作的《电影的本性》,必须在与克拉考尔的身后遗作《历史:终结前的最终事》(History:The Last Thing Before the Last,1969)的对照阅读中,才能真正显现出它的意义和价值所在。而且,在克拉考尔个人的著作序列里面,《电影的本性》的核心关切也可以一直追溯到他的早期著述。在《历史:终结前的最终事》开篇,克拉考尔便坦陈: 近来我突然发现对历史的兴趣实际产生于我在《电影的本性》一书中试图思考与挖掘的一些观点。……某一瞬间我认识到,历史与摄影媒介、历史现实与摄影机现实之间存在很多相似之处。后来,我不经意间重读自己《论摄影》的小文,发现自己在20世纪20年代的这篇文章里就已经对历史主义和摄影进行了比较,这让我非常震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