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曾一针见血地指明了机械复制对艺术之光晕(Aura)的迫害,因为复制技术,艺术品首次成为唾手可得又毫无价值的商品,“在一切写出的作品中我只喜爱一个人用血写成的东西”[1],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曾如此喟叹;而随着机械复制时代的来临,艺术品的权威性和“血性”都已经不复存在。然而,《攻壳机动队》(Ghost in the Shell,1995)、《阿丽塔:战斗天使》(Alita:Battle Angel,2019)等有关“义体人”的科幻电影作品,则带给人类更深层而强劲的刺激——若唯一的肉身变为可以无限复制的机械躯体,身上的每一个部位化作可替换的电子零件,则个体命运又会如何?无论在电影中、还是电影外,真实与虚拟、有机物与无机物、生物与机器的边界开始消失;一种后人类的、崭新的美学想象被打开,成了值得关注的议题——由机器体系所创生的技术美学,缔造了怎样的身体景观?又如何形塑了个体有关身体的意识形态? 一、青春崇拜·线条控制·完美之躯 多年前曾有传闻,一名日本少女在十六岁生日当天毅然选择自杀,她在留给家人的遗书中写道:“现在是我人生中最美丽的时刻,我不愿看到自己的美丽消逝,在这个时刻离去,为的就是留住生命中最美的时光。”这一荒谬而又充溢着痛感的自杀事件,其实隐含着一份近乎癫狂的“青春崇拜”。纵使美并不属于特定的年龄段,但迄今为止的媒介叙事却不遗余力地制造了一个关于美的时间囿限——青春即美、美即青春,美成为人生一个特定阶段的标志和产物。[2]意大利导演卢基诺·维斯康蒂(Luchino Visconti)的名作《魂断威尼斯》(Morte a Venezia,1971),亦呈现了这种“青春一衰老”的二元对立,青春被圣化为一种终极的美,超越了艺术与生死:中年失意的作曲家奥芬巴赫(Aschenbach),独自前往威尼斯度假散心,却在下榻的酒店里迷恋上了一位名为塔奇奥(Tadzio)的陌生美少年。自始至终,两人之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交流,电影中却有大量奥芬巴赫的主观镜头——他情不自禁地跟踪着塔奇奥,又幻想着和塔奇奥的对话;塔奇奥那俊美脱俗的年轻面容、优雅轻盈的少年体态,使奥芬巴赫兀自陷入了爱欲的池沼。 反观《阿丽塔:战斗天使》中的机械少女,来自失落的“火联(United Republic of Mars)”文明的阿丽塔(Alita),实际年龄早已经超过三百岁了;但电影中的她,却始终拥有着豆蔻年华的外表——吹弹可破的肌肤、娇俏的五官、纤美的身体,尤其是那漫画式的大眼睛、透着天真与活力的双眸,令人无法否认她的“青春之美”。这样“洛丽塔”(Lolita)般的角色设定,几乎带有一种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式的审美趣味——“洛为人变幻莫测,脾气暴躁,生气蓬勃,难以应付,具有活泼的十二三岁孩子的那种尖嘴薄唇的风姿,从头到脚都叫人欲火中烧”[3]。 耐人寻味之处在于,纵使是全身电子元件化的“义体人”,也不能违抗“青春”之律令,而是必须完美地、恒久地呈现出年轻的姿容。对于“义体人”而言,只要定期维护、更换身体的零件,年龄便是一个凝固的概念,他们将永远年轻下去。不难看出,通过“义体人”这一形象,一种关乎身体的“青春崇拜”,被推向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人类美少年塔奇奥终会老去、终会失去青春的光环,但“义体人”的“青春”却是牢牢固定在其身体上的。我们对于“青春之美”的认知不再具有时间囿限,而是将其扩充为一种贯穿人生的要求;这意味着,我们不止偏爱年轻人的身体之美,还命令不同年龄段的人都要努力将这种“青春之美”长久地维系在自己身上。当下的娱乐报道时常乐于夸奖明星们的“冻龄美貌”,正是如此观念作祟。“机器过程和机器环境的三个重要特征是统一性、标准化和可替换性”[4],而“通过机器体系来表达意味着承认以下较新的审美概念:精密、审慎考量、没有瑕疵、简洁、经济等”[5]。但身体的“自然衰老”意味着朽坏与非标准化,是工业社会中碍眼的瑕疵,是需要被鄙夷与拒斥的;被替换的风险因此被悬置于每个人的身体之上,使得你我不得不小心翼翼地、长久地臣服于“青春”之律令。 除了“青春崇拜”以外,还有一种对于“线条”的迷恋驻扎在我们的身体观念之中。一般而言,苗条与美丽之间并不存在天然的联系,丰满乃至肥腴的体态,亦在某些时代、某些地方颇受推崇。但是,“那种强制性的、普遍的以及大众化的美丽”[6]却是和苗条密不可分的。当代一切与身体相关的集体牵挂,实则将其构筑为“压制性关切”的对象——由“苗条即美”引发的“线条崇拜”将每个人的身体拖入一种漫长的、无止境的苛责之中,身体变成了必须根据某些美学标准来进行监护、简约、禁欲的物品;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甚至将此指认为一种势不可挡的“献祭”与“暴力”——“对线条的狂热、对苗条的痴迷是如此深刻,完全是因为这正是一种暴力形式,是因为身体本身在其中变成了祭品,同时就像在祭祀中一样达到了完美并激烈的复苏”[7]。 线条之于身体,苗条之于美丽,成了一道宗教式的绝对命令;如此观念,自然也渗透到了国内外的影视文化之中。杜琪峰导演于2001年推出了浪漫爱情喜剧片《瘦身男女》,电影中肥胖的男女主人公,在各自成功瘦身后终于相恋;无独有偶,韩国电影《丑女大翻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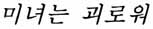
,2006)中,肥胖无比的女主人公,亦是在大幅度整容瘦身后才得到心上人的青睐。一定程度上,肥胖的、无线条的身体被不断塑造为一种“原罪”:若是不苗条,便是不美丽,甚至不能够享有爱与被爱的权利;苗条,成了一种最低准入门槛,成了现代男女体面地、有尊严地生活的资格证,成了一种身体的政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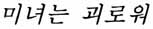 ,2006)中,肥胖无比的女主人公,亦是在大幅度整容瘦身后才得到心上人的青睐。一定程度上,肥胖的、无线条的身体被不断塑造为一种“原罪”:若是不苗条,便是不美丽,甚至不能够享有爱与被爱的权利;苗条,成了一种最低准入门槛,成了现代男女体面地、有尊严地生活的资格证,成了一种身体的政治。
,2006)中,肥胖无比的女主人公,亦是在大幅度整容瘦身后才得到心上人的青睐。一定程度上,肥胖的、无线条的身体被不断塑造为一种“原罪”:若是不苗条,便是不美丽,甚至不能够享有爱与被爱的权利;苗条,成了一种最低准入门槛,成了现代男女体面地、有尊严地生活的资格证,成了一种身体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