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电影工业的后发国家,中国电影史以外来电影的消费和接受为开端。在一个华洋杂陈的环境中观看外来电影,形成了中国观众对电影的初步认知,成为本土电影观念和电影美学建构的土壤。本文将关注舶来的活动影像作为一种新的观察技术让中国观众形成了怎样的感受和认知,这些感受和认知有着怎样的根源和意涵,以此为根基,思考本土电影美学形成的动力。 一、电影的传入与传播 中国电影史的开端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到目前为止,这样的说法已经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接受——根据《德臣西报》等中外文报纸的报道,1897年4月26日,法国人莫里斯·查维特教授(Prof.Maurice Charvet)在香港大会堂的圣安德鲁堂(St.Andrew’s Hall)用cinematagraph放映了《沙皇驾临巴黎》等短片[1][2],是电影传入香港的证据确凿的开端;1897年5月22日,哈利·威尔比库克(Harry Welby-Cook)在礼查饭店(Astor House Hotel)用号称由爱迪生发明的ainimatascope放映了《海浪拍岸》等影片,是上海有据可查的第一次电影放映。[3][4]香港大会堂和礼查饭店都是当时在华西人中的上流人士出入的地方,可见这两次放映的观众主要也是这些人。随后,电影转移到了以中国人为主的娱乐场所,而票价也在不断下降,到20世纪10年代成为大部分城市居民都能消费得起的娱乐,本土的制片也开始萌芽。 这样的描述,相比于更早的电影史研究者如程继华、余慕云等简单而缺乏论证地将“西洋影戏”“奇巧洋画”的放映视为电影传入的标志,显然深入细致了很多,也更加清晰地勾勒出了中国电影史最初时期的状态。但是,这些学者似乎同时忽略了一个本质性的问题——为什么这些放映活动能够被视为“电影的”,而“西洋影戏”“奇巧洋画”则不能?两者之间究竟差别何在?这个问题今天回答起来仍有一定的难度。首先,是因为通过简略而夸张的文字广告,我们很难确定这些所谓的“影戏”究竟是什么,与1897年放映的“电影”有多大的差别,是否大到足以形成根本性的区分。 其次,从“本质”层面界定最早期的电影,本身可能就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电影学界曾经流传着这样一种普遍的看法——作为“第七艺术”的电影,是唯一有着明确诞生日期的艺术门类。1895年12月28日,在巴黎大咖啡馆的公开放映,标志着电影的诞生;而放映了自己摄制的《火车进站》等影片的卢米埃尔兄弟,则是电影的发明人。当然,一些美国学者可能更倾向于认为,发明电影的是当时名扬天下的美国人爱迪生,并有着同样充足的理由来证明爱迪生的开创作用(如建立了最早的摄影棚“黑玛丽”[Black Maria],并先于卢米埃尔兄弟拍摄了多种影片,等等)。但是,越来越多的电影学者逐渐放弃了这样的看法。其实,早在上个世纪中叶,法国电影史家乔治·萨杜尔已经明确指出,“摄影和活动形象的发明者不是一个人,而是几十个人。如此复杂的发明是不可能单独由一个人来实现的”。[5]并在其皇皇七卷本的《电影通史》中,花费了整整一卷的篇幅,追溯了从19世纪20年代静态摄影技术萌芽到90年代各种电影技术出现的过程。而近年来,许多电影史著作也不再将电影的发明归结到某一人名下。例如,美国学者查尔斯·马瑟(Charles Musser)详细考察了17世纪以来各种投影装置(如magic lantern、fantasmagorie、stereopiticon等)的出现和流行,为爱迪生名下的vitascope所铺设的社会文化语境。①综合现有的早期电影研究成果,我们可以认为,如果单纯地从其呈现形态上来看,早期电影具有这样的特征:(1)连续、快速地摄制;(2)清晰地洗印;(3)投映为真人大小的影像;(4)匀速、稳定地放映。只有同时达到这样几个条件,才能最大程度地营造真实的幻象和运动的幻觉,从而与其他视觉娱乐形成明显的区分。但这几个条件是经过几十年时间才逐步实现的,需要不同领域的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并非一个人或一家公司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能做到。集摄、印、放于一体的cinématographe固然具备了全部上述特点,但更多是对其他产品的改良而非创新;同时,面对众多模仿者和竞争者,卢米埃尔兄弟及其代理人未能采取恰当的保护和反击措施,不能有效占领足够多的市场份额,引领电影技术的发展方向。我们当然不能说这一形制的机器被市场淘汰意味着“电影”的终结,但认为它的出现意味着电影的诞生同样不可取。至于kinetoscope、vitascope及animatascope等,虽然是由爱迪生提出的最初设想,但他并没有亲自参与研发,而是把这项工作委托给了助手迪克森(W.K.L.Dickson),而且占用了阿尔马特(Thomas Armat)、拉泰姆父子(the Lathams)等人的创意,②不但没有从无到有地“发明”电影,甚至有欺世盗名之嫌。可以说,无论是cinématographe、vitascope,还是其他以“-graph(e)”“-scope”等词缀来命名的多种技术产品,往往相互模仿乃至抄袭,彼此之间的差距并不显著。而在制造这些机器的企业当中,如爱迪生主导成立的电影专利公司(Motion Picture Patent Company)那样规模较大、掌控力较强的,则在专利保护、产权界定、胶片格式、影片租售、放映条件等方面制定出全行业的通行规则,导致电影逐渐标准化、狭义化,形成了制式统一、形态固定的电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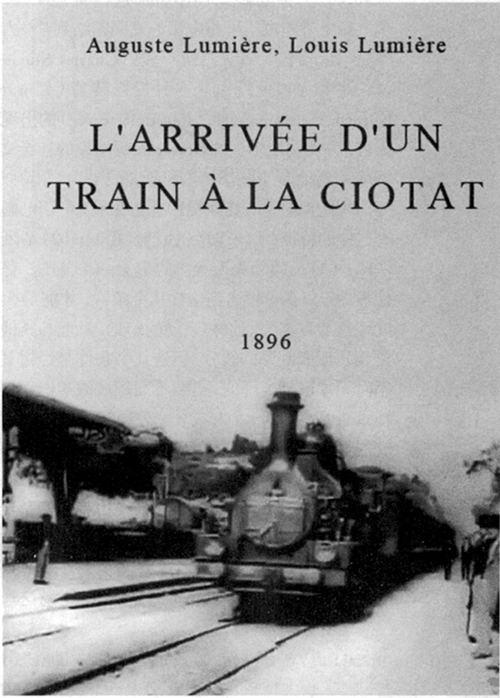
电影《火车进站》海报 一方面,可以说电影在技术、资本、市场、法律乃至个人魅力相互博弈的过程中不断演变,认为它在某一个确定的日期像一个婴儿一样“诞生”到这个世界上的修辞性说法虽然形象生动,却经不起推敲。正因为如此,萨杜尔从摄影技术发展和完善的角度,马瑟从技术普及和惯例形成的角度,论证了cinématographe和vitascope的优越性,但在承认这些技术设备标志性意义的同时,两位严谨的学者更注重它们与前后历史事件之间的延续,而避免生硬地制造断裂。另一方面,侧重点各有不同的电影史论述同时也表明,早期电影并非单数,而是复数的存在。 如果承认电影复数、渐进的形态,那么电影与之前的“影戏”之间的区分并不泾渭分明,电影及其“发明者”之间的关系也是脆弱且可疑的。我们不能以电影的“发明”为参照点来确定中国电影史的开端。更何况,根据台湾学者李道明教授研究了放映片单之后所作的推测,虽然查维特打出了cinematograph的名号,库克宣称自己的机器为爱迪生所发明,但两人所使用的很有可能并非卢米埃尔和爱迪生公司生产的正品,而分别是英国R.W.Paul和Ottway&Son公司的仿制品。[6]也就是说,即便我们承认卢米埃尔和爱迪生及其技术成果是世界电影史的起点,香港和上海这两次放映的也不是“正宗”的电影,和两位“发明者”的技术研发、商业推广之间并不存在直接关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查维特和库克放映的不是“电影”,而是说不加思辨地将他们的放映确立为电影史的开端,则割裂了电影与其形成和传播环境之间的关系,也遮蔽了他们的放映活动除了作为中国电影史开端之外的意义。如果换一种思路,反而可能为电影史论述打开更为广阔的空间——我们不妨思考,这些放映活动是在什么样的语境下进行的?这样的语境,给了观众怎样的视觉经验?这样的经验,导致他们如何理解和接受电影?这样的理解和接受,是否有鲜明的地域和时代特征?这些特征,串联起怎样的中国电影史叙述?很显然,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不能将“电影的”放映视为孤立的事件,而需要将更大范围的相关因素囊括进来,加以综合考虑和交叉对比。而对这些问题有了一定的思索之后,我们才能很好地理解电影这样一种舶来的新技术,如何与中国本土的旧眼光融合,进而成长为一门本土工业和民族艺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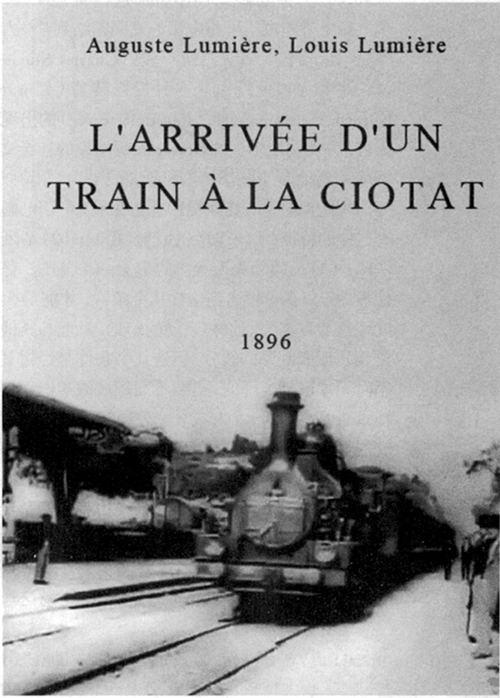 电影《火车进站》海报 一方面,可以说电影在技术、资本、市场、法律乃至个人魅力相互博弈的过程中不断演变,认为它在某一个确定的日期像一个婴儿一样“诞生”到这个世界上的修辞性说法虽然形象生动,却经不起推敲。正因为如此,萨杜尔从摄影技术发展和完善的角度,马瑟从技术普及和惯例形成的角度,论证了cinématographe和vitascope的优越性,但在承认这些技术设备标志性意义的同时,两位严谨的学者更注重它们与前后历史事件之间的延续,而避免生硬地制造断裂。另一方面,侧重点各有不同的电影史论述同时也表明,早期电影并非单数,而是复数的存在。 如果承认电影复数、渐进的形态,那么电影与之前的“影戏”之间的区分并不泾渭分明,电影及其“发明者”之间的关系也是脆弱且可疑的。我们不能以电影的“发明”为参照点来确定中国电影史的开端。更何况,根据台湾学者李道明教授研究了放映片单之后所作的推测,虽然查维特打出了cinematograph的名号,库克宣称自己的机器为爱迪生所发明,但两人所使用的很有可能并非卢米埃尔和爱迪生公司生产的正品,而分别是英国R.W.Paul和Ottway&Son公司的仿制品。[6]也就是说,即便我们承认卢米埃尔和爱迪生及其技术成果是世界电影史的起点,香港和上海这两次放映的也不是“正宗”的电影,和两位“发明者”的技术研发、商业推广之间并不存在直接关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查维特和库克放映的不是“电影”,而是说不加思辨地将他们的放映确立为电影史的开端,则割裂了电影与其形成和传播环境之间的关系,也遮蔽了他们的放映活动除了作为中国电影史开端之外的意义。如果换一种思路,反而可能为电影史论述打开更为广阔的空间——我们不妨思考,这些放映活动是在什么样的语境下进行的?这样的语境,给了观众怎样的视觉经验?这样的经验,导致他们如何理解和接受电影?这样的理解和接受,是否有鲜明的地域和时代特征?这些特征,串联起怎样的中国电影史叙述?很显然,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不能将“电影的”放映视为孤立的事件,而需要将更大范围的相关因素囊括进来,加以综合考虑和交叉对比。而对这些问题有了一定的思索之后,我们才能很好地理解电影这样一种舶来的新技术,如何与中国本土的旧眼光融合,进而成长为一门本土工业和民族艺术。
电影《火车进站》海报 一方面,可以说电影在技术、资本、市场、法律乃至个人魅力相互博弈的过程中不断演变,认为它在某一个确定的日期像一个婴儿一样“诞生”到这个世界上的修辞性说法虽然形象生动,却经不起推敲。正因为如此,萨杜尔从摄影技术发展和完善的角度,马瑟从技术普及和惯例形成的角度,论证了cinématographe和vitascope的优越性,但在承认这些技术设备标志性意义的同时,两位严谨的学者更注重它们与前后历史事件之间的延续,而避免生硬地制造断裂。另一方面,侧重点各有不同的电影史论述同时也表明,早期电影并非单数,而是复数的存在。 如果承认电影复数、渐进的形态,那么电影与之前的“影戏”之间的区分并不泾渭分明,电影及其“发明者”之间的关系也是脆弱且可疑的。我们不能以电影的“发明”为参照点来确定中国电影史的开端。更何况,根据台湾学者李道明教授研究了放映片单之后所作的推测,虽然查维特打出了cinematograph的名号,库克宣称自己的机器为爱迪生所发明,但两人所使用的很有可能并非卢米埃尔和爱迪生公司生产的正品,而分别是英国R.W.Paul和Ottway&Son公司的仿制品。[6]也就是说,即便我们承认卢米埃尔和爱迪生及其技术成果是世界电影史的起点,香港和上海这两次放映的也不是“正宗”的电影,和两位“发明者”的技术研发、商业推广之间并不存在直接关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查维特和库克放映的不是“电影”,而是说不加思辨地将他们的放映确立为电影史的开端,则割裂了电影与其形成和传播环境之间的关系,也遮蔽了他们的放映活动除了作为中国电影史开端之外的意义。如果换一种思路,反而可能为电影史论述打开更为广阔的空间——我们不妨思考,这些放映活动是在什么样的语境下进行的?这样的语境,给了观众怎样的视觉经验?这样的经验,导致他们如何理解和接受电影?这样的理解和接受,是否有鲜明的地域和时代特征?这些特征,串联起怎样的中国电影史叙述?很显然,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不能将“电影的”放映视为孤立的事件,而需要将更大范围的相关因素囊括进来,加以综合考虑和交叉对比。而对这些问题有了一定的思索之后,我们才能很好地理解电影这样一种舶来的新技术,如何与中国本土的旧眼光融合,进而成长为一门本土工业和民族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