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图书馆机构用户,欢迎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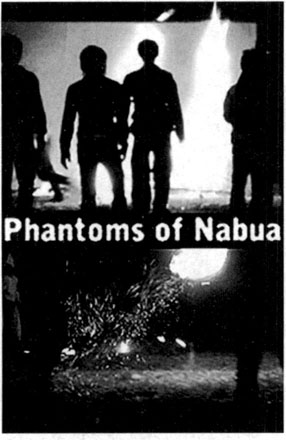 《纳布亚魅影》剧照 以上即是短片《纳布亚魅影》(Phantoms of Nabua,2009)的叙事,该片由泰国电影人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导演。对单一场景身临其境的研究,就像把日常琐事放在放大镜下,把观众带向另一个叙事时空。片中没有对话,也就没有多少理性信息。然而,我们对场景的了解均直观来自于影片中占主要成分的感官刺激。这样的手段也许是一种很“自然的”方式,哪怕短暂地,将解释电影叙事中移动影像所惯用的理性和心理分析态度摈弃一旁。然而,对诸如韦拉斯哈古的片中所包含的感官维度开放的接受能够放大我们“感同身受”与“身临其境”的体会,令我们几乎置身于场景之中。这种人与场景的亲近并不是运用本世纪初兴起的好莱坞三维技术所展示的测量意义上的沉浸感,而是依靠观众与影像之间达成的默契。在这个默契之下,强烈的情感交流就此开始。在交流中,我们的感觉与镜头记录的事件相伴而行,观察事件中每个细节的发展变化,就好像我们完全融入到了这些细节之中。 世界很多地区电影中的场景都适合用来表达这个主题。在其中一个场景中,摄像机一开始似乎是随意探进一间被废弃的印刷车间,镜头划过印刷机和其它工具,在各房间进进出出,直到停留在两个孩子身上。两个孩子开始玩游戏,镜头一直跟着他们跑过小巷、街道、树林,最后镜头停下来,像人一样,稍作休息,喘口气(《沙罗双树》[Shara],河濑直美[日本],2003)。在另外一个场景中,一个年轻人在车站专心聆听并记录声音,火车在镜头前来往穿行,摄像机一直如呼吸般微调着画面(《咖啡时光》[Café Lumière],侯孝贤[中国台湾],2003)。而在又一个场景中,观众看到的是训练中的外籍军团士兵一个接一个、不断重复的肢体动作。摄影机在拍摄这些动作时采用了最小幅度、漂浮式的移动方式,在一连串的重复后,呈现出催眠的特性,能够从一个情节延续至下一个。比如:在拍完钢索训练这个镜头之后是晾衣绳的全景镜头,绳上晾着衣服等着被沙漠风吹干(《军中禁恋》[Beau Travail],克莱尔·丹尼斯[法国],1999)。 所有的场景(和影片)都使用了一种叙事策略,在这个策略中,感官因素被视为观众审美体验的原始层面,它并不用动作和对话来解释一切,而是采用了视觉和文本模糊的基调,使观众能够探索影像中内蕴的所有感官体验。换言之,这些影片代表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视听教育——通常与影像中的视觉痕迹相关。劳拉·马克斯将此称为“触觉可视”,这可以让我们重新了解如何去观看和聆听电影,从而打破霸权电影传统(甚或是当代电影的后现代叙事解构和立体视觉冲击)长久以来加诸于观众身上的感觉麻痹。 一些电影批评家采用“心流电影”(flow cinema)或“心流美学”(flow aesthetics)来指称这种视听叙事模式,斯蒂芬·布凯2002年在《电影手册》刊发的一篇文章中创造了这两个术语。最早一批此类型的电影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拍摄的。这些电影的特点是强调人身再入日常时空,这些电影也被认为是受到视听语言影响的感官经历,其存在与被解读皆源于此。电影中既能引发不安又会带来微妙惊奇感的时间省略和视觉模糊制造了不确定性。电影中的影像和让观众彻底放松的环境组合在一起强化了这种不确定性,使观众以一种新的电影心态沉浸在场景的时空之中,推动他先去感知,再来寻理。 因此,这种电影风格拉开了自己与影像受制于场景动作这个鼓舞人心的观念的距离,该观念是传统电影的主要特点,在当代大多数影音产品中依然有所体现。同时,此风格还与巴赞提出的现实主义叙述保持距离。此外,现代电影的许多流派认为语言实验会使批判性质疑处于恒久状态,这种电影风格也要与此保持距离。再有,它还要与后现代电影叙事解构的碎片化、非线性(有时是彼得·格林威和大卫·柯南伯格电影中的样式主义或新巴洛克风格)风格区别开来,以及与最近几十年阿巴斯·基阿罗斯塔米、斯派克·琼斯和米歇尔·贡德里等人实践的自我指涉性元电影区别开来。
《纳布亚魅影》剧照 以上即是短片《纳布亚魅影》(Phantoms of Nabua,2009)的叙事,该片由泰国电影人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导演。对单一场景身临其境的研究,就像把日常琐事放在放大镜下,把观众带向另一个叙事时空。片中没有对话,也就没有多少理性信息。然而,我们对场景的了解均直观来自于影片中占主要成分的感官刺激。这样的手段也许是一种很“自然的”方式,哪怕短暂地,将解释电影叙事中移动影像所惯用的理性和心理分析态度摈弃一旁。然而,对诸如韦拉斯哈古的片中所包含的感官维度开放的接受能够放大我们“感同身受”与“身临其境”的体会,令我们几乎置身于场景之中。这种人与场景的亲近并不是运用本世纪初兴起的好莱坞三维技术所展示的测量意义上的沉浸感,而是依靠观众与影像之间达成的默契。在这个默契之下,强烈的情感交流就此开始。在交流中,我们的感觉与镜头记录的事件相伴而行,观察事件中每个细节的发展变化,就好像我们完全融入到了这些细节之中。 世界很多地区电影中的场景都适合用来表达这个主题。在其中一个场景中,摄像机一开始似乎是随意探进一间被废弃的印刷车间,镜头划过印刷机和其它工具,在各房间进进出出,直到停留在两个孩子身上。两个孩子开始玩游戏,镜头一直跟着他们跑过小巷、街道、树林,最后镜头停下来,像人一样,稍作休息,喘口气(《沙罗双树》[Shara],河濑直美[日本],2003)。在另外一个场景中,一个年轻人在车站专心聆听并记录声音,火车在镜头前来往穿行,摄像机一直如呼吸般微调着画面(《咖啡时光》[Café Lumière],侯孝贤[中国台湾],2003)。而在又一个场景中,观众看到的是训练中的外籍军团士兵一个接一个、不断重复的肢体动作。摄影机在拍摄这些动作时采用了最小幅度、漂浮式的移动方式,在一连串的重复后,呈现出催眠的特性,能够从一个情节延续至下一个。比如:在拍完钢索训练这个镜头之后是晾衣绳的全景镜头,绳上晾着衣服等着被沙漠风吹干(《军中禁恋》[Beau Travail],克莱尔·丹尼斯[法国],1999)。 所有的场景(和影片)都使用了一种叙事策略,在这个策略中,感官因素被视为观众审美体验的原始层面,它并不用动作和对话来解释一切,而是采用了视觉和文本模糊的基调,使观众能够探索影像中内蕴的所有感官体验。换言之,这些影片代表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视听教育——通常与影像中的视觉痕迹相关。劳拉·马克斯将此称为“触觉可视”,这可以让我们重新了解如何去观看和聆听电影,从而打破霸权电影传统(甚或是当代电影的后现代叙事解构和立体视觉冲击)长久以来加诸于观众身上的感觉麻痹。 一些电影批评家采用“心流电影”(flow cinema)或“心流美学”(flow aesthetics)来指称这种视听叙事模式,斯蒂芬·布凯2002年在《电影手册》刊发的一篇文章中创造了这两个术语。最早一批此类型的电影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拍摄的。这些电影的特点是强调人身再入日常时空,这些电影也被认为是受到视听语言影响的感官经历,其存在与被解读皆源于此。电影中既能引发不安又会带来微妙惊奇感的时间省略和视觉模糊制造了不确定性。电影中的影像和让观众彻底放松的环境组合在一起强化了这种不确定性,使观众以一种新的电影心态沉浸在场景的时空之中,推动他先去感知,再来寻理。 因此,这种电影风格拉开了自己与影像受制于场景动作这个鼓舞人心的观念的距离,该观念是传统电影的主要特点,在当代大多数影音产品中依然有所体现。同时,此风格还与巴赞提出的现实主义叙述保持距离。此外,现代电影的许多流派认为语言实验会使批判性质疑处于恒久状态,这种电影风格也要与此保持距离。再有,它还要与后现代电影叙事解构的碎片化、非线性(有时是彼得·格林威和大卫·柯南伯格电影中的样式主义或新巴洛克风格)风格区别开来,以及与最近几十年阿巴斯·基阿罗斯塔米、斯派克·琼斯和米歇尔·贡德里等人实践的自我指涉性元电影区别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