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图书馆机构用户,欢迎您!
我国职业教育的主要矛盾是人才培养质量与企业的优质、多元需求不相适应,其根源在于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不足。依照弗里德曼的法律制度生成理论建构校企合作法律制度,其“输入”端应为确立企业职业教育主导地位的客观立法需求。“加工”内容则重在调整校企合作法律关系,厘清法律关系主体,重新匹配权利义务,聚焦法律关系客体。至于校企合作法律制度的“输出”端,则应为包括制度规范、行为规范和责任规范在内的旨在规范校企合作主体行为的制度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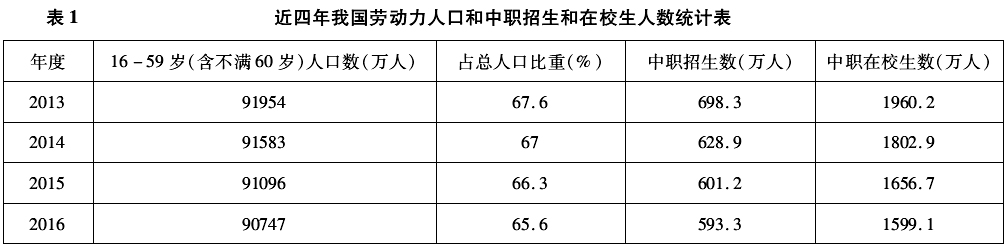 (二)企业参与不足严重制约职业教育质量 企业需求决定职业教育的标准和方向。作为工业社会的产物,现代职业教育的经济功能决定了它与行业、企业关系最密切,效果最直接,作用也最明显。职业教育作为直接面向职业岗位需求、服务产业发展的一种教育类型,企业的作用无可替代、不可或缺。企业的员工岗位要求决定了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企业的生产技术、生产工艺和生产流程决定了职业教育的课程,企业的用人层次与数量决定着职业教育的结构和规模。因此,企业的人才需求是校企合作的逻辑起点,企业的岗位标准是校企合作的育人标杆,而企业的用人评价则是校企合作的质量标准。 现行经济和教育制度影响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可能性。21世纪初我国实行的国有企业主辅分离政策,使企业与职业教育日渐分离。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企业对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却未达到应有高度,尚未充分看到参与职业教育能够给企业带来的人力资源优势和潜在的长远发展利益。[9]据110家500强企业调查显示,企业真正参与校企合作、共建产学研中心,开展技能大赛的比例偏少,只有22.34%和13.6%。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主要出于经济和公益目的诉求,缺乏长效机制和制度供给。[10]同时,20世纪90年代开展的高校扩招政策带来的中专升大专、大专升本科的“升级热”,导致中职发展空间被挤压,高职亦步亦趋本科办学,成为本科的“压缩饼干”;政府投资的主导地位,国企改革的阵痛带来的用人需求和职业教育投入的减少,使职业教育越来越依靠政府,而逐渐偏离市场的需求;加之我国职业教育实行学年制而非学分制,学生自主选择学习时间的余地不大,制约了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开展。
(二)企业参与不足严重制约职业教育质量 企业需求决定职业教育的标准和方向。作为工业社会的产物,现代职业教育的经济功能决定了它与行业、企业关系最密切,效果最直接,作用也最明显。职业教育作为直接面向职业岗位需求、服务产业发展的一种教育类型,企业的作用无可替代、不可或缺。企业的员工岗位要求决定了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企业的生产技术、生产工艺和生产流程决定了职业教育的课程,企业的用人层次与数量决定着职业教育的结构和规模。因此,企业的人才需求是校企合作的逻辑起点,企业的岗位标准是校企合作的育人标杆,而企业的用人评价则是校企合作的质量标准。 现行经济和教育制度影响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可能性。21世纪初我国实行的国有企业主辅分离政策,使企业与职业教育日渐分离。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企业对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却未达到应有高度,尚未充分看到参与职业教育能够给企业带来的人力资源优势和潜在的长远发展利益。[9]据110家500强企业调查显示,企业真正参与校企合作、共建产学研中心,开展技能大赛的比例偏少,只有22.34%和13.6%。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主要出于经济和公益目的诉求,缺乏长效机制和制度供给。[10]同时,20世纪90年代开展的高校扩招政策带来的中专升大专、大专升本科的“升级热”,导致中职发展空间被挤压,高职亦步亦趋本科办学,成为本科的“压缩饼干”;政府投资的主导地位,国企改革的阵痛带来的用人需求和职业教育投入的减少,使职业教育越来越依靠政府,而逐渐偏离市场的需求;加之我国职业教育实行学年制而非学分制,学生自主选择学习时间的余地不大,制约了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