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图书馆机构用户,欢迎您!
西方早期电影中的正反打主要有三种不同的形式:轴线、侧偏和主次,在默片时代发展过程中,轴线和主次的方式逐渐式微,有人根据西方电影的这一特征,将面对镜头的表演归属于另类,并且将这一结论推演至早期的中国电影。而中国默片时代电影中正反打发展的轨迹与西方完全不同,不是单科独进,而是三种方式齐头并进,特别是主次方式的正反打发展出了多种样式,形成了自身独特的语言风格。按照波德维尔的理论,正反打既不应该是“自然”(倾向感知)的,也不应该是“惯例”(文化决定)的,而是应该兼顾这两端,这样才能够包容发展中所出现的各种不同形式。
 苏联电影《母亲》中维拉索夫与白军军官对话正反打镜头 一、正反打问题的由来 梳理西方默片时代的正反打,可以发现以下三种基本的方式: 1.轴线正反打。 所谓轴线正反打是指拍摄机位放在对话双方构成的“轴线”(“轴线是影片分别表现有交流的双方时,它们之间假象的连线”①)上,演员面对摄影机如同面对对方。如在苏联著名导演普多夫金的电影《母亲》(1926)中,男主人公维拉索夫与前来他家搜查的白军军官的对话,被影片表现为他们两人的正面影像(演员面对摄影机镜头表演),因此,轴线正反打也可以称之为“正面正反打”。 2.侧偏正反打。
苏联电影《母亲》中维拉索夫与白军军官对话正反打镜头 一、正反打问题的由来 梳理西方默片时代的正反打,可以发现以下三种基本的方式: 1.轴线正反打。 所谓轴线正反打是指拍摄机位放在对话双方构成的“轴线”(“轴线是影片分别表现有交流的双方时,它们之间假象的连线”①)上,演员面对摄影机如同面对对方。如在苏联著名导演普多夫金的电影《母亲》(1926)中,男主人公维拉索夫与前来他家搜查的白军军官的对话,被影片表现为他们两人的正面影像(演员面对摄影机镜头表演),因此,轴线正反打也可以称之为“正面正反打”。 2.侧偏正反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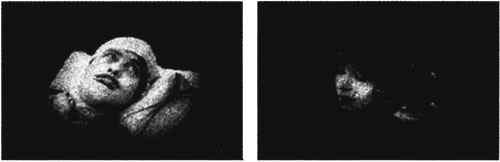 美国电影《一个国家的诞生》中喀麦隆与艾丝·斯塔曼小姐在医院相遇的正反打镜头 所谓侧偏正反打是指拍摄对话双方时摄影机放在轴线的一侧,接近轴线但与轴线形成一定的角度,一般来说偏离的角度在轴线夹角的45度之内。上面是美国著名导演格里菲斯影片《一个国家的诞生》(1915)的截图,如果我们在两张截图之间画一条连线(轴线),就会发现摄影机拍摄人物的角度大约在偏离轴线30至45度之间,我们看到的人物面部影像都是侧偏的(喀麦隆看上去相对正面是因为他受伤不能面对斯塔曼小姐,只能扭头看,因而偶然地出现了正面影像,这里所谓的“侧偏”主要根据人物的视线,但凡不看镜头的表演都属于“侧偏”,而不论其面部是否被正面表现,后面还会出现类似的案例)。 3.主次正反打。
美国电影《一个国家的诞生》中喀麦隆与艾丝·斯塔曼小姐在医院相遇的正反打镜头 所谓侧偏正反打是指拍摄对话双方时摄影机放在轴线的一侧,接近轴线但与轴线形成一定的角度,一般来说偏离的角度在轴线夹角的45度之内。上面是美国著名导演格里菲斯影片《一个国家的诞生》(1915)的截图,如果我们在两张截图之间画一条连线(轴线),就会发现摄影机拍摄人物的角度大约在偏离轴线30至45度之间,我们看到的人物面部影像都是侧偏的(喀麦隆看上去相对正面是因为他受伤不能面对斯塔曼小姐,只能扭头看,因而偶然地出现了正面影像,这里所谓的“侧偏”主要根据人物的视线,但凡不看镜头的表演都属于“侧偏”,而不论其面部是否被正面表现,后面还会出现类似的案例)。 3.主次正反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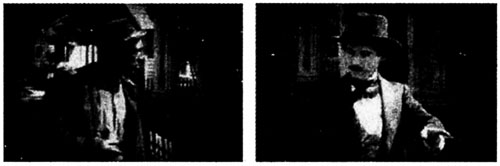 美国电影《一个国家的诞生》中黑人士兵与喀麦隆发生争执的正反打镜头 不论是轴线(正面)正反打还是侧偏正反打,其在表现对话双方时基本上是均衡的,并不特别突出其中的某一方,而主次正反打则是要在对话的两方中分出主次来,这种区分主要表现在镜头拍摄的景别和角度上。如在影片《一个国家的诞生》中,白人喀麦隆和在他家门口窥视喀麦隆妹妹的黑人士兵发生了争执,我们可以看到,拍摄喀麦隆的机位与轴线的夹角大约是在45度,而黑人则是约90度的位置,因此我们看到的喀麦隆画面是半侧脸,而黑人则是全侧脸。这种主次之分有时也体现在景别上。如在同一部影片中,表现斯塔曼先生与另一绅士对话时,明显是将斯塔曼先生作为了主要的一方,斯塔曼是影片中的主要人物,用近景表现,而另一位作为过场人物的绅士则是用中景表现。
美国电影《一个国家的诞生》中黑人士兵与喀麦隆发生争执的正反打镜头 不论是轴线(正面)正反打还是侧偏正反打,其在表现对话双方时基本上是均衡的,并不特别突出其中的某一方,而主次正反打则是要在对话的两方中分出主次来,这种区分主要表现在镜头拍摄的景别和角度上。如在影片《一个国家的诞生》中,白人喀麦隆和在他家门口窥视喀麦隆妹妹的黑人士兵发生了争执,我们可以看到,拍摄喀麦隆的机位与轴线的夹角大约是在45度,而黑人则是约90度的位置,因此我们看到的喀麦隆画面是半侧脸,而黑人则是全侧脸。这种主次之分有时也体现在景别上。如在同一部影片中,表现斯塔曼先生与另一绅士对话时,明显是将斯塔曼先生作为了主要的一方,斯塔曼是影片中的主要人物,用近景表现,而另一位作为过场人物的绅士则是用中景表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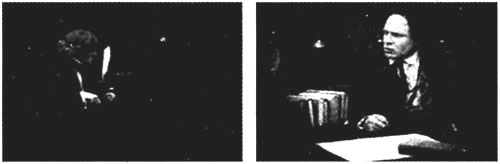 美国电影《一个国家的诞生》中斯塔曼先生会见某绅士的正反打镜头 西方电影中人物对话正反打的这三种方式在20世纪20年代的末期,也就是有声片出现之前,已经演变成几乎是单一的侧偏正反打,轴线的和主次的正反打方式几乎消亡,特别是在美国好莱坞的商业电影中已经难得一见。据此,有人将中国电影默片时代经常出现的轴线和主次正反打认定为是前叙事的,如在讨论侯曜的电影《西厢记》(1927)时,认为“在该片中,狂热观看的特写镜头,以及在热情与不安之间摆动的一双眉毛的特写镜头,也上演了同一类型的‘演员反复观看摄影机’的情景,而这恰恰是美国和欧洲早期‘吸引力’电影的特征”。②所谓“吸引力”电影简单来说是指与“叙事”为主电影对立的,以“展示”为主导的电影形态。一般来说,人们所认同的电影艺术与叙事不可分割,如果影片仅只“展示”则是一种前叙事,或者说处于前电影艺术阶段,因此林格伦在60年代出版的《论电影艺术》一书中会说:“兴趣在故事中乃是一个最基本的东西,E·M·福斯特把它称之为‘文学有机体的最低级的和最简单的东西’……”③因此,所谓“吸引力电影”其实就是“前电影”,或者说“原始电影”的别称。按照这样的说法,《西厢记》这样的电影便要被划归到“最低级”和“最简单”的前电影艺术中去了。贺瑞晴在自己文章中提出的这一观点,把“演员反复观看摄影机”作为一种判断的标志来判定影片的性质,从而在逻辑上把轴线正反打、含正面表现的主次正反打这样的表现手段划归为了单纯的“展示”手段,按照这一逻辑,几乎所有中国默片时代的电影都可以被装进“吸引力电影”的麻袋。这样的说法究竟有没有道理?需要我们从事实的源头上予以辨别。
美国电影《一个国家的诞生》中斯塔曼先生会见某绅士的正反打镜头 西方电影中人物对话正反打的这三种方式在20世纪20年代的末期,也就是有声片出现之前,已经演变成几乎是单一的侧偏正反打,轴线的和主次的正反打方式几乎消亡,特别是在美国好莱坞的商业电影中已经难得一见。据此,有人将中国电影默片时代经常出现的轴线和主次正反打认定为是前叙事的,如在讨论侯曜的电影《西厢记》(1927)时,认为“在该片中,狂热观看的特写镜头,以及在热情与不安之间摆动的一双眉毛的特写镜头,也上演了同一类型的‘演员反复观看摄影机’的情景,而这恰恰是美国和欧洲早期‘吸引力’电影的特征”。②所谓“吸引力”电影简单来说是指与“叙事”为主电影对立的,以“展示”为主导的电影形态。一般来说,人们所认同的电影艺术与叙事不可分割,如果影片仅只“展示”则是一种前叙事,或者说处于前电影艺术阶段,因此林格伦在60年代出版的《论电影艺术》一书中会说:“兴趣在故事中乃是一个最基本的东西,E·M·福斯特把它称之为‘文学有机体的最低级的和最简单的东西’……”③因此,所谓“吸引力电影”其实就是“前电影”,或者说“原始电影”的别称。按照这样的说法,《西厢记》这样的电影便要被划归到“最低级”和“最简单”的前电影艺术中去了。贺瑞晴在自己文章中提出的这一观点,把“演员反复观看摄影机”作为一种判断的标志来判定影片的性质,从而在逻辑上把轴线正反打、含正面表现的主次正反打这样的表现手段划归为了单纯的“展示”手段,按照这一逻辑,几乎所有中国默片时代的电影都可以被装进“吸引力电影”的麻袋。这样的说法究竟有没有道理?需要我们从事实的源头上予以辨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