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图书馆机构用户,欢迎您!
电影由充满“神韵”的“活动影像”构成,此“活动”即电影中的“运动”。它共有四重面貌:“具象运动”,即以影像或元素等为载体的“位移运动”;“纯粹运动”,即通过移动镜头或蒙太奇单元呈现出来的所有影像及元素共有的“纯粹活动性”;“规范运动”,即始终按照“感知-回应”模式循环延伸,间接呈现电影“神韵”的影像运动;“脱轨运动”,即脱离了“感知-回应”模式,让电影“神韵”自主直接呈现的影像运动。
 图1 “具象运动”只呈现为元素的位移 从移动镜头看,有两种情况。其一是移动空镜头。所谓空镜头,就是其中没有人物,甚至没有动物的纯景物镜头。当镜头本身移动时,其中的景物也会随之出现位移,如从上到下或从下到上(上下移动空镜头),从左到右或从右到左(左右移动空镜头),从前到后或从后到前(前后推拉空镜头)等。《非诚勿扰》中有一个交代西溪风光的空镜头:原生态的林木、小桥从右到左移动。这里,造成景物移动的是整个影像的方位移动(图2)。在此,“具象运动”表现为整个影像的方位移动(或说景物随同整个影像而位移)。
图1 “具象运动”只呈现为元素的位移 从移动镜头看,有两种情况。其一是移动空镜头。所谓空镜头,就是其中没有人物,甚至没有动物的纯景物镜头。当镜头本身移动时,其中的景物也会随之出现位移,如从上到下或从下到上(上下移动空镜头),从左到右或从右到左(左右移动空镜头),从前到后或从后到前(前后推拉空镜头)等。《非诚勿扰》中有一个交代西溪风光的空镜头:原生态的林木、小桥从右到左移动。这里,造成景物移动的是整个影像的方位移动(图2)。在此,“具象运动”表现为整个影像的方位移动(或说景物随同整个影像而位移)。  图2 整个影像的方位移动 其二是镜头中有人物或事物移动的移动镜头。例如美国导演罗伯特·泽米吉斯(Robert Zemeckis)《阿甘正传》开始时的长镜头:摄影机对准空中飘荡的羽毛做同步移动,最后在羽毛落地时捕捉到主人公的脚(图3)。再比如尹力《云水谣》交待20世纪40年代末台北环境的那个长镜头:摄影机在建筑、家庭、街道、活动的人物中移动穿行,最后停在女主人公的家中。其中既有电影影像本身的方位移动,也有影像构成元素如羽毛、人物等的位移。在此,“具象运动”一方面表现为影像构成元素的位移,另一方面表现为影像本身的方位移动。 蒙太奇段落说,则有三种情况:由固定镜头构成的蒙太奇段落、由固定镜头和移动镜头构成的蒙太奇段落和由移动镜头构成的蒙太奇段落。爱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战舰波将金号》中“三个石狮子”的蒙太奇段落,就是第一种情况的典型。三个固定的石狮子镜头,经过蒙太奇行动而转化为一个活动狮子的影像。“具象运动”在此表现为狮子的位移,也表现为整个影像的跨空间位移。
图2 整个影像的方位移动 其二是镜头中有人物或事物移动的移动镜头。例如美国导演罗伯特·泽米吉斯(Robert Zemeckis)《阿甘正传》开始时的长镜头:摄影机对准空中飘荡的羽毛做同步移动,最后在羽毛落地时捕捉到主人公的脚(图3)。再比如尹力《云水谣》交待20世纪40年代末台北环境的那个长镜头:摄影机在建筑、家庭、街道、活动的人物中移动穿行,最后停在女主人公的家中。其中既有电影影像本身的方位移动,也有影像构成元素如羽毛、人物等的位移。在此,“具象运动”一方面表现为影像构成元素的位移,另一方面表现为影像本身的方位移动。 蒙太奇段落说,则有三种情况:由固定镜头构成的蒙太奇段落、由固定镜头和移动镜头构成的蒙太奇段落和由移动镜头构成的蒙太奇段落。爱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战舰波将金号》中“三个石狮子”的蒙太奇段落,就是第一种情况的典型。三个固定的石狮子镜头,经过蒙太奇行动而转化为一个活动狮子的影像。“具象运动”在此表现为狮子的位移,也表现为整个影像的跨空间位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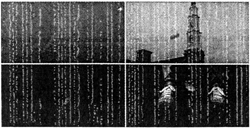 图3 影像本身及其元素同时移动 张艺谋的《英雄》中,“小树林”一场戏则可以视为第二种情况的范例。它从飞雪的全景固定镜头开始,以如月的全景固定镜头结束,中间则是不同景别的移动镜头和固定镜头的串联。在此我们既可以看到人物、事物(黄叶)的位移,也能看到影像本身的方位、景别移动,还能看到影像本身的跨空间移动。这里,“具象运动”首先表现为影像构成元素的位移,其次表现为影像的方位移动,最后表现为影像本身的跨空间移动。
图3 影像本身及其元素同时移动 张艺谋的《英雄》中,“小树林”一场戏则可以视为第二种情况的范例。它从飞雪的全景固定镜头开始,以如月的全景固定镜头结束,中间则是不同景别的移动镜头和固定镜头的串联。在此我们既可以看到人物、事物(黄叶)的位移,也能看到影像本身的方位、景别移动,还能看到影像本身的跨空间移动。这里,“具象运动”首先表现为影像构成元素的位移,其次表现为影像的方位移动,最后表现为影像本身的跨空间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