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图书馆机构用户,欢迎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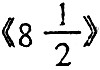 ,哈罗德·品特的《法 国中尉的女人》,谿耕平的《蒲田进行曲》等等。 可以说,几乎所有的“片中戏”和“片中片”故事片所表现的内容,都与戏剧艺术或 者戏剧艺术家和电影艺术或者电影艺术家这一题材有关。它们总是由电影创作者来给我 们讲述一个关于戏剧艺术家或者电影艺术家的故事,再由戏剧艺术家或者电影艺术家来 给我们讲述另外一个故事。这样,故事片中的人物既承担了角色又承担了演员这一复调 叙事者职能。显然,这种故事片所表现的双重内容决定了这种故事片的结构形态必然呈 现出复调的叙事结构框架。这多少有些象西方人所说的一种“中国式盒子”——大盒子 中套着小盒子。“片中戏”和“片中片”故事片的叙事结构也是这样,一个故事的叙述 总是被包含在另一个故事的叙述之中。 只要我们对这种类型的故事片稍做分析,我们便会发现,所谓复调叙事结构,在这类故事片中其叙述形态是各个有别的,而如果我们做更进一步的分析,还会明白一个重要 得多的问题——这种故事片的复调叙事结构已经远远超越了技巧学上的意义,它们自身 具备了一种更为深刻的艺术意味。 对叙事艺术结构形态的分析与归纳,人们历来就是从各种不同的视角上着眼的。我们 从那些讨论有关这一问题的理论书籍中看到,站在不同的视角上来分析与归纳,相同的 叙事结构形态可以显现出异质,相异的叙事结构形态也可以显现出同质。我们认为,无 论选择何种视角来对叙事艺术的结构形态进行分析与归纳,只要它们能够不同程度地揭 示出艺术美学与艺术创造上的意义,那么这种视角便可以成立为合理的依据。 当我们说“片中戏”和“片中片”故事类型是复调叙事结构的时候,我们显然已从第 一重叙事层面的戏外片或者片外片和第二重叙事层面的片中戏或者片中片之间的叙述线 索的分析来对这种故事片的结构进行了归纳,同样,当我们要进一步对这种复调叙事结 构的叙述形态做出归纳时,我们仍然遵循它们第一重叙事层面与第二重叙事层面之间的 叙述关系来进行分析。 溶入式复调叙事结构 在“片中戏”和“片中片”故事片类型中,有一种故事片的第二重叙事层便溶入了第 一叙事层面之中,即是说,在叙述关系上,第二重叙事层面被镶嵌或包容在第一重叙事 层面中,我们把它称做溶入式复调叙事结构的故事片,或简称“溶入式”。 法国当年的“新浪潮”电影战将弗朗索瓦·特吕弗在八十年代编导的《最后一班地铁 》,是一部才华横溢的故事片杰作,它叙述了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在巴黎留存下来 的一个剧团的故事。一九四二年的巴黎已沦陷为德国军队的占领区,在法国的所有占领 区内,法西斯分子进行了大规模的排犹活动,蒙马特尔剧团的犹太人导演吕卡斯在这样 严峻的时刻只得隐藏到剧院的地窖里去,而此时蒙马特尔剧团正在准备上演一出新戏《 失踪的女人》,吕卡斯的妻子玛丽安扮演女主角“海伦娜”,初出茅庐的新手贝尔纳扮 演男主角“卡尔”。在上演《失踪的女人》的过程中,玛丽安和贝尔纳产生了恋情,可 是,贝尔纳很快便又离开了剧团,参加抵抗运动去了。 故事片《最后一班地铁》的第一重叙事层面表现了蒙马特尔剧团在占领时期争取上演 《失踪的女人》的过程中,女演员玛丽安和丈夫吕卡斯以及男演员贝尔纳之间的情感故 事,第二重叙事层面展现了挪威女作家卡伦·贝根写的话剧《失踪的女人》。对于第一 重故事,弗朗索瓦·特吕弗进行了近乎平铺直叙的完整叙述,而话剧《失踪的女人》, 他只不过给我们展示出了一些支离破碎的片断性内容。 严格地说,在叙述关系上,《最后一班地铁》的叙事结构是不可能一分为二地截然划 分开来的,因为话剧《失踪的女人》既可以被看成为一个独立的第二重叙事层面的内容 ,也可以被看成为是第一重叙事层面的内容。《失踪的女人》的第一次排练出现在影片 开始后的近半个小时,它的排练和演出在影片中总共插入了大约15次。当然,这样一个 时间性问题和数字性问题本身并不表明任何东西。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失踪的女人 》的每一次出现都是在第一重叙事层面的叙述线索上合乎情理地自然展现出来的,即是 说它已经被第一重叙事层面作为自身的内容因素所纳入。并且,在第二重叙事层面的叙 述中——无论排练还是演出《失踪的女人》,弗朗索瓦·特吕弗多次让它同时承载起了 对第一重叙事层面的叙述。
,哈罗德·品特的《法 国中尉的女人》,谿耕平的《蒲田进行曲》等等。 可以说,几乎所有的“片中戏”和“片中片”故事片所表现的内容,都与戏剧艺术或 者戏剧艺术家和电影艺术或者电影艺术家这一题材有关。它们总是由电影创作者来给我 们讲述一个关于戏剧艺术家或者电影艺术家的故事,再由戏剧艺术家或者电影艺术家来 给我们讲述另外一个故事。这样,故事片中的人物既承担了角色又承担了演员这一复调 叙事者职能。显然,这种故事片所表现的双重内容决定了这种故事片的结构形态必然呈 现出复调的叙事结构框架。这多少有些象西方人所说的一种“中国式盒子”——大盒子 中套着小盒子。“片中戏”和“片中片”故事片的叙事结构也是这样,一个故事的叙述 总是被包含在另一个故事的叙述之中。 只要我们对这种类型的故事片稍做分析,我们便会发现,所谓复调叙事结构,在这类故事片中其叙述形态是各个有别的,而如果我们做更进一步的分析,还会明白一个重要 得多的问题——这种故事片的复调叙事结构已经远远超越了技巧学上的意义,它们自身 具备了一种更为深刻的艺术意味。 对叙事艺术结构形态的分析与归纳,人们历来就是从各种不同的视角上着眼的。我们 从那些讨论有关这一问题的理论书籍中看到,站在不同的视角上来分析与归纳,相同的 叙事结构形态可以显现出异质,相异的叙事结构形态也可以显现出同质。我们认为,无 论选择何种视角来对叙事艺术的结构形态进行分析与归纳,只要它们能够不同程度地揭 示出艺术美学与艺术创造上的意义,那么这种视角便可以成立为合理的依据。 当我们说“片中戏”和“片中片”故事类型是复调叙事结构的时候,我们显然已从第 一重叙事层面的戏外片或者片外片和第二重叙事层面的片中戏或者片中片之间的叙述线 索的分析来对这种故事片的结构进行了归纳,同样,当我们要进一步对这种复调叙事结 构的叙述形态做出归纳时,我们仍然遵循它们第一重叙事层面与第二重叙事层面之间的 叙述关系来进行分析。 溶入式复调叙事结构 在“片中戏”和“片中片”故事片类型中,有一种故事片的第二重叙事层便溶入了第 一叙事层面之中,即是说,在叙述关系上,第二重叙事层面被镶嵌或包容在第一重叙事 层面中,我们把它称做溶入式复调叙事结构的故事片,或简称“溶入式”。 法国当年的“新浪潮”电影战将弗朗索瓦·特吕弗在八十年代编导的《最后一班地铁 》,是一部才华横溢的故事片杰作,它叙述了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在巴黎留存下来 的一个剧团的故事。一九四二年的巴黎已沦陷为德国军队的占领区,在法国的所有占领 区内,法西斯分子进行了大规模的排犹活动,蒙马特尔剧团的犹太人导演吕卡斯在这样 严峻的时刻只得隐藏到剧院的地窖里去,而此时蒙马特尔剧团正在准备上演一出新戏《 失踪的女人》,吕卡斯的妻子玛丽安扮演女主角“海伦娜”,初出茅庐的新手贝尔纳扮 演男主角“卡尔”。在上演《失踪的女人》的过程中,玛丽安和贝尔纳产生了恋情,可 是,贝尔纳很快便又离开了剧团,参加抵抗运动去了。 故事片《最后一班地铁》的第一重叙事层面表现了蒙马特尔剧团在占领时期争取上演 《失踪的女人》的过程中,女演员玛丽安和丈夫吕卡斯以及男演员贝尔纳之间的情感故 事,第二重叙事层面展现了挪威女作家卡伦·贝根写的话剧《失踪的女人》。对于第一 重故事,弗朗索瓦·特吕弗进行了近乎平铺直叙的完整叙述,而话剧《失踪的女人》, 他只不过给我们展示出了一些支离破碎的片断性内容。 严格地说,在叙述关系上,《最后一班地铁》的叙事结构是不可能一分为二地截然划 分开来的,因为话剧《失踪的女人》既可以被看成为一个独立的第二重叙事层面的内容 ,也可以被看成为是第一重叙事层面的内容。《失踪的女人》的第一次排练出现在影片 开始后的近半个小时,它的排练和演出在影片中总共插入了大约15次。当然,这样一个 时间性问题和数字性问题本身并不表明任何东西。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失踪的女人 》的每一次出现都是在第一重叙事层面的叙述线索上合乎情理地自然展现出来的,即是 说它已经被第一重叙事层面作为自身的内容因素所纳入。并且,在第二重叙事层面的叙 述中——无论排练还是演出《失踪的女人》,弗朗索瓦·特吕弗多次让它同时承载起了 对第一重叙事层面的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