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图书馆机构用户,欢迎您!
本文介绍西北方言历史的演变过程,并以此历史过程加以断代。所讨论的年代,由汉末三国开始,至现代为止。地域主要包括陕西南部的关中平原,以及甘肃走廊。断代系统基于各个历史阶段的现有文献资料,并着重讨论材料中最为明晰的那些历史时期。由于词汇和句法方面的材料较为缺乏,乃以声韵演变为断代之标准,划分出七个历史阶段:一、前古代西北话阶段(公元280年左右);二、古代西北话阶段(公元400年左右);三、隋唐长安阶段(公元580-650年);四、盛唐长安与盛唐沙洲阶段(公元700-800年);五、晚唐长安与沙洲阶段(公元800-1000年);六、后沙洲阶段(公元12世纪);七、现代方言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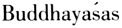 )对音材料和竺佛念对音材料。这些材料已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详细讨论过③。另一类是随后不久(约公元420年)出现的昙无谶(
)对音材料和竺佛念对音材料。这些材料已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详细讨论过③。另一类是随后不久(约公元420年)出现的昙无谶(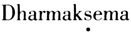 )对音材料,亦在Studies in Old Northwest Chinese中有所述及④。总之,这些可能是最早详细记录前现代时期西北方言音系的资料。因此,我们暂且将该时期称为“古代西北话阶段”(ONWC)。 对于“古代西北话阶段”以前的时期,我们有出自竺法护译本的对音材料。竺法护(
)对音材料,亦在Studies in Old Northwest Chinese中有所述及④。总之,这些可能是最早详细记录前现代时期西北方言音系的资料。因此,我们暂且将该时期称为“古代西北话阶段”(ONWC)。 对于“古代西北话阶段”以前的时期,我们有出自竺法护译本的对音材料。竺法护(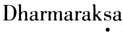 )于公元230年左右出生在敦煌的一个世居家族—月氏家族⑤,他的大部分翻译工作似乎都是在3世纪80年代(280′s)完成的,他从业于长安和甘肃走廊各地,一生著述颇丰,但遗憾的是其作品中的对音用例仅占一小部分。这部分对音用例经柯蔚南考察并收录⑥。至少就目前而言,这个时期也许是拥有早期西北方言可靠对音材料的最早的阶段。我们称其为“前古代西北话阶段”(Pre-ONWC)。 汉代中期出现了另一批对音材料,并非僧人所著。蒲立本(尤其是1962年的一项著述⑦)作过介绍,因而人们并不陌生。我们最近为这批材料做了索引,并在一篇未刊稿中述评了若干相关的问题⑧。该批材料中的一些汉代用例也许出自西北。除此之外,我们尚未发现有进一步论述甘肃走廊地区方言的材料。同时期,关中诗人也撰写了一批诗歌韵文资料,某种程度上可能是以当时的地域方音为基础创作的(参见柯蔚南相关研究⑨)。较汉代中期更早的阶段,有一批来自古秦地的金石资料(paleographic data)可能与当前研究相关。此处主要指的是云梦墓(秦时期)出土文献中的及东周秦国青铜器铭文中的“假借”材料。韵文和假借材料可能都以某种方式反映了西北方言音系极为早期的面貌,但在我们看来,我们并不知道这种类型的资料是否一定可用于上述时期音系的实际构拟。因此,是否可将其纳入该断代系统也是无法确定的。但如果执意如此的话,我们可以借鉴考古学领域的术语,称这种类型的材料代表了“前古代西北话阶段”之前的那个时期(Archaic Northwest phase⑩)。 三、中古阶段 1.古代西北话阶段(ONWC)之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材料几乎全都来自关中地区。此期第一个主要阶段(包括6世纪后半叶和7世纪前半叶)以两种不同类型的材料为代表。第一种是可能出自6世纪后半叶长安地区的阇那崛多(
)于公元230年左右出生在敦煌的一个世居家族—月氏家族⑤,他的大部分翻译工作似乎都是在3世纪80年代(280′s)完成的,他从业于长安和甘肃走廊各地,一生著述颇丰,但遗憾的是其作品中的对音用例仅占一小部分。这部分对音用例经柯蔚南考察并收录⑥。至少就目前而言,这个时期也许是拥有早期西北方言可靠对音材料的最早的阶段。我们称其为“前古代西北话阶段”(Pre-ONWC)。 汉代中期出现了另一批对音材料,并非僧人所著。蒲立本(尤其是1962年的一项著述⑦)作过介绍,因而人们并不陌生。我们最近为这批材料做了索引,并在一篇未刊稿中述评了若干相关的问题⑧。该批材料中的一些汉代用例也许出自西北。除此之外,我们尚未发现有进一步论述甘肃走廊地区方言的材料。同时期,关中诗人也撰写了一批诗歌韵文资料,某种程度上可能是以当时的地域方音为基础创作的(参见柯蔚南相关研究⑨)。较汉代中期更早的阶段,有一批来自古秦地的金石资料(paleographic data)可能与当前研究相关。此处主要指的是云梦墓(秦时期)出土文献中的及东周秦国青铜器铭文中的“假借”材料。韵文和假借材料可能都以某种方式反映了西北方言音系极为早期的面貌,但在我们看来,我们并不知道这种类型的资料是否一定可用于上述时期音系的实际构拟。因此,是否可将其纳入该断代系统也是无法确定的。但如果执意如此的话,我们可以借鉴考古学领域的术语,称这种类型的材料代表了“前古代西北话阶段”之前的那个时期(Archaic Northwest phase⑩)。 三、中古阶段 1.古代西北话阶段(ONWC)之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材料几乎全都来自关中地区。此期第一个主要阶段(包括6世纪后半叶和7世纪前半叶)以两种不同类型的材料为代表。第一种是可能出自6世纪后半叶长安地区的阇那崛多( )对音材料。尉迟治平(11)、柯蔚南(12)最近对此进行了讨论。早期水谷真城(13)、蒲立本(14)也围绕这些材料展开过专门的研究。第二种是颜师古(581-645)《汉书音义》(成书于公元641年)注解中的反切和直音材料。人们通常认为它是以同时期的长安方言音系为基础创作的。如果这种观点成立的话,相较于阇那崛多的对音材料(第一种材料)而言,第二种材料可能代表着稍晚期的语言变化。大岛正二(15)、董忠司(16)及钟兆华(17)对此进行了详细研究。这些研究通过严密的内部分析和比较,揭示了有关反切基础音系的大量信息。最后我们要提到的是一小部分7世纪的“藏汉对音”及“汉藏对音”材料。其中有些肯定至少可追溯到约公元650年或稍早时期,故而这些对音材料同颜师古的材料属同一时期。以上所有这些材料代表的是“隋唐长安阶段”(STCA)。从“古代西北话阶段”(ONWC)到“隋唐长安阶段”(STCA)的过渡是以某些明显的音系变化为标志的。声母中,双唇塞音(bilabial stops)在元音*u前变为唇齿音,舌尖塞音(dental stops)中开始出现一种带有卷舌音特征的新的塞音系列。韵母中,止摄内部广为合并,一等东、冬两韵已完全合二为一。
)对音材料。尉迟治平(11)、柯蔚南(12)最近对此进行了讨论。早期水谷真城(13)、蒲立本(14)也围绕这些材料展开过专门的研究。第二种是颜师古(581-645)《汉书音义》(成书于公元641年)注解中的反切和直音材料。人们通常认为它是以同时期的长安方言音系为基础创作的。如果这种观点成立的话,相较于阇那崛多的对音材料(第一种材料)而言,第二种材料可能代表着稍晚期的语言变化。大岛正二(15)、董忠司(16)及钟兆华(17)对此进行了详细研究。这些研究通过严密的内部分析和比较,揭示了有关反切基础音系的大量信息。最后我们要提到的是一小部分7世纪的“藏汉对音”及“汉藏对音”材料。其中有些肯定至少可追溯到约公元650年或稍早时期,故而这些对音材料同颜师古的材料属同一时期。以上所有这些材料代表的是“隋唐长安阶段”(STCA)。从“古代西北话阶段”(ONWC)到“隋唐长安阶段”(STCA)的过渡是以某些明显的音系变化为标志的。声母中,双唇塞音(bilabial stops)在元音*u前变为唇齿音,舌尖塞音(dental stops)中开始出现一种带有卷舌音特征的新的塞音系列。韵母中,止摄内部广为合并,一等东、冬两韵已完全合二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