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图书馆机构用户,欢迎您!
动词的评价性形态是指通过形态手段表达动词的“主观量”与默认值或标准值发生偏离,常常附加“褒化”或“贬化”的主观评价。文章考察了52种世界语言和45种中国境内民族语言的动词评价性形态,总结了其在区域分布、表现形式和意义方面的共性与类型特征。从世界范围来看,动词评价性形态不是语言共性特征,其区域分布具有明显差异和倾向性;在表现形式上,后缀和重叠占优势;在意义上,以贬化评价为主,常与“复动性”和“体貌”发生交融。我国境内民族语言的动词评价性形态较发达,具体表现在:1)形式多样,有完全重叠、重叠+词缀、部分重叠、重叠式的四音格词、动词与状貌词结合、加缀等;2)意义丰富,既有表达增量的,也有表达减量的,以附加贬化评价为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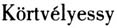 (2015)进一步用量范畴框架概括评价性形态:人对世界的基本认识范畴包括事物、动作、性质和情形等,通常有一个标准或默认量(default value),当说话人的认识偏离标准值或默认值时就会产生评价范畴(说话人对默认值的偏离分为正向和负向,以“指大、指小、贬化、褒化”为原型意义,适用于不同的认知范畴),表现在形态上就是评价性形态。 EM的认知基础是具身认知(embodiment)和隐喻。人从身体出发认识世界,往往借助物理维度表征抽象情感。“指小”“指大”表达的是说话人对物理维度主观量的判断,“贬化”“褒化”则是在主观量基础上通过隐喻表达说话人的态度或情感。EM的本质是语言表达的主观性和主观化。语言的主观性体现于说话人对世界的认识和认识世界的视角,而EM系统地反映了说话人对世界的认识存在“量”上的主观偏离。EM的使用不是语法强制的,而是取决于说话人的态度和感情、说话人与听话人所处的会话语境,以及说话人与被评价事物或事件之间的关系。 1.2 动词评价性形态的相关研究 跨语言来看,不同词类的EM存在等级差异(Bauer 1997):名词>形容词,动词>副词,数词,代词,感叹词>限定词。名词最容易附加EM,其次是形容词,然后是动词。①目前EM的研究以名词为主,针对动词的研究还不多。一是因为动词上的EM没有名词那么常见,二是以往的研究视角局限于狭义的指小和指大,主要关注的是与名词范畴相关的量的偏离。其实,按照量范畴的理论框架,其他词类范畴的“量”也会产生认识偏离。就动词而言,对“动作量”的主观认识同样会产生评价含义,以往归入动词屈折范畴的部分体貌(aspectuality)和复动性(pluractionality),如动作的频率(frequentative)、反复(iterative)、强化(intensive)、弱化(attenuative)、分布(distributive)、尝试(tentative)、不认真(incassative)等,都表达了动作的主观量与默认值发生或增或减的偏离。因此,动词的EM可以界定为:通过形态手段表示动作主观量的改变,包括动作持续的时间、发生的频率、施行的强度、执行的意愿、方式、速度等,以表达不同的主观态度和感情。 文献中关于动词EM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罗曼语、斯拉夫语和少量阿尔泰语中,比如意大利语(Scalise 1984)、西班牙语(Prieto 2005)、克罗地亚语(Katunar 2013)、保加利亚语(Bagasheva 2015)、拉蒙钦语(Lamunkhin-Even,Pakendorf 2017)等,这些语言的EM很丰富。有些语言的动词EM与内部复动性(internal pluractionality)(Tovena 2008;Stosic 2013)发生融合,如现代希伯来语(Greenberg 2010);有些与体貌发生融合,如意大利语(Grandi2006)、现代希腊语和俄语(Efthymiou 2013)等。 目前还未见到专门针对动词EM的类型学研究,汉藏语系的相关研究更少见。本文将以52种语言为样本考察世界范围内动词EM的总体特征,然后重点分析中国境内民族语言动词EM的共性和类型特征。 2 动词评价性形态的总体特征 本文以《评价形态学手册》(Grandi和
(2015)进一步用量范畴框架概括评价性形态:人对世界的基本认识范畴包括事物、动作、性质和情形等,通常有一个标准或默认量(default value),当说话人的认识偏离标准值或默认值时就会产生评价范畴(说话人对默认值的偏离分为正向和负向,以“指大、指小、贬化、褒化”为原型意义,适用于不同的认知范畴),表现在形态上就是评价性形态。 EM的认知基础是具身认知(embodiment)和隐喻。人从身体出发认识世界,往往借助物理维度表征抽象情感。“指小”“指大”表达的是说话人对物理维度主观量的判断,“贬化”“褒化”则是在主观量基础上通过隐喻表达说话人的态度或情感。EM的本质是语言表达的主观性和主观化。语言的主观性体现于说话人对世界的认识和认识世界的视角,而EM系统地反映了说话人对世界的认识存在“量”上的主观偏离。EM的使用不是语法强制的,而是取决于说话人的态度和感情、说话人与听话人所处的会话语境,以及说话人与被评价事物或事件之间的关系。 1.2 动词评价性形态的相关研究 跨语言来看,不同词类的EM存在等级差异(Bauer 1997):名词>形容词,动词>副词,数词,代词,感叹词>限定词。名词最容易附加EM,其次是形容词,然后是动词。①目前EM的研究以名词为主,针对动词的研究还不多。一是因为动词上的EM没有名词那么常见,二是以往的研究视角局限于狭义的指小和指大,主要关注的是与名词范畴相关的量的偏离。其实,按照量范畴的理论框架,其他词类范畴的“量”也会产生认识偏离。就动词而言,对“动作量”的主观认识同样会产生评价含义,以往归入动词屈折范畴的部分体貌(aspectuality)和复动性(pluractionality),如动作的频率(frequentative)、反复(iterative)、强化(intensive)、弱化(attenuative)、分布(distributive)、尝试(tentative)、不认真(incassative)等,都表达了动作的主观量与默认值发生或增或减的偏离。因此,动词的EM可以界定为:通过形态手段表示动作主观量的改变,包括动作持续的时间、发生的频率、施行的强度、执行的意愿、方式、速度等,以表达不同的主观态度和感情。 文献中关于动词EM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罗曼语、斯拉夫语和少量阿尔泰语中,比如意大利语(Scalise 1984)、西班牙语(Prieto 2005)、克罗地亚语(Katunar 2013)、保加利亚语(Bagasheva 2015)、拉蒙钦语(Lamunkhin-Even,Pakendorf 2017)等,这些语言的EM很丰富。有些语言的动词EM与内部复动性(internal pluractionality)(Tovena 2008;Stosic 2013)发生融合,如现代希伯来语(Greenberg 2010);有些与体貌发生融合,如意大利语(Grandi2006)、现代希腊语和俄语(Efthymiou 2013)等。 目前还未见到专门针对动词EM的类型学研究,汉藏语系的相关研究更少见。本文将以52种语言为样本考察世界范围内动词EM的总体特征,然后重点分析中国境内民族语言动词EM的共性和类型特征。 2 动词评价性形态的总体特征 本文以《评价形态学手册》(Grandi和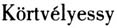 2015)中收录的52种语言为样本,考察了动词EM在世界范围内的分布情况,总结了其表现形式和意义的类型特征。
2015)中收录的52种语言为样本,考察了动词EM在世界范围内的分布情况,总结了其表现形式和意义的类型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