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缘起 《福州藏》为北宋时代刊刻于福州易俗里白马山东禅等觉寺的《崇宁藏》(1080-1112)与刊刻于福州闽县东芝山开元寺的《毗卢藏》(1112-1151)的合称,即所谓“由于《崇宁藏》与《毗卢藏》同刊板于福州,世人又统称这两部大藏经为《福州藏》《闽本》”①。佛经版本学家李际宁先生《佛经版本·〈崇宁藏〉与〈毗卢藏〉》对两藏刊本形制和相关收藏状况有如下解说: 《毗卢藏》版式与《崇宁藏》相同,一版6个半页或5个半页,半页6行,行17字。纸质亦厚实坚韧,色黄,纸背往往有长方形朱印“开元经局黄纸”,5×15厘米。 《崇宁》《毗卢》两藏皆每函十册,每函内又有单行音义。后补版者,又有将音义合刊于卷册之后者。 福州两藏在我国仅有少数单位收藏零本。在日本,有宫内厅图书寮、京都醍醐寺、教王护国寺、高野山劝学院、知恩院、横滨金泽文库等多个单位有收藏。这些单位的收藏品,几乎全部是两种藏的混合装。② 本文所作研究,即上述引文所言“混合装”《福州藏》中的“单行音义”(独立成型的音义)。“单行音义”即随函音义,卷轴本大藏经中与佛经经文卷帙相独立的“单卷音义”。因与经卷(一般为十卷,少部分不足十卷)相随而又同属一函,方有此称呼。随函音义列出本函所有经卷中的疑难词语做出语音语义的解释,与后世一律将“音义”置于各卷卷末的“卷末音义”相区别。《福州藏》以千字文序排列经函,“单卷音义”习称“某字音”,如“天地玄黄”中的玄字函,随函音义称作“玄字音”。《福州藏》所属的《崇宁藏》与《毗卢藏》是历史上空前绝后唯独匹配随函音义的汉文大藏经③。 本文研究使用的材料为以上引文所述日本宫内厅图书寮藏《宋版一切经》中五部经藏随函音义中的直音注音,经名与所属函之名称如下: (1)《大方广佛华严经》八十卷,“拱平章爱育黎首臣”八卷随函音义; (2)《大唐西域记》十二卷,“转疑”两卷随函音义; (3)《弘明集》十四卷,“集坟”两卷随函音义; (4)《广弘明集》三十卷,“典亦聚”三卷随函音义; (5)《大方广佛华严经合论》一百二十卷,“集盟何遵约法韩弊烦刑起剪”十二卷随函音义。④ 五种经本计256卷,音义27卷。⑤通过对音义实施相关系统研究是选题的总的出发点,作为音韵研究的一部分,本文对其所收直音做综合考察。 二、注音状况与直音分布 五种《福州藏》经本随函音义收有大约9万字的音义文本,平均每卷3300余字。按此推算,《福州藏》所收530卷随函音义总计高达175万字,实属汉文藏经版本语言类文献中最庞大的辞书。 所谓“音义”,既有释音部分,也有释义部分。五种经本在释音释义上各有侧重。《大方广佛华严经》以释音为主,释义甚少。《大唐西域记》释音释义兼顾,行文简洁。《弘明集》释音为主,条目丰富且几乎不释义。《广弘明集》在《弘明集》类型基础上更重视全面匹配释义,是五种佛经中音义内容最厚重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合论》卷数虽多,但音义文本字数才1.5万,每卷平均只有1200多字,五种材料中内容最为单薄。且其音义文字不多,但同一释音多次重复率高缺乏多样性,研究价值亦相应低一些。五种经本的音义制作虽在音义性质上看似无所不同,但释义与否或释义多寡,各经之间悬殊较大,可见刻经局对音义制作的释义部分无统一要求,任凭音义创制者斟酌实施。但随函音义中无论何种经本释音部分必不可少,虽然条目可以或多或少,但不可或缺。总体所见,《福州藏》作为最早开创经本音义模式的汉文大藏经,其释音是首要而必具的,是以卷为本的音义形式之根本所在。不言而喻,这与阅经诵经首先需要解决识字问题有密切关联。这种传统深刻影响了其后宋元时代的《思溪藏》《碛砂藏》《普宁藏》乃至明清两代多种大藏经的出版理念,音义以释音为主的出版形式,超越千年,一脉相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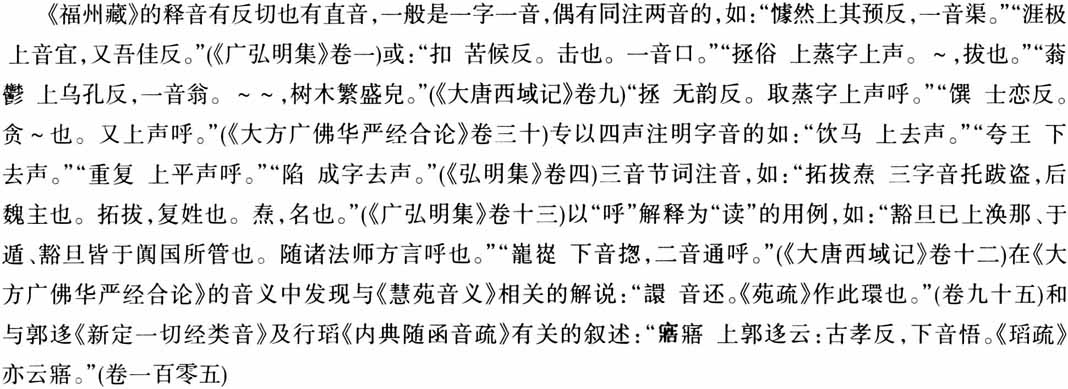
五种经本的音义编写出于何人之手,皆无考。既可能是五个人,也可能由更多人经手。但在不同种类音义的注音中,发现它们有高度的统一性、雷同性,同一注音多经本多次重复,可以窥见不仅《毗卢藏》音义对《崇宁藏》音义有继承关系,同藏的各音义制作者之间也有资料共享的可能性。这种跨经本的音注相似性是可以把多种经本的音注放在一起来作综合考察研究的基本前提。⑥ 五种经本音义中,反切居多,直音较少。本文首先选择直音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除了时间关系,也因为直音非宋代主流韵书《广韵》《集韵》之主体注音形式,直音研究涉及不引用或移植反切,有可能发现更多自然语音的蛛丝马迹。 据统计,五种经本音义中共有3760多条直音音注,其中《大方广佛华严经》416条,《大唐西域记》442条,《弘明集》839条,《广弘明集》2208条,《大方广佛华严经合论》133条。按卷数平均计算《广弘明集》最多,73条;其次《弘明集》,50条;《大唐西域记》37条;《大方广佛华严经》只有5.2条;《大方广佛华严经合论》最少,只有1.1条。直音数量的多寡不仅跟反切注音与直音注音的比率有关,与经本注音总量也有关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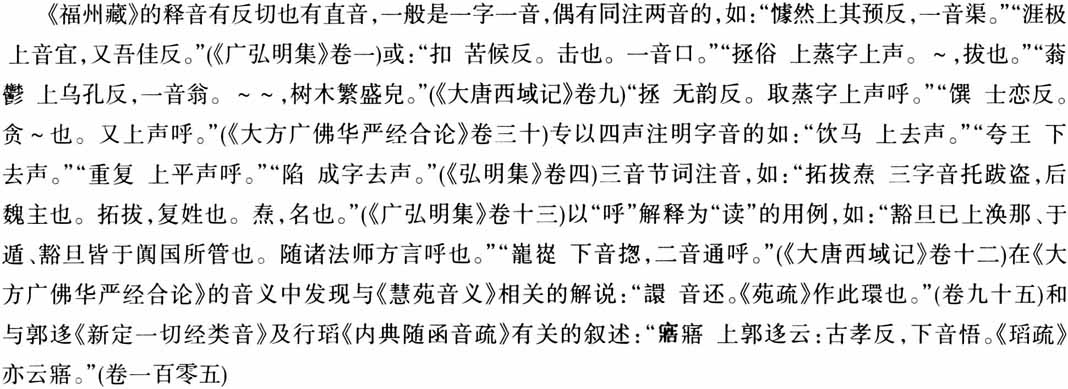 五种经本的音义编写出于何人之手,皆无考。既可能是五个人,也可能由更多人经手。但在不同种类音义的注音中,发现它们有高度的统一性、雷同性,同一注音多经本多次重复,可以窥见不仅《毗卢藏》音义对《崇宁藏》音义有继承关系,同藏的各音义制作者之间也有资料共享的可能性。这种跨经本的音注相似性是可以把多种经本的音注放在一起来作综合考察研究的基本前提。⑥ 五种经本音义中,反切居多,直音较少。本文首先选择直音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除了时间关系,也因为直音非宋代主流韵书《广韵》《集韵》之主体注音形式,直音研究涉及不引用或移植反切,有可能发现更多自然语音的蛛丝马迹。 据统计,五种经本音义中共有3760多条直音音注,其中《大方广佛华严经》416条,《大唐西域记》442条,《弘明集》839条,《广弘明集》2208条,《大方广佛华严经合论》133条。按卷数平均计算《广弘明集》最多,73条;其次《弘明集》,50条;《大唐西域记》37条;《大方广佛华严经》只有5.2条;《大方广佛华严经合论》最少,只有1.1条。直音数量的多寡不仅跟反切注音与直音注音的比率有关,与经本注音总量也有关联。
五种经本的音义编写出于何人之手,皆无考。既可能是五个人,也可能由更多人经手。但在不同种类音义的注音中,发现它们有高度的统一性、雷同性,同一注音多经本多次重复,可以窥见不仅《毗卢藏》音义对《崇宁藏》音义有继承关系,同藏的各音义制作者之间也有资料共享的可能性。这种跨经本的音注相似性是可以把多种经本的音注放在一起来作综合考察研究的基本前提。⑥ 五种经本音义中,反切居多,直音较少。本文首先选择直音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除了时间关系,也因为直音非宋代主流韵书《广韵》《集韵》之主体注音形式,直音研究涉及不引用或移植反切,有可能发现更多自然语音的蛛丝马迹。 据统计,五种经本音义中共有3760多条直音音注,其中《大方广佛华严经》416条,《大唐西域记》442条,《弘明集》839条,《广弘明集》2208条,《大方广佛华严经合论》133条。按卷数平均计算《广弘明集》最多,73条;其次《弘明集》,50条;《大唐西域记》37条;《大方广佛华严经》只有5.2条;《大方广佛华严经合论》最少,只有1.1条。直音数量的多寡不仅跟反切注音与直音注音的比率有关,与经本注音总量也有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