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图书馆机构用户,欢迎您!
漢字字符斷代是梳理漢字發展史的基礎工作,也是漢語字詞關係研究的關鍵性問題。文獻古籍受多種因素的影響,用字情況呈現鮮明的層累性,同時文本、後時文本、泛時性釋字材料都可用於字符斷代,但它們的價值和效用不同。在文本材料真實有效的前提下,還需利用典型主證法、字料剝離法、分布統計法、綜合佐證法、異文比勘法、同詞類證法等多種手段對文本用字進行綜合分析,才能保證斷代結論的準確可靠。
 ”,楚文字或作“梪”等,秦統一後追加義符記作“樹”,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則簡化記作“树”。 其次,文本用字存在“當代化”的現象。創作於前代的文獻流傳至後代,古字不爲人所識,爲破除理解障礙,以整理時代的社會通用字替换古字,已然成爲古籍整理的慣例,這種現象稱之爲用字“當代化”。李榮(2012:80)指出:“傳世古籍屢經抄刊,屢經‘當代化’。某字某種演變始於何時往往無法查考,始見於何書也難於查考。我們只能一面採用前人的說法,一面根據文獻來驗證補充。”太田辰夫(1987:375)也說:“看來把文字改成時髦的,這一點,從古到今所有的校訂者無一例外地一直在做。”如北魏賈思勰《齊民要術》卷一《種穀第三》:“率多人者,田日三十畝;少者十三畝。以故田多墾辟。”同是記録地積單位{畝},南宋紹興龍舒本作“畮”,明汲古閣津逮秘書本作“畝”。明刊本作“畝”疑是改字應是有道理的,明代著作明代刊刻的同時文本普遍作“畝”,宋元以前習用“畮”或“畝”字。 再次,文本的特殊形成過程使文獻用字呈現滯後性,記録某詞棄相應時代習用字不用而以古字記録。文本輾轉傳抄或改編均有所本,傳抄刊刻或改編過程中有意無意都會受到底本用字習慣的影響。因此改編自前代的文本往往會保留前代的用字習慣,轉抄轉刻形成的古籍雖然經歷了用字“當代化”的過程,前代的用字習慣常會有改之未盡的情況。如周朋升(2010)研究發現今本《墨子》雖經歷代改寫,某些詞語却保留了戰國時期的用字習慣,可與出土文獻相互印證。又如馬楠(2013)發現敦煌写本P.3315《尚書釋文》所據作音義者爲梅賾所獻《古文尚書傳》,從中可見梅本“古文”多與正始石經古文或《說文》正篆、古文相合,並存在根據《說文》古文偏旁更造隸古奇字的現象,也往往與戰國文字相合,密合程度甚至超過正始石經和《說文》古文。
”,楚文字或作“梪”等,秦統一後追加義符記作“樹”,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則簡化記作“树”。 其次,文本用字存在“當代化”的現象。創作於前代的文獻流傳至後代,古字不爲人所識,爲破除理解障礙,以整理時代的社會通用字替换古字,已然成爲古籍整理的慣例,這種現象稱之爲用字“當代化”。李榮(2012:80)指出:“傳世古籍屢經抄刊,屢經‘當代化’。某字某種演變始於何時往往無法查考,始見於何書也難於查考。我們只能一面採用前人的說法,一面根據文獻來驗證補充。”太田辰夫(1987:375)也說:“看來把文字改成時髦的,這一點,從古到今所有的校訂者無一例外地一直在做。”如北魏賈思勰《齊民要術》卷一《種穀第三》:“率多人者,田日三十畝;少者十三畝。以故田多墾辟。”同是記録地積單位{畝},南宋紹興龍舒本作“畮”,明汲古閣津逮秘書本作“畝”。明刊本作“畝”疑是改字應是有道理的,明代著作明代刊刻的同時文本普遍作“畝”,宋元以前習用“畮”或“畝”字。 再次,文本的特殊形成過程使文獻用字呈現滯後性,記録某詞棄相應時代習用字不用而以古字記録。文本輾轉傳抄或改編均有所本,傳抄刊刻或改編過程中有意無意都會受到底本用字習慣的影響。因此改編自前代的文本往往會保留前代的用字習慣,轉抄轉刻形成的古籍雖然經歷了用字“當代化”的過程,前代的用字習慣常會有改之未盡的情況。如周朋升(2010)研究發現今本《墨子》雖經歷代改寫,某些詞語却保留了戰國時期的用字習慣,可與出土文獻相互印證。又如馬楠(2013)發現敦煌写本P.3315《尚書釋文》所據作音義者爲梅賾所獻《古文尚書傳》,從中可見梅本“古文”多與正始石經古文或《說文》正篆、古文相合,並存在根據《說文》古文偏旁更造隸古奇字的現象,也往往與戰國文字相合,密合程度甚至超過正始石經和《說文》古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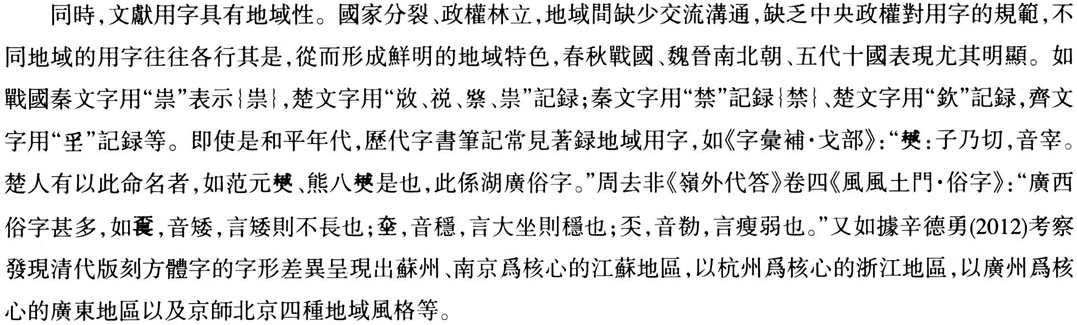 此外,文獻用字帶有集團或個人的用字特徵,武周新字、新莽和太平天國的特殊用字俱是其例。文字的使用者是“人”,用字者的主觀偏好時刻影響着文本的用字呈現。作爲國家的統治者,他們對文字構形理據的特殊認識以及個人喜好都會對文本用字產生直接影響。如王觀國《學林》:“明皇不好隸古,天寶三載,詔集賢學土衛包改《古文尚書》從今文,故有《今文尚書》,今世所傳《尚書》,乃《今文尚書》也。《今文尚書》多用俗字,如改說爲悅,改景爲影之類,皆用後世俗書,良因明皇不好隸古,故有司亦隨俗鹵莽而改定也。”崇尚典雅古樸的社會文化心理普遍存在於各個時期,文人雅士重視傳統繼承和文字構形理據,或是出於炫耀學識的需要,用字偏好古字,已被文獻的實際用字面貌所檢驗。《清稗類鈔·文學類》:“且我國文人好用古字,故每爲文,常搜羅古書中之僻字而用之,以爲矜奇。而其所用之字,自皆有本原,人於是皆以爲博,曾未敢有以杜撰之字爲文者也。”又如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二十八:“今就毛版《史》《漢》考之,《史記》多俗字,《漢書》多古字。”《漢書》成書時代晚於《史記》,用字却更趨古雅,與作者班固的個人用字“崇古”的習慣是分不開的。
此外,文獻用字帶有集團或個人的用字特徵,武周新字、新莽和太平天國的特殊用字俱是其例。文字的使用者是“人”,用字者的主觀偏好時刻影響着文本的用字呈現。作爲國家的統治者,他們對文字構形理據的特殊認識以及個人喜好都會對文本用字產生直接影響。如王觀國《學林》:“明皇不好隸古,天寶三載,詔集賢學土衛包改《古文尚書》從今文,故有《今文尚書》,今世所傳《尚書》,乃《今文尚書》也。《今文尚書》多用俗字,如改說爲悅,改景爲影之類,皆用後世俗書,良因明皇不好隸古,故有司亦隨俗鹵莽而改定也。”崇尚典雅古樸的社會文化心理普遍存在於各個時期,文人雅士重視傳統繼承和文字構形理據,或是出於炫耀學識的需要,用字偏好古字,已被文獻的實際用字面貌所檢驗。《清稗類鈔·文學類》:“且我國文人好用古字,故每爲文,常搜羅古書中之僻字而用之,以爲矜奇。而其所用之字,自皆有本原,人於是皆以爲博,曾未敢有以杜撰之字爲文者也。”又如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二十八:“今就毛版《史》《漢》考之,《史記》多俗字,《漢書》多古字。”《漢書》成書時代晚於《史記》,用字却更趨古雅,與作者班固的個人用字“崇古”的習慣是分不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