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图书馆机构用户,欢迎您!
在藤原定家“有心”诗学体系中,“定家十体”的诗体学占据重要地位。其中“有心体”与“事可然体”起到统领作用,概括来说,含蓄蕴籍的思想内容与道法自然的表现方法是二种和歌体的核心。“事可然体”的“可然”有“赞许”之义,包括和歌的题材、立意、构思等方面,更重要的是崇真贵实、无意为文、思与境谐等和歌创作的审美思维。“事可然体”的主要诗学特征是“崇真贵实”,表达真情实感,或宇宙人生的摄理法则:在表达技巧层面上朴实无华,摒弃矫饰雕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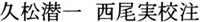 ,1973:126)。日本学者久松潜一(1963:78)将“定家十体”分成四类,即“创作态度”“知性内容”“感性内容”“统一纲领”。“有心体”与“事可然体”为统摄“定家十体”的总纲领,关乎和歌的本体论内容。 “可然”原本是和歌的批评用语——“判词”。“事可然”“理可然”“心可然”等用语由藤原俊成首创,藤原定家继承了其父歌学思想,创立了“事可然体”。简单来说,“事可然体”最主要的诗学特征可用“崇真贵实”四个字概括,表达诗人的真情实感,以及宇宙人生的摄理法则,从而引发读者的情感共鸣;其次,在表达技巧层面上具有朴实无华、清新自然、摒弃矫饰雕琢等特征。 限于篇幅原因,本文对“事可然体”与“有心体”的关系不展开论述,而是围绕“事可然体”进行讨论。“事可然体”除了是一种诗体之外,还包括多个方面内容,主要有创作思想、审美风格、表现方法等内容。纪贯之《假名序》云:“和歌者,以(人)心为种子”(转自
,1973:126)。日本学者久松潜一(1963:78)将“定家十体”分成四类,即“创作态度”“知性内容”“感性内容”“统一纲领”。“有心体”与“事可然体”为统摄“定家十体”的总纲领,关乎和歌的本体论内容。 “可然”原本是和歌的批评用语——“判词”。“事可然”“理可然”“心可然”等用语由藤原俊成首创,藤原定家继承了其父歌学思想,创立了“事可然体”。简单来说,“事可然体”最主要的诗学特征可用“崇真贵实”四个字概括,表达诗人的真情实感,以及宇宙人生的摄理法则,从而引发读者的情感共鸣;其次,在表达技巧层面上具有朴实无华、清新自然、摒弃矫饰雕琢等特征。 限于篇幅原因,本文对“事可然体”与“有心体”的关系不展开论述,而是围绕“事可然体”进行讨论。“事可然体”除了是一种诗体之外,还包括多个方面内容,主要有创作思想、审美风格、表现方法等内容。纪贯之《假名序》云:“和歌者,以(人)心为种子”(转自 ,1981:15)。细分起来,此文中的“心”字包括“人心”(主观)与“歌心”(客观)两方面内容,可以理解为思想、感情、哲理、真理等。好的诗歌必须具备深刻的思想,正如古人所说:“以意为主”“以意取胜”;但思想内容还必须依靠好的形式表达。因此,纪贯之主张“心词相兼”或“花实相兼”(转自实方清,1974:2-3),这与孔子提倡的“文质斌斌”是同一个道理。 如果只是在“文质说”“文意说”的层面上来谈“事可然体”则未免简单了。按字面的意思,“事可然体”的“事可然”是“值得赞许”之义,和歌的内容当然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则是表现的形式与技巧,尤其是审美思维。“事可然体”的构成要素有“正确”“真诚”“率直”等主观性思想,再加上客观理性的巧妙制衡,不偏不依,心与物游,思与境偕,暗合道家“道法自然”“法天贵真”的审美思想。 一、“崇真尚实”:生命意识的觉醒 古代日本人认为语言中存在一种神力,称之为“言灵”,具有类似巫术咒语的效力,“makoutou”一词源于“言灵”信仰,借用“真”“诚”“实”等汉字作为表记符号,日本文学自古有“崇真尚实”的传统思想(叶渭渠 唐月梅,2004:56)。“崇真尚实”的文学传统在《万叶集》时代表现得最为显著,到了《古今集》时代,纪贯之等人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秉持“以心为先”的创作理念,强调真情实感的抒发。然而“诗赋欲丽”(曹丕语)是诗歌追求形式学的原动力,日本十二世纪《后拾遗和歌集》时期,形式主义诗风也一度泛滥,犹如齐梁宫体的“俪采百字之偶 争价一句之奇”(刘勰语)。藤原定家《近代秀歌》中感叹道:“往昔纪贯之,歌心精妙,格调(后人)难及,崇尚壮词、歌姿(兴象)优美之歌体,不作余情妖艳(婉丽)之体。……但世风日下,人心衰退,格调渐靡,文词变鄙”(笔者译)(久松潜一校注,1973:99)。 熟悉日本历史的人都知道,平安朝后期宫廷内斗使日本社会陷入了动乱,“摄政关白”(外戚干政)与“院政”(太上皇干政)削弱了王权,武士阶层趁机崛起,1192年镰仓幕府建立,日本进入了中世社会。这一时期的天灾人祸恰好印证了1052年日本社会已经进入了末法时代的事实(森新之介,2009)。正如鲁迅先生(2005:194)《中国小说史略》中所说:“悲凉之雾,遍被华林。呼吸领会之,唯宝玉而已”。同样,日本王朝贵族对大厦将倾痛彻心扉却无能为力,一部分人或遁入空门或隐居草庵,隐逸文学格外盛行;另一部分人以藤原定家为代表,宣称“红旗征戎非吾事”,视和歌创作为“花鸟之使”,表面上“嘲风雪、弄花草”,但内心痛苦不堪,对现实极度不满。正因为如此,为了寻求心理补偿,他们创作的和歌充满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色调,浓丽细婉的“妖艳美”成为《新古今和歌集》的时代风格。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种现象表明了日本中世贵族文人的生命意识开始觉醒,他们开始关注个我的生命体验与人生感悟,和歌已不再是“润色鸿业”“宜登公宴”之物,和歌创作也不再是“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籍谈笑”(刘勰语)的文人集团的社交工具。从这种意义上说,个性化创作的时代到来了。此外,仁和年间(885-889),光孝天皇主办了现存日本的最早歌合——《民部卿行平家歌合》,所谓“歌合”(赛诗会),左歌与右歌为一组,就同一诗题即兴或事先创作,由“判者”作出胜负评判,这种“判词”往往体现出评委个人或文人集团的审美思想与价值取向。早期的“歌合”出于社交与娱乐目的,平安时代后期的和歌诗人则非常看中比赛的胜负,而且以王室与公卿贵族为主的“堂上派”文人频繁举行“歌合”,客观上促进了和歌艺术的发展与繁荣。
,1981:15)。细分起来,此文中的“心”字包括“人心”(主观)与“歌心”(客观)两方面内容,可以理解为思想、感情、哲理、真理等。好的诗歌必须具备深刻的思想,正如古人所说:“以意为主”“以意取胜”;但思想内容还必须依靠好的形式表达。因此,纪贯之主张“心词相兼”或“花实相兼”(转自实方清,1974:2-3),这与孔子提倡的“文质斌斌”是同一个道理。 如果只是在“文质说”“文意说”的层面上来谈“事可然体”则未免简单了。按字面的意思,“事可然体”的“事可然”是“值得赞许”之义,和歌的内容当然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则是表现的形式与技巧,尤其是审美思维。“事可然体”的构成要素有“正确”“真诚”“率直”等主观性思想,再加上客观理性的巧妙制衡,不偏不依,心与物游,思与境偕,暗合道家“道法自然”“法天贵真”的审美思想。 一、“崇真尚实”:生命意识的觉醒 古代日本人认为语言中存在一种神力,称之为“言灵”,具有类似巫术咒语的效力,“makoutou”一词源于“言灵”信仰,借用“真”“诚”“实”等汉字作为表记符号,日本文学自古有“崇真尚实”的传统思想(叶渭渠 唐月梅,2004:56)。“崇真尚实”的文学传统在《万叶集》时代表现得最为显著,到了《古今集》时代,纪贯之等人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秉持“以心为先”的创作理念,强调真情实感的抒发。然而“诗赋欲丽”(曹丕语)是诗歌追求形式学的原动力,日本十二世纪《后拾遗和歌集》时期,形式主义诗风也一度泛滥,犹如齐梁宫体的“俪采百字之偶 争价一句之奇”(刘勰语)。藤原定家《近代秀歌》中感叹道:“往昔纪贯之,歌心精妙,格调(后人)难及,崇尚壮词、歌姿(兴象)优美之歌体,不作余情妖艳(婉丽)之体。……但世风日下,人心衰退,格调渐靡,文词变鄙”(笔者译)(久松潜一校注,1973:99)。 熟悉日本历史的人都知道,平安朝后期宫廷内斗使日本社会陷入了动乱,“摄政关白”(外戚干政)与“院政”(太上皇干政)削弱了王权,武士阶层趁机崛起,1192年镰仓幕府建立,日本进入了中世社会。这一时期的天灾人祸恰好印证了1052年日本社会已经进入了末法时代的事实(森新之介,2009)。正如鲁迅先生(2005:194)《中国小说史略》中所说:“悲凉之雾,遍被华林。呼吸领会之,唯宝玉而已”。同样,日本王朝贵族对大厦将倾痛彻心扉却无能为力,一部分人或遁入空门或隐居草庵,隐逸文学格外盛行;另一部分人以藤原定家为代表,宣称“红旗征戎非吾事”,视和歌创作为“花鸟之使”,表面上“嘲风雪、弄花草”,但内心痛苦不堪,对现实极度不满。正因为如此,为了寻求心理补偿,他们创作的和歌充满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色调,浓丽细婉的“妖艳美”成为《新古今和歌集》的时代风格。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种现象表明了日本中世贵族文人的生命意识开始觉醒,他们开始关注个我的生命体验与人生感悟,和歌已不再是“润色鸿业”“宜登公宴”之物,和歌创作也不再是“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籍谈笑”(刘勰语)的文人集团的社交工具。从这种意义上说,个性化创作的时代到来了。此外,仁和年间(885-889),光孝天皇主办了现存日本的最早歌合——《民部卿行平家歌合》,所谓“歌合”(赛诗会),左歌与右歌为一组,就同一诗题即兴或事先创作,由“判者”作出胜负评判,这种“判词”往往体现出评委个人或文人集团的审美思想与价值取向。早期的“歌合”出于社交与娱乐目的,平安时代后期的和歌诗人则非常看中比赛的胜负,而且以王室与公卿贵族为主的“堂上派”文人频繁举行“歌合”,客观上促进了和歌艺术的发展与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