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图书馆机构用户,欢迎您!
敦煌博物馆藏敦煌文献77号《坛经》等五种禅籍合抄,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并被定为“归义军时期写本”。其中的后一种唐释净觉《注心经》写本不但抄手、行款、标识符号与前四种不同,而且该本出现了 (薩)、
(薩)、 (留)、数(數)、灯(燈)、还(還)、
(留)、数(數)、灯(燈)、还(還)、 (離)、斍(覺)、顕(顯)、尽(盡)、国(國)、宝(寶)等一批可靠的敦煌写本罕见甚至未见的俗字,这些俗字大多是宋代甚至元代以后才产生的。因此,《注心经》写本未必是莫高窟藏经洞之物,而很可能是元代以后甚至近人补抄的。
(離)、斍(覺)、顕(顯)、尽(盡)、国(國)、宝(寶)等一批可靠的敦煌写本罕见甚至未见的俗字,这些俗字大多是宋代甚至元代以后才产生的。因此,《注心经》写本未必是莫高窟藏经洞之物,而很可能是元代以后甚至近人补抄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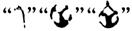 等篇名标识符号,而后一种文献篇题前则没有任何符号。前四种文献字句重文重出者大抵用重文符号代替,而后一种文献则一般不用重文符号。可见二者抄写格式也有很大区别。至于这五种禅籍的抄写年代,荣新江、邓文宽(1994)主要根据其中《坛经》写本的形制、方音别字、抄写特点等的比较考察,“推测敦博本禅籍抄成于张氏归义军时期”。上引《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定为“归义军时期写本”,大概就是沿袭了荣、邓二位的说法。如果限于出自同一个书手的前四种文献,这一推断也许不无道理,但出自另一书手的后一种文献,由于其用字用词及抄写格式方面与前四种文献并无共同之处(参下节),这一推断的可靠性就很成问题了。 关于后一种文献的来源,大家都注意到了尾题“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卷终”后比丘光范的跋文。 遗法比丘光范幸于末代荻偶真诠,伏睹经意明明,兼认注文了了。授之滑汭,藏保筐箱。或一披寻,即喜顶荷。旋忘二执,潜晓三空,实众法之源,乃诸佛之母。无价大宝,今喜遇之;苟自利而不济他,即滞理而成吝法。今即命工雕印,永冀流通。凡(后缺) 此号原件本为敦煌当地的收藏家任子宜所藏④。卷中《南阳和上顿教解脱禅门直了性坛语》篇题前有“民国廿四年四月八日获此经于敦煌千佛山之上寺任子宜敬志”题记一行。1943、1944年,向达到西北考察,曾先后两次向任氏借录该件,其中后一过录本跋云:“未有比丘光范跋,谓命工雕印,永冀流传云云。不知为雕印四种,抑仅指净觉《心经》而言,惜有缺叶,不知原本雕于何时,唯据写本字体及书写格式推之,最早不能过于五代也。……净觉《注心经》则为久佚之籍,北宗渐教法门,由此可以略窥一二,治禅宗史者之要典也。”(转引自邓文宽、荣新江,1998:14-15)向氏后来据这两次考察日记整理刊布的《西征小记》也说:“光范《跋》缺一叶,不知仅刻《心经》一种,抑兼指前三者而言。任君所藏,当是五代或宋初传抄本,每半叶六行,尚是《宋藏》格式也。……净觉注《心经》,首有行荆州(原注:荆原作全,误)⑤长史李知非序,从知此注作于开元十五年。净觉乃神秀门人,书为《大藏》久佚之籍,北宗渐教法门由此可窥一二。”(向达,1987:333)杨曾文(1989:36)认为光范所作只是《注心经》的跋文,而不包括前几种抄本,而光范得到《注心经》的地点“滑汭”,当为洛阳东北的滑州治所白马(滑台)。周绍良也说:“我觉得光范跋文明白说到‘经意明明’,‘注文了了’,可见是专指《心经》而言,并没有指其它一些。五个重要经典汇集在一个册子上,首先它不同于敦煌石室所藏的一些卷轴,它是一个方册本子,所以很可能是从外地赍来的,而且这个抄本明显是一个比较晚的抄本。”(转引自邓文宽、荣新江,1998:3-4)邓文宽、荣新江(1998:28-29)在杨说的基础上推测“光范是洛阳一带的和尚,他命工雕印《注心经》的地点,也应在洛阳附近。敦博本《注心经》并非光范原印本,而是抄自光范印本,也就是说抄自来源于洛阳一带的印本。……虽然《注心经》及其跋文的字体与前四种文献的笔迹不同,但它们订成一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光范的跋文虽然不包含前四种文献,但也透露出同样来自洛阳一带的可能性”。
等篇名标识符号,而后一种文献篇题前则没有任何符号。前四种文献字句重文重出者大抵用重文符号代替,而后一种文献则一般不用重文符号。可见二者抄写格式也有很大区别。至于这五种禅籍的抄写年代,荣新江、邓文宽(1994)主要根据其中《坛经》写本的形制、方音别字、抄写特点等的比较考察,“推测敦博本禅籍抄成于张氏归义军时期”。上引《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定为“归义军时期写本”,大概就是沿袭了荣、邓二位的说法。如果限于出自同一个书手的前四种文献,这一推断也许不无道理,但出自另一书手的后一种文献,由于其用字用词及抄写格式方面与前四种文献并无共同之处(参下节),这一推断的可靠性就很成问题了。 关于后一种文献的来源,大家都注意到了尾题“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卷终”后比丘光范的跋文。 遗法比丘光范幸于末代荻偶真诠,伏睹经意明明,兼认注文了了。授之滑汭,藏保筐箱。或一披寻,即喜顶荷。旋忘二执,潜晓三空,实众法之源,乃诸佛之母。无价大宝,今喜遇之;苟自利而不济他,即滞理而成吝法。今即命工雕印,永冀流通。凡(后缺) 此号原件本为敦煌当地的收藏家任子宜所藏④。卷中《南阳和上顿教解脱禅门直了性坛语》篇题前有“民国廿四年四月八日获此经于敦煌千佛山之上寺任子宜敬志”题记一行。1943、1944年,向达到西北考察,曾先后两次向任氏借录该件,其中后一过录本跋云:“未有比丘光范跋,谓命工雕印,永冀流传云云。不知为雕印四种,抑仅指净觉《心经》而言,惜有缺叶,不知原本雕于何时,唯据写本字体及书写格式推之,最早不能过于五代也。……净觉《注心经》则为久佚之籍,北宗渐教法门,由此可以略窥一二,治禅宗史者之要典也。”(转引自邓文宽、荣新江,1998:14-15)向氏后来据这两次考察日记整理刊布的《西征小记》也说:“光范《跋》缺一叶,不知仅刻《心经》一种,抑兼指前三者而言。任君所藏,当是五代或宋初传抄本,每半叶六行,尚是《宋藏》格式也。……净觉注《心经》,首有行荆州(原注:荆原作全,误)⑤长史李知非序,从知此注作于开元十五年。净觉乃神秀门人,书为《大藏》久佚之籍,北宗渐教法门由此可窥一二。”(向达,1987:333)杨曾文(1989:36)认为光范所作只是《注心经》的跋文,而不包括前几种抄本,而光范得到《注心经》的地点“滑汭”,当为洛阳东北的滑州治所白马(滑台)。周绍良也说:“我觉得光范跋文明白说到‘经意明明’,‘注文了了’,可见是专指《心经》而言,并没有指其它一些。五个重要经典汇集在一个册子上,首先它不同于敦煌石室所藏的一些卷轴,它是一个方册本子,所以很可能是从外地赍来的,而且这个抄本明显是一个比较晚的抄本。”(转引自邓文宽、荣新江,1998:3-4)邓文宽、荣新江(1998:28-29)在杨说的基础上推测“光范是洛阳一带的和尚,他命工雕印《注心经》的地点,也应在洛阳附近。敦博本《注心经》并非光范原印本,而是抄自光范印本,也就是说抄自来源于洛阳一带的印本。……虽然《注心经》及其跋文的字体与前四种文献的笔迹不同,但它们订成一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光范的跋文虽然不包含前四种文献,但也透露出同样来自洛阳一带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