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图书馆机构用户,欢迎您!
艺术文化在南斯拉夫就如同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政治事业。而马克思主义既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手中的官方意识形态,也是批判表达领域的官方意识形态。当南斯拉夫解体为新的民族国家,由社会主义转向资本主义之时,文化领域失去了其意识形态方面的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也几乎从公共领域消失了。马克思主义的地位则被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所取代,尽管这一地位也不如从前那样重要。然而,这一危机给了边缘化的马克思主义以兴起的机会,成为一种有说服力、创造力并可能具有实践影响力的思维方式。在社会主义时期,审美马克思主义是对官方文化意识形态做出的乌托邦式批判,并与官方文化意识形态争夺马克思主义正统的地位。然而在危机的时期,马克思主义方法的元素则几乎是由艺术家们自己契合于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美学/反美学之中。艺术家们并不寻求正统性,而是寻求实践的答案:在从晚期资本主义向后资本主义转变的过程中,艺术可以做些什么?艺术是否可以再次拥抱某种形式的审美乌托邦?然而,这些尝试并没有找到答案,而是陷入了“化圆为方”的境地之中。他们在美学和艺术中所造成的乃是所谓的真实的乌托邦——同时包含了现代性其矛盾的双方(an oxymoron of contemporaneity)。 为了揭示审美马克思主义领域的转变以及其乌托邦视角,文章将按照下列四个步骤逐步展开: 第一,20世纪70年代时南斯拉夫的审美马克思主义及其乌托邦特征; 第二,20世纪80年代时后现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及乌托邦的抹消; 第三,向议会民主制的资本主义以及新的民族国家进行转变:针对文化丧失其政治重要性的颠覆性的艺术行动主义; 第四,近十年的危机:马克思主义的重生以及艺术的/审美的“化圆为方”。
 Summer School)的存在于1964年至1974年间是得到首肯的。但在1974年,杂志被停刊,夏令学园也被迫停办,学派中的一些南斯拉夫成员则被打压迫害,然而他们却始终没有完全消失在公共视野之外。贝尔格莱德的实践派教授们丢掉了大学的工作,并被勒令不得开课,随后他们被调到研究机构从事他们想做的工作(愿意的话,他们也可以什么都不做),但是在一段时间内不得出版任何著作。这是另一种保证威权权力的典型的南斯拉夫方式。 知识话语和文化话语的自治以很多的方式表达了出来,其中包括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式,也包括对于涵盖了南斯拉夫式的审美马克思主义及审美乌托邦在内的未完成的革命的批判。这一切都开始于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实践派也就得名于此。 1960至1974年间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可以通过三位不同作家而加以概括:《实践》杂志萨格勒布支部的丹科·格尔里奇(Danko
Summer School)的存在于1964年至1974年间是得到首肯的。但在1974年,杂志被停刊,夏令学园也被迫停办,学派中的一些南斯拉夫成员则被打压迫害,然而他们却始终没有完全消失在公共视野之外。贝尔格莱德的实践派教授们丢掉了大学的工作,并被勒令不得开课,随后他们被调到研究机构从事他们想做的工作(愿意的话,他们也可以什么都不做),但是在一段时间内不得出版任何著作。这是另一种保证威权权力的典型的南斯拉夫方式。 知识话语和文化话语的自治以很多的方式表达了出来,其中包括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式,也包括对于涵盖了南斯拉夫式的审美马克思主义及审美乌托邦在内的未完成的革命的批判。这一切都开始于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实践派也就得名于此。 1960至1974年间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可以通过三位不同作家而加以概括:《实践》杂志萨格勒布支部的丹科·格尔里奇(Danko  )与他的《美学》四卷本;来自贝尔格莱德的斯雷坦·彼得洛维奇(Sreten
)与他的《美学》四卷本;来自贝尔格莱德的斯雷坦·彼得洛维奇(Sreten  ),他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美学》一书对实践派的历史进行了阐释;米兰·达姆尼亚诺维奇(Milan
),他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美学》一书对实践派的历史进行了阐释;米兰·达姆尼亚诺维奇(Mil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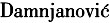 )的《本质和历史》与他的其他作品表明他反对自认为自己是哲学的终结,并将美学从哲学学科中剔除出去的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
)的《本质和历史》与他的其他作品表明他反对自认为自己是哲学的终结,并将美学从哲学学科中剔除出去的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