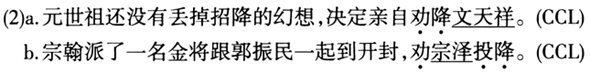一、引言:汉语词法结构与句法结构的同构异构关系 关于汉语词法结构与句法结构关系的研究,从大的格局来看,一般认为,两者之间具有一致性(如赵元任,1948、1968;吕叔湘、朱德熙,1952;陆志韦等,1957;任学良,1981;李行健,1982;朱德熙,1982;汤廷池,1991等,以及大多数《现代汉语》教材)。最有代表性的说法如朱德熙(1982:32):“复合是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根成分组成合成词的构词方式。用复合方式构成的合成词叫复合词。汉语复合词的组成成分之间的结构关系基本上是和句法结构关系一致的。句法结构关系有主谓、述宾、述补、偏正、联合等等,绝大部分复合词也是按照这几类结构关系组成的。”这种共时性认识跟“今天的词法是昨天的句法”(Givón,1971)的历时性认识在基本观念上是一致的,但更能显示出两者在构造过程上的同构性。这正如李行健(1982)指出的那样:汉语的复合词“大多是由词组演变而来的,因此,它们的结构规律同句法是一致的”。这种认识实际是从句法来看词法,而且将词素间语义关系的分析放在从属的地位(虽然句法关系的确定离不开语义关系的分析)。 然而,学界同时也看到,汉语复合词词素的结合是相当有灵活性的,不能简单地用句法结构来比附复合词词法结构(如孙常叙,1956;戴昭铭,1988;刘叔新,1990;黎良军,1995;徐通锵,1997;王宁,1999、2008;周荐,2004;朱彦,2004;李运富,2010;苏宝荣,2016)。总体而言,这种认识往往重视词素(字本位理论中则为字)之间语义关系的分析,同时重视复合词复合之源的考察,这样就必然重视那些经过非句法规则运作而成的复合词,而且关注词素意义与复合词整体意义之间的关系。如王宁(1999)指出:“现代汉语造句法与构词法不是同一的关系,而是互补的关系。它们不是共时语法的两个层次,而是实质不同的两个领域的语言结构,二者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不能用同一方式分析。”贺阳、崔艳蕾(2012)进一步指出:“汉语复合词结构和句法结构既有一致性,也有差异性,二者的异同在很大程度上与词汇化过程有关。”当然,人们也认识到,不考虑短语缩略和跨层整合等非词法因素,复合词词法结构与句法结构又确有相通之处,大多数复合词来自短语的词汇化(lexicalization)。正如沈家煊(2006a)基于当代语言类型学观念所考察的那样,语言词法类型和句法类型的联系有强有弱,相对而言,“汉语是(两者)联系比较强和直接的语言”。当然,这种联系的强弱和直接间接,除了原则层面的阐释,还需要对具体现象进行精细考察。 本文暂不考虑一般认为的词法跟句法结构关系不一致的地方,而重点考察一般认为两者相对一致的情况。然而,我们并非再次论证这种一致性,而是通过深入探讨结构内部的类型多样性和复杂性,来进一步考察一致中的差异,同构中的异构,进而阐释句法结构词法化(morphologization)的可能性以及词法结构词汇化的空间,即词法化、词汇化的组构性和能产性及其相关问题(如使用频率对词汇化的作用及其限度)。下面我们先看几个具体例子。 学界认识到汉语复合词词素间的结构关系和短语的结构关系具有一致性,是从大的构造类型(即主谓、述宾、述补、偏正、联合)来着眼的,然而,如果我们深入到特定结构类型的内部,会发现两者之间在基本关系一致的前提下也呈现出不一致的地方。例如: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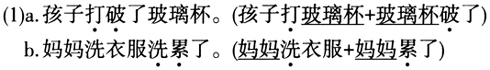
其中的“打破”和“洗累”都是句法层面上的述补结构(此为动结式)。在构词法中也有述补式,如“提高、阐明”,但其语义结构类型只是跟“打破”相同(即“打”的客体论元跟“破”的主体论元所指相同),而跟“洗累”的语义结构类型(即“洗”的主体论元跟“累”的主体论元所指相同)有所区别。就“洗累”而言,“洗”的对象“衣服”并不能出现在“洗累”之后,即不能形成“妈妈洗累了衣服”这样的表达;但“衣服”可以作为致事(Causer)出现在由“洗累”构成的“把”字句中,如“(这一大堆)

把妈妈洗累了”。而“打破”的用法正好与此相反,不能形成“玻璃杯把孩子打破了”这样的表达。出现这样互补用法的根本原因,就是这两个述补结构的内部语义关系并不相同;两者是否具有成词可能性也受此约束。由此可见,高层结构关系相同的复合结构能否成词,受其底层内部语义结构关系的制约。这是问题的一方面。 另一方面,一般在概括词法和句法的结构类型基本一致时,都是从主谓、述宾、述补、联合、偏正这五种来考虑的。如果扩大考察的类型,就会发现新的问题。例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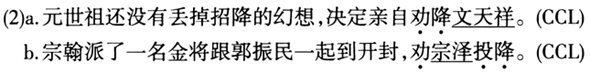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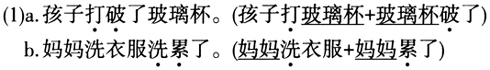 其中的“打破”和“洗累”都是句法层面上的述补结构(此为动结式)。在构词法中也有述补式,如“提高、阐明”,但其语义结构类型只是跟“打破”相同(即“打”的客体论元跟“破”的主体论元所指相同),而跟“洗累”的语义结构类型(即“洗”的主体论元跟“累”的主体论元所指相同)有所区别。就“洗累”而言,“洗”的对象“衣服”并不能出现在“洗累”之后,即不能形成“妈妈洗累了衣服”这样的表达;但“衣服”可以作为致事(Causer)出现在由“洗累”构成的“把”字句中,如“(这一大堆)
其中的“打破”和“洗累”都是句法层面上的述补结构(此为动结式)。在构词法中也有述补式,如“提高、阐明”,但其语义结构类型只是跟“打破”相同(即“打”的客体论元跟“破”的主体论元所指相同),而跟“洗累”的语义结构类型(即“洗”的主体论元跟“累”的主体论元所指相同)有所区别。就“洗累”而言,“洗”的对象“衣服”并不能出现在“洗累”之后,即不能形成“妈妈洗累了衣服”这样的表达;但“衣服”可以作为致事(Causer)出现在由“洗累”构成的“把”字句中,如“(这一大堆) 把妈妈洗累了”。而“打破”的用法正好与此相反,不能形成“玻璃杯把孩子打破了”这样的表达。出现这样互补用法的根本原因,就是这两个述补结构的内部语义关系并不相同;两者是否具有成词可能性也受此约束。由此可见,高层结构关系相同的复合结构能否成词,受其底层内部语义结构关系的制约。这是问题的一方面。 另一方面,一般在概括词法和句法的结构类型基本一致时,都是从主谓、述宾、述补、联合、偏正这五种来考虑的。如果扩大考察的类型,就会发现新的问题。例如:
把妈妈洗累了”。而“打破”的用法正好与此相反,不能形成“玻璃杯把孩子打破了”这样的表达。出现这样互补用法的根本原因,就是这两个述补结构的内部语义关系并不相同;两者是否具有成词可能性也受此约束。由此可见,高层结构关系相同的复合结构能否成词,受其底层内部语义结构关系的制约。这是问题的一方面。 另一方面,一般在概括词法和句法的结构类型基本一致时,都是从主谓、述宾、述补、联合、偏正这五种来考虑的。如果扩大考察的类型,就会发现新的问题。例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