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图书馆机构用户,欢迎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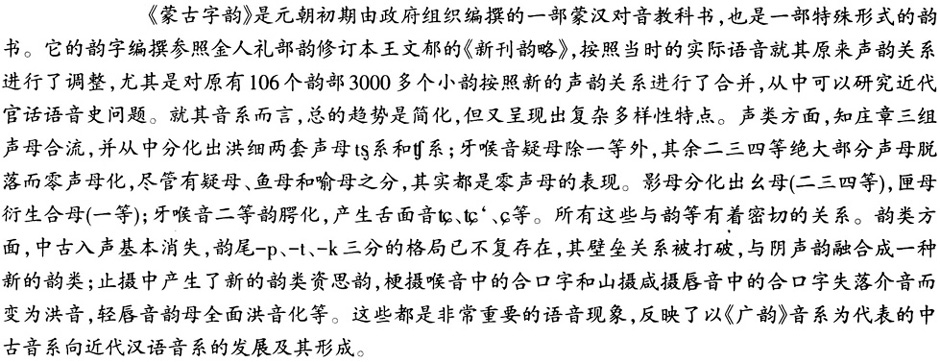
 ]字脱落与喻母字合流;牙喉音二等韵的腭化,资思韵的出现,等等,都是一些值得研究的语音现象。 要研究《蒙古字韵》的语音性质,就必须认真研究其编撰时代及其历史背景。据《元史》,元世祖忽必烈中统元年(1260),命帝师八思巴制定蒙古新字,十年后的至元六年(1269)颁布,并于州县设蒙古字学,教习生员,至元八年改国号为元,因此,《蒙古字韵》的撰作最有可能在此间进行。其为配合蒙古新字的推广而制作,故名曰“蒙古字韵”。因为蒙元帝国刚刚建立,还没有自己的文化官员,当时南宋政权尚处于对峙状态,只能依靠亡金礼部大臣。这些人在编撰时,从实用考虑,只会选择一部现成韵书作为参照,而作为官韵书的修订本《新刊韵略》必在首选之列。根据研究,《蒙古字韵》的韵字收录基本上以《新刊韵略》为基础,这是宁忌浮先生的重大发现。然而《蒙古字韵》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韵字摘录,而是在编排上做了大胆的革新:取消原有106部结构,易以声类为序,四声相承,并从实际语音出发,就其声类、韵类作了必要的分合。 既然如此,我们就必须澄清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个认识误区,以为《蒙古字韵》与《新刊韵略》是同一个韵书体系。其实,它仅仅是利用了《新刊韵略》的韵字,它有自己的编排体例和语音系统,两者完全是不同体系的韵书。 就语音系统而言,《新刊韵略》采用的是《广韵》编排体系,虽然依据《广韵》《集韵》同用独用例合并为106部,但206部的框架并没有改变,反切注音采用的也是《广韵》音系。而《蒙古字韵》不同,它虽然以《新刊韵略》韵字为基础,但它完全改变了其编排体例,以音同音近的关系编排成一组组新的小韵,这些小韵来自《新刊》不同韵部的小韵,如一东部平声“公功工(东)攻(冬)觥觵(庚)肱(登)
]字脱落与喻母字合流;牙喉音二等韵的腭化,资思韵的出现,等等,都是一些值得研究的语音现象。 要研究《蒙古字韵》的语音性质,就必须认真研究其编撰时代及其历史背景。据《元史》,元世祖忽必烈中统元年(1260),命帝师八思巴制定蒙古新字,十年后的至元六年(1269)颁布,并于州县设蒙古字学,教习生员,至元八年改国号为元,因此,《蒙古字韵》的撰作最有可能在此间进行。其为配合蒙古新字的推广而制作,故名曰“蒙古字韵”。因为蒙元帝国刚刚建立,还没有自己的文化官员,当时南宋政权尚处于对峙状态,只能依靠亡金礼部大臣。这些人在编撰时,从实用考虑,只会选择一部现成韵书作为参照,而作为官韵书的修订本《新刊韵略》必在首选之列。根据研究,《蒙古字韵》的韵字收录基本上以《新刊韵略》为基础,这是宁忌浮先生的重大发现。然而《蒙古字韵》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韵字摘录,而是在编排上做了大胆的革新:取消原有106部结构,易以声类为序,四声相承,并从实际语音出发,就其声类、韵类作了必要的分合。 既然如此,我们就必须澄清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个认识误区,以为《蒙古字韵》与《新刊韵略》是同一个韵书体系。其实,它仅仅是利用了《新刊韵略》的韵字,它有自己的编排体例和语音系统,两者完全是不同体系的韵书。 就语音系统而言,《新刊韵略》采用的是《广韵》编排体系,虽然依据《广韵》《集韵》同用独用例合并为106部,但206部的框架并没有改变,反切注音采用的也是《广韵》音系。而《蒙古字韵》不同,它虽然以《新刊韵略》韵字为基础,但它完全改变了其编排体例,以音同音近的关系编排成一组组新的小韵,这些小韵来自《新刊》不同韵部的小韵,如一东部平声“公功工(东)攻(冬)觥觵(庚)肱(登) 玒(东)”一组小韵,就包含了《新刊》东冬庚登四个韵部的韵字(
玒(东)”一组小韵,就包含了《新刊》东冬庚登四个韵部的韵字( 玒二字《新刊》不收,后人补录),又如“中衷忠(陟弓切,知东)、鐘鍾蚣(职容切,章钟)、终螽(职戎,章东)”一组小韵,来自东钟两个韵部三个小韵,知组与照三组已经合流。因此,简单地把《蒙古韵略》看作是《新刊韵略》的同一个韵书体系是错误的。 我们可以这样说,《蒙古字韵》的韵字除了增加的韵字以外,全部来自《新刊韵略》,但在语音系统上却自成体系。它是一个活的语音体系,而《新刊韵略》却是一个旧的韵书体系,所表现的还是《广韵》的中古音系。 这个活的语音体系实质上就是宋金时期北方官话音系统。自从20世纪40年代初苏联学者龙果夫发表《八思巴字与古官话》一文以后,《蒙古字韵》的语音史价值越来越受到中外学者的重视。国内学者中罗常培先生、杨耐思先生和宁忌浮先生以及台湾学者郑再发先生等前辈学者为此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一些青年学者沿着前辈学者开拓的路径继续研究,也卓有成绩,诸如宋洪民、陈鑫海等都有相关研究论文发表。 应该说,经过中外学者数十年的艰苦耕耘,在八思巴字及其时代背景、《蒙古字韵》的文献版本、校勘及音系研究上都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尽管如此,但仍有许多问题需要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可补充发掘的东西还有很多,诸如《蒙古字韵》的内部编撰特点、语音性质与近代语音史的定位,《蒙古字韵》与相关韵书之间的关系,诸如《新刊韵略》《礼部韵略七音三十六母通考》(下简称《通考》)和《古今韵会举要》(下简称《韵会》)等,《蒙古字韵》声韵系统中的问题等等,都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玒二字《新刊》不收,后人补录),又如“中衷忠(陟弓切,知东)、鐘鍾蚣(职容切,章钟)、终螽(职戎,章东)”一组小韵,来自东钟两个韵部三个小韵,知组与照三组已经合流。因此,简单地把《蒙古韵略》看作是《新刊韵略》的同一个韵书体系是错误的。 我们可以这样说,《蒙古字韵》的韵字除了增加的韵字以外,全部来自《新刊韵略》,但在语音系统上却自成体系。它是一个活的语音体系,而《新刊韵略》却是一个旧的韵书体系,所表现的还是《广韵》的中古音系。 这个活的语音体系实质上就是宋金时期北方官话音系统。自从20世纪40年代初苏联学者龙果夫发表《八思巴字与古官话》一文以后,《蒙古字韵》的语音史价值越来越受到中外学者的重视。国内学者中罗常培先生、杨耐思先生和宁忌浮先生以及台湾学者郑再发先生等前辈学者为此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一些青年学者沿着前辈学者开拓的路径继续研究,也卓有成绩,诸如宋洪民、陈鑫海等都有相关研究论文发表。 应该说,经过中外学者数十年的艰苦耕耘,在八思巴字及其时代背景、《蒙古字韵》的文献版本、校勘及音系研究上都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尽管如此,但仍有许多问题需要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可补充发掘的东西还有很多,诸如《蒙古字韵》的内部编撰特点、语音性质与近代语音史的定位,《蒙古字韵》与相关韵书之间的关系,诸如《新刊韵略》《礼部韵略七音三十六母通考》(下简称《通考》)和《古今韵会举要》(下简称《韵会》)等,《蒙古字韵》声韵系统中的问题等等,都有很大的研究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