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词法”类型,“词序”类型,“词类”类型 语言类型研究和语言共性研究可以说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可以这样来理解:类型学是通过比较从结构特点上对语言进行分类;世界上的语言看上去结构千变万化,但是“万变不离其宗”,结构变异要受一定的限制,有些变异类型不可能出现,这种变异的限制就是语言的共性。因此,语言的类型研究和共性研究只是侧重面不同而已:共性研究主要关心语言类型的变化有哪些限制,而类型学主要关心语言有哪些不同的变化类型。但是,说有易,说无难,一时认为不可能有的语言类型不见得真的不存在,只是存在的时间比较短暂或者较为罕见而已。近年来国际语言学界出现“重视语言结构多样性”的趋向。曾经有一句流传很广的名言:“按照乔姆斯基的说法,火星上来访的科学家一定得出结论,除了词汇互相听不懂,地球人说的是同一种语言”(Pinker 1994:232)。语言学的新动向是,很多人开始认识到,要找出语言真正的共性,应该要先充分了解语言结构的多样性,研究的重点应该从一致性转移到多样性上来,这方面可参看Evans和Levinson(2009)发表在《行为和脑科学》杂志上的那篇重要文章。那句名言应该改为:“火星上来访的科学家发现,地球上的生物多种多样,人类所操的语言也多种多样。” 19世纪的语言类型学,重点是研究“词法”类型,从“构词方式”这个变化参项着眼,将语言分为孤立语、粘着语、屈折语,或者分为分析语、综合语、多式综合语等类型。汉语划归孤立语或分析语类型,这是大家都熟知的。 20世纪的语言类型学不满足于词法的类型,从Greenberg(1963)开始,研究重点从词法类型转移到“词序”类型,如动词和宾语的顺序分VO和OV两大类型,形容词和名词的顺序分AN和NA两大类型。研究者认为,词法类型只是对语言局部结构的分类,只观察一个变化参项,而词序类型着眼于多个变化参项及其之间的联系,是对一种语言整体结构的分类,更能反映不同语言的类型特点(Comrie 1981)。“蕴含共性”(implicational universals)是词序类型学中最重要的概念,它能说明语言类型变异所受的普遍限制,其表述形式为P→Q。例如,“如果一种语言的名词(N)位于指代词(Dem)之前,那么名词也位于关系小句(Rel)之前”,用逻辑上的蕴含式表示就是NDem→NRel。这个蕴含式在逻辑上肯定了可能有的四种词序中的三种,即(1)NRel & NDem,(2)NRel & DemN,(3)RelN & DemN,而排除第(4)种RelN & NDem。这就对可能有的语言类型作出了限制,这种限制被认为是一种语言共性。 近年来类型学的研究又从“词序”类型进入“词类”类型。个中的原因是,讲“词序”其实是在讲概括的“词类顺序”,而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个先天不足的问题就逐渐暴露出来,也就是“词类”和“句法成分类”的关系没有厘清。例如常说的SVO(主动宾)和SOV(主宾动)其实是词类(动词)和句法成分类(主语宾语)混杂在一起的,这对于英语和其他一些印欧语来说问题不大,因为这些语言的词类和句法成分类是大致对应的。拿英语来讲,名词对应主宾语,动词对应谓语,形容词对应定语,副词对应状语。然而汉语不同,正如朱德熙(1985:4,64)指出的,汉语的词类和句法成分之间缺乏一一对应的关系。“生成语法”刚刚兴起的时候,朱德熙就敏锐地指出,它那条最基本的句子转写规则S→NP+VP在汉语里“是行不通的”,汉语的事实是: S→NP+VP 我不去。|卖菜的来了。 S→NP+NP 小王上海人。|这本书他的。 S→VP+VP 光哭没用。|不撞墙不罢休。 S→VP+NP 逃,僝头。|不死(今年)一百岁。 这就穷尽了NP和VP加合成句的所有可能。对汉语进行“形式语法”的研究很有必要,但是在开始这种研究之前,最好对这个问题有个说得过去的交代。另外,从陈承泽到赵元任再到朱德熙,汉语语法学界都已经承认汉语的主谓结构可以做谓语,如“象鼻子长、她肚子大了”,那就还需要有一条S→NP+S’(NP-VP)规则,而现行的词序类型学框架却容不下这条规则。那么“羊肉我不吃”这一句,词序到底算是OSV还是SSV呢? 跟这个问题相联系,S、O、V、N、A这些范畴的内涵和外延在语言之间其实有很大的差异,不能一概而论。例如汉语S涵盖的范围要比英语的S大,“今年一百岁”,“今年”是主语,这在英语里就要算作状语了。英语的V只能做谓语,做主宾语的时候要“名词化”或变为非限定形式,而汉语的V几乎都可以做主宾语,做主宾语的时候还是动词,并没有“名词化”,例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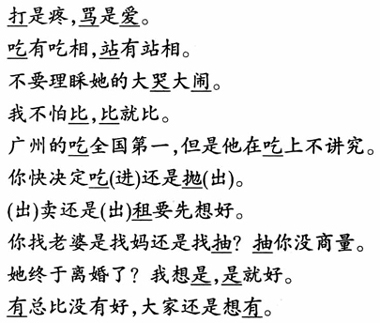
即便是十分抽象的动词“是”和“有”也是如此。跟这个事实直接相关联的是,汉语的A(形容词)不仅修饰名词做定语,也修饰动词做状语,例如“快车”和“快跑”的“快”是同一个“快”,不像英语的A基本上只修饰名词做定语,如要修饰动词做状语,就要加词缀-ly变为副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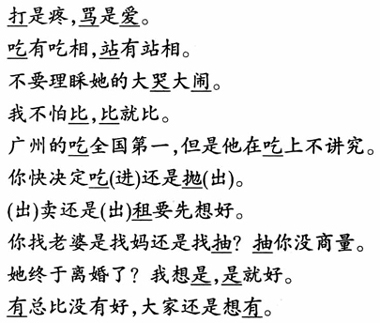 即便是十分抽象的动词“是”和“有”也是如此。跟这个事实直接相关联的是,汉语的A(形容词)不仅修饰名词做定语,也修饰动词做状语,例如“快车”和“快跑”的“快”是同一个“快”,不像英语的A基本上只修饰名词做定语,如要修饰动词做状语,就要加词缀-ly变为副词。
即便是十分抽象的动词“是”和“有”也是如此。跟这个事实直接相关联的是,汉语的A(形容词)不仅修饰名词做定语,也修饰动词做状语,例如“快车”和“快跑”的“快”是同一个“快”,不像英语的A基本上只修饰名词做定语,如要修饰动词做状语,就要加词缀-ly变为副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