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图书馆机构用户,欢迎您!
從古希臘開始,父權制的邏輯就支配着西方美學的建構:男人之美更多地意味着力量、勇敢、強壯,女人則被視爲“較弱的性別”,衹是特定的現實處境使得相應的分野遲遲未能充分展開。到了文藝復興時期,一個悖論式的變化出現了:隨着“人的解放”和經濟的發展,越來越多的女性開始參與公共生活,成爲被頻繁打量的審美客體;同時,由於未能立刻獲得相應的權利,她們依舊衹能以弱者的形象出現於社會空間;反映到美學理論上,崇高(男性)/優美(女性)之類二分法被正式提出並獲得系統表述;這對此後的西方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到了20世紀以後,男/女之別依然對應着大/小、強/弱、高/低等二分法,相關的身體美學仍舊處於分裂狀態。雖然解構性因素早已出現,但由此產生的力量尚難以與主流話語抗衡。如何克服這些根深蒂固的二分法,乃當今世界必須解決的問题。對於中國學者來說,加入到博弈的行列會使漢語美學直面世界性問題,獲得重新出場的重要機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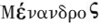 ,前342—前291)的劇本中,讀者甚至可以發現“可愛的面孔”和“甜美的聲音”等針對女性的描述(12)。吊詭的是,此類言說並不多見,聚焦女性的身體美學並未因此誕生。由於不能參與公共生活(如當將軍、政治家、陪審員),女性身體事實上處於隱匿狀態,很難進入大衆的視野,因此,作爲一個性屬—性別的她們並非重要的審美對象。(13)在審美領域,她們被覆蓋和遮蔽:“古希臘人認爲理想的美體現在青少年身上”,“大量的花瓶上刻有‘漂亮的少年’字樣,而‘漂亮的少女’則較少見”。(14)在《理想國》中,柏拉圖曾經興致勃勃地提到雅典人對美少年的偏愛:“你沒看到人們說塌鼻子的‘容貌俏麗’,高鼻子‘儀表堂堂’,鼻子不高不低的則‘長得恰到好處’?”(Republic 474d)(15)如此說話的他關注的是男性,女人的美則難入他的法眼。對於他來說,女性雖然屬於“較弱的性別”,但仍然應該像男人一樣被對待:“在教育問題上和在別的事情上,女性一定要和男性結合在一起。”(《法篇》805c)“立法者應當徹底,不能半心半意,他一定不能在爲男性立法後,就把另一種性別的人當作放蕩的奢侈生活的工具和取樂的對象,這樣做的結果必然使整個社會的幸福生活衹剩下一半。”(《法篇》806c)(16)這種考慮的核心並非女性的福祉,而是其社會功能:“如果城邦的婦女沒有訓練好,乃至於連母雞面對最危險的野獸或其他任何危險冒死保護小雞的勇氣都沒有,如果她們衹是朝着神廟狂奔,坐在祭壇和神龕前,那麼這種表現確實是城邦的奇恥大辱,是人類最卑賤的表現。”(《法篇》814b)(17)柏拉圖所在的雅典人口並不多,小國寡民的現實處境使他不能過於強調男女之別,否則,本就不大的城邦就會衹剩下一半的勞動力。古希臘的女性雖然被限制在家庭中,但仍需部分參與城邦的物質生產。正因爲如此,古希臘思想家傾向於建構統一的身體美學。譬如,寫作《修辭學》時,亞里士多德主張“男人和女人”應該具有“共同的優點”:其一,所有青年人身體上的優點是身材高大、漂亮、強壯、善於運動,“靈魂上的優點則是自治和勇敢”;其二,“對於女性來說,身體上的優點包括美麗和高大;靈魂上的優點是自治,勤勞而不利慾熏心”(Rhetoric,1361a)。(18)在《尼各馬科倫理學》中,他又曾提到:“如若狀況良好是指肌肉的結實,那麼,狀況不佳必定是指肌肉的衰弱。要造成良好的身體,就在於使肌肉結實。”(19)顯然,這是一種以男人爲樣板的身體美學。男人被樹立爲典範,女性則不過是難以成功的效仿者。有關男性的審美尺度被擴展到女性身上,規範和引領她們,但又同時顯露其欠缺。在審美場域中,她們被男性巨大的身影覆蓋了,處於從屬地位。
,前342—前291)的劇本中,讀者甚至可以發現“可愛的面孔”和“甜美的聲音”等針對女性的描述(12)。吊詭的是,此類言說並不多見,聚焦女性的身體美學並未因此誕生。由於不能參與公共生活(如當將軍、政治家、陪審員),女性身體事實上處於隱匿狀態,很難進入大衆的視野,因此,作爲一個性屬—性別的她們並非重要的審美對象。(13)在審美領域,她們被覆蓋和遮蔽:“古希臘人認爲理想的美體現在青少年身上”,“大量的花瓶上刻有‘漂亮的少年’字樣,而‘漂亮的少女’則較少見”。(14)在《理想國》中,柏拉圖曾經興致勃勃地提到雅典人對美少年的偏愛:“你沒看到人們說塌鼻子的‘容貌俏麗’,高鼻子‘儀表堂堂’,鼻子不高不低的則‘長得恰到好處’?”(Republic 474d)(15)如此說話的他關注的是男性,女人的美則難入他的法眼。對於他來說,女性雖然屬於“較弱的性別”,但仍然應該像男人一樣被對待:“在教育問題上和在別的事情上,女性一定要和男性結合在一起。”(《法篇》805c)“立法者應當徹底,不能半心半意,他一定不能在爲男性立法後,就把另一種性別的人當作放蕩的奢侈生活的工具和取樂的對象,這樣做的結果必然使整個社會的幸福生活衹剩下一半。”(《法篇》806c)(16)這種考慮的核心並非女性的福祉,而是其社會功能:“如果城邦的婦女沒有訓練好,乃至於連母雞面對最危險的野獸或其他任何危險冒死保護小雞的勇氣都沒有,如果她們衹是朝着神廟狂奔,坐在祭壇和神龕前,那麼這種表現確實是城邦的奇恥大辱,是人類最卑賤的表現。”(《法篇》814b)(17)柏拉圖所在的雅典人口並不多,小國寡民的現實處境使他不能過於強調男女之別,否則,本就不大的城邦就會衹剩下一半的勞動力。古希臘的女性雖然被限制在家庭中,但仍需部分參與城邦的物質生產。正因爲如此,古希臘思想家傾向於建構統一的身體美學。譬如,寫作《修辭學》時,亞里士多德主張“男人和女人”應該具有“共同的優點”:其一,所有青年人身體上的優點是身材高大、漂亮、強壯、善於運動,“靈魂上的優點則是自治和勇敢”;其二,“對於女性來說,身體上的優點包括美麗和高大;靈魂上的優點是自治,勤勞而不利慾熏心”(Rhetoric,1361a)。(18)在《尼各馬科倫理學》中,他又曾提到:“如若狀況良好是指肌肉的結實,那麼,狀況不佳必定是指肌肉的衰弱。要造成良好的身體,就在於使肌肉結實。”(19)顯然,這是一種以男人爲樣板的身體美學。男人被樹立爲典範,女性則不過是難以成功的效仿者。有關男性的審美尺度被擴展到女性身上,規範和引領她們,但又同時顯露其欠缺。在審美場域中,她們被男性巨大的身影覆蓋了,處於從屬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