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图书馆机构用户,欢迎您!
文章讨论北京话的轻声与其韵律变量的语法功能,认为北京话的轻声是一种现行语音变化的现象,其轻化度的表现不一。这种轻度不同的表现,是该语言多重层面和多种因素(如韵素、音节与声调,韵律与形态,构词与语法、词汇意义与功能意义)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文章认为,从韵律语法的角度看轻声,可以加深我们对北京话轻声语法功能的理解和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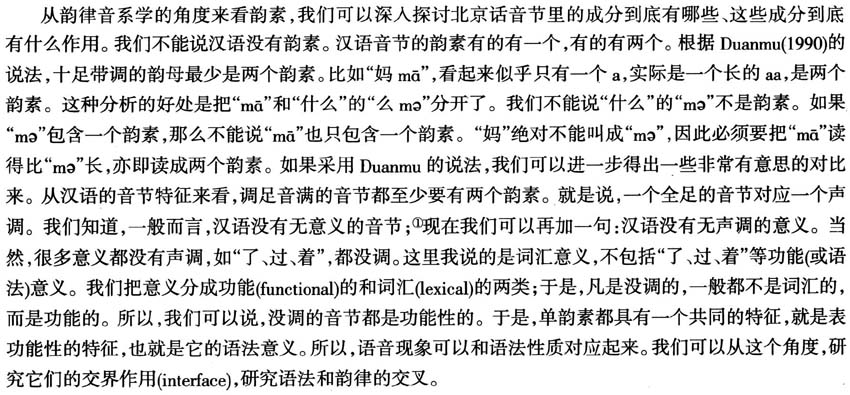 上面的构想意义何在?如何证明?回答这些问题的最好办法是,根据上面的构想我们可以推导出什么新的“通理(generalization)”、能发现什么新的“规则(rule)”?譬如,我们可以推出:“凡是一个韵素的音节都不足以承载声调。”对不对呢?能不能反过来说,“凡是没调的形式都只包含一个韵素”。这两个推理实际互为因果。韵素太小了,声调就实现不了了。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凡是丢了调的,就变成了一个韵素。于是“天啊tiān+a”可以变成“天呐tiān+na”——打破了不能“跨词界音节化(resyllabification)”的常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语音上的“丢调”、“减量(变成单韵素)”就总和语言中的另一个层面相互对应,那个层面就是词汇语法的层面。在词汇领域,它不是词汇词,是功能词;在语法领域里,它不是实词而是黏着性语素(或系联句法单位之间的那些功能成分),像“的、在”一类表达语法意义的虚词(参庄会彬等(2012)有关进一步区分“G-的”与“P-的”的不同)。
上面的构想意义何在?如何证明?回答这些问题的最好办法是,根据上面的构想我们可以推导出什么新的“通理(generalization)”、能发现什么新的“规则(rule)”?譬如,我们可以推出:“凡是一个韵素的音节都不足以承载声调。”对不对呢?能不能反过来说,“凡是没调的形式都只包含一个韵素”。这两个推理实际互为因果。韵素太小了,声调就实现不了了。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凡是丢了调的,就变成了一个韵素。于是“天啊tiān+a”可以变成“天呐tiān+na”——打破了不能“跨词界音节化(resyllabification)”的常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语音上的“丢调”、“减量(变成单韵素)”就总和语言中的另一个层面相互对应,那个层面就是词汇语法的层面。在词汇领域,它不是词汇词,是功能词;在语法领域里,它不是实词而是黏着性语素(或系联句法单位之间的那些功能成分),像“的、在”一类表达语法意义的虚词(参庄会彬等(2012)有关进一步区分“G-的”与“P-的”的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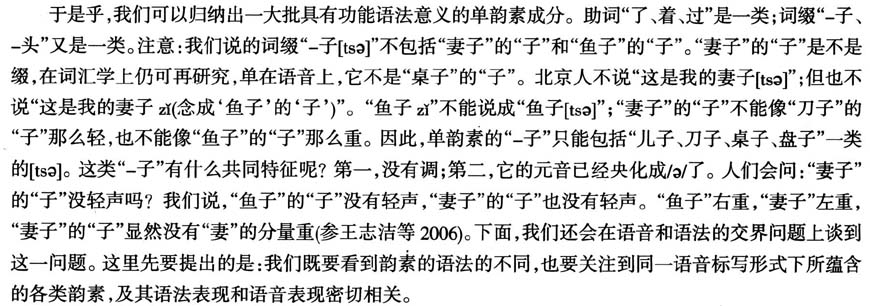 在北京话里,鱼子、妻子、孩子的不同,不是孤立的,是有系统性的。譬如“头”。“石头”的“头”和“砖头”的“头”不一样。用语音一测,这里有两个“头”。“砖头”不能念成“砖头
在北京话里,鱼子、妻子、孩子的不同,不是孤立的,是有系统性的。譬如“头”。“石头”的“头”和“砖头”的“头”不一样。用语音一测,这里有两个“头”。“砖头”不能念成“砖头 ”。此外还有一个“炕头”的“头”,指的就是炕里面那一块儿地方。这个“头”还带有特定的意义,所以它显然不是我们说的最小韵素的功能词。 北京话还有一些单韵素功能化的语法成分,如“-在”、“-进”等都可以归入到韵律层级里面的“附着成分”(clitic forms)。“放在桌上”北京人可以说成“放
”。此外还有一个“炕头”的“头”,指的就是炕里面那一块儿地方。这个“头”还带有特定的意义,所以它显然不是我们说的最小韵素的功能词。 北京话还有一些单韵素功能化的语法成分,如“-在”、“-进”等都可以归入到韵律层级里面的“附着成分”(clitic forms)。“放在桌上”北京人可以说成“放 桌上”。/
桌上”。/ /实际就是一个轻声化的韵律附着成分。再如“吃进一苍蝇去”,这里的“进”和“去.qie”也是轻声化的虚词。“桌上”、“门上”,“门上一苍蝇”,“脸上一黑点”的“上”,都是轻的。 北京话里还有一种叫“一个半(即1.5)音节”的。“一个半音节”指的是我们说的轻声化的双音节词。比如“清楚”,不是“qīngchǔ”,而是qīng.chu;“明白”不是míngbái,而是míng.b
/实际就是一个轻声化的韵律附着成分。再如“吃进一苍蝇去”,这里的“进”和“去.qie”也是轻声化的虚词。“桌上”、“门上”,“门上一苍蝇”,“脸上一黑点”的“上”,都是轻的。 北京话里还有一种叫“一个半(即1.5)音节”的。“一个半音节”指的是我们说的轻声化的双音节词。比如“清楚”,不是“qīngchǔ”,而是qīng.chu;“明白”不是míngbái,而是míng.b “漂亮、红火、得罪、摩挲、眨么”都是这样,越口语越轻。北京话里有很多双音节词,但没有几个十足双音的。口语里双音节的第二个字几乎都是轻声的,而且轻的程度还挺大。所以,我们说一个音节(syllable=两个韵素)再加上一个韵素(μ),叫“一个半音节”,不是两个音节。两个音节是韵律词(冯胜利1996),一个半音节是什么?很值得研究。我们下面再谈。 还有一批单韵素的功能词是代词。譬如,“想他”这个“他”,非常轻。北京人说“放那儿一本书”,其中的“在”字都没了,要是说成“放在那里一本书”就不是北京话了。还有“给他俩耳刮子”里的“他”,后面还可以带“了”:“给他了俩耳刮子”。这更证明这个“他”字是动词上的附着成分了,附到了“给”字身上,变成动词的一部分了,有点像“靠在”、“放在”的“在”,要加“了”的话,就得加到“在”的后头,跟说成“放在了桌子上”一样。就上边的理论上说,做到这一步必须是单韵素。韵素不单,不具备这种功能。所以说,语法的功能和语音的长短是彼此对应的,是一张纸的两个面——单韵素和双韵素有词汇和语法上的对立,所以北京话不能只讲音节,不讲韵素。
“漂亮、红火、得罪、摩挲、眨么”都是这样,越口语越轻。北京话里有很多双音节词,但没有几个十足双音的。口语里双音节的第二个字几乎都是轻声的,而且轻的程度还挺大。所以,我们说一个音节(syllable=两个韵素)再加上一个韵素(μ),叫“一个半音节”,不是两个音节。两个音节是韵律词(冯胜利1996),一个半音节是什么?很值得研究。我们下面再谈。 还有一批单韵素的功能词是代词。譬如,“想他”这个“他”,非常轻。北京人说“放那儿一本书”,其中的“在”字都没了,要是说成“放在那里一本书”就不是北京话了。还有“给他俩耳刮子”里的“他”,后面还可以带“了”:“给他了俩耳刮子”。这更证明这个“他”字是动词上的附着成分了,附到了“给”字身上,变成动词的一部分了,有点像“靠在”、“放在”的“在”,要加“了”的话,就得加到“在”的后头,跟说成“放在了桌子上”一样。就上边的理论上说,做到这一步必须是单韵素。韵素不单,不具备这种功能。所以说,语法的功能和语音的长短是彼此对应的,是一张纸的两个面——单韵素和双韵素有词汇和语法上的对立,所以北京话不能只讲音节,不讲韵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