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图书馆机构用户,欢迎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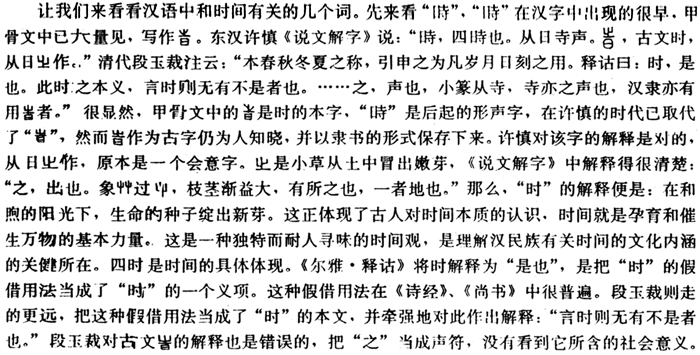 中国古人这种对时间的认识,根源于对大自然(尤其是植物)随时间的孕育、生长、繁盛和消亡这一现象的观察和体悟。这一认识随着农耕时代的到来进一步加深和巩固。对“春”、“秋”、“年”等词的分析也能印证这一点。这几个表示时间或季节的词,其本义都与植物或庄稼的生长、成熟有关。“年”本义是禾谷成熟的意思,《说文》曰:“年,谷熟也,从禾干声。”“年”字在卜辞中亦多见,本义即为“谷熟”,卜辞中的“受年”、“求年”,就是后世“祈谷”之祭。〔3 〕《春秋·宣公十六年》中有“大有年”,即是年谷物大丰收。古时一年庄稼成熟一次,于是庄稼成熟的周期便很自然成了古人计时的一个单位“年”。“春”《说文》作“萅”,“推也。从草从日,草,春时生也,屯声。”根据甲骨卜辞材料,“屯”其实就是“春”的本字。这个结论的线索也是《说文》提供的。《说文》:“屯”,难也,象草木之初生屯然而难,从草贯一……“象草木之初生”便是屯的本义,难是后起的引伸义。
中国古人这种对时间的认识,根源于对大自然(尤其是植物)随时间的孕育、生长、繁盛和消亡这一现象的观察和体悟。这一认识随着农耕时代的到来进一步加深和巩固。对“春”、“秋”、“年”等词的分析也能印证这一点。这几个表示时间或季节的词,其本义都与植物或庄稼的生长、成熟有关。“年”本义是禾谷成熟的意思,《说文》曰:“年,谷熟也,从禾干声。”“年”字在卜辞中亦多见,本义即为“谷熟”,卜辞中的“受年”、“求年”,就是后世“祈谷”之祭。〔3 〕《春秋·宣公十六年》中有“大有年”,即是年谷物大丰收。古时一年庄稼成熟一次,于是庄稼成熟的周期便很自然成了古人计时的一个单位“年”。“春”《说文》作“萅”,“推也。从草从日,草,春时生也,屯声。”根据甲骨卜辞材料,“屯”其实就是“春”的本字。这个结论的线索也是《说文》提供的。《说文》:“屯”,难也,象草木之初生屯然而难,从草贯一……“象草木之初生”便是屯的本义,难是后起的引伸义。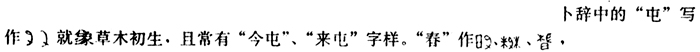 很容易看出都是屯的后起字,加日,加草是为了使“屯”的表时间意味更明显。“秋”的本义是谷物成熟,《说文》云:“秋,禾谷熟也。”甲骨文“秋”作很显然是突出成熟的谷穗。《尚书·盘庚》中“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就是“秋”的本义。殷人只分春秋两迹簿很显然是因为“春”与“秋”正是播种和收获的时间,于农事极为关键。这种划分有很实际的意义。 农事中的“种”,是最讲时机的,先秦汉语中“时”就有播种的含义,这就是后来的“莳”字。直到现在,南方很多地方都不把插秧叫“莳田”或“莳禾”,莳者,不失时机地栽种也。二十四节气也是汉族特有的时间划分,它也是为农业生产而制定的。《淮南子·天文训》说:“十五日为一节,乃生二十四时之变。”“节气”一词,指明了时间与气候的关系,二十四节气中,许多节气的名称,即透露这方面的信息:如小寒、大寒、雨水、谷雨、小满、小署、大署、处署、白露、霜降、小雪、大雪。还应指出,这里“气”有更深刻的内涵。气的本义是人之气息,古人从人死气息绝体悟到气是生命的本原,并将这种观念推衍到万事万物。天之气形现为云,所以《说文》谓“气,云气也”。地之气形现为风,(今还可见“风气”连用。)《礼记·月令》中就说过:“是月也,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萌动。”可见,“天气”,“气候”、“节气”这些词的构成,都是有深刻的内涵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汉民族的传统时间观,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把时间和农业生产紧密联系起来,把农事的进程作为时间的一种重要尺度,把时间和大自然的生息紧密联系在一起。 汉语中还有一组耐人寻味的词:月令、时令、节令,它们把时间与命令、政令联系在一起,这也是汉民族深植于农耕文化的时间体悟。《吕氏春秋·十二纪》帮我们揭示了时与令的关系,因农事和时间的关系极为密切,农耕社会的一切政令都要围绕着农时来颁行,“不违农时”成为中国古代政治的一条铁律。《十二纪》记载了每月相应的政令,如孟春之月,天子须在立春前三天斋戒。“立春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迎春于东郊”,“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乃择元辰,天子亲载耒耜。”“王命布农事,命田舍东郊,皆修封疆,审端经术,善相丘陵阪险原
很容易看出都是屯的后起字,加日,加草是为了使“屯”的表时间意味更明显。“秋”的本义是谷物成熟,《说文》云:“秋,禾谷熟也。”甲骨文“秋”作很显然是突出成熟的谷穗。《尚书·盘庚》中“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就是“秋”的本义。殷人只分春秋两迹簿很显然是因为“春”与“秋”正是播种和收获的时间,于农事极为关键。这种划分有很实际的意义。 农事中的“种”,是最讲时机的,先秦汉语中“时”就有播种的含义,这就是后来的“莳”字。直到现在,南方很多地方都不把插秧叫“莳田”或“莳禾”,莳者,不失时机地栽种也。二十四节气也是汉族特有的时间划分,它也是为农业生产而制定的。《淮南子·天文训》说:“十五日为一节,乃生二十四时之变。”“节气”一词,指明了时间与气候的关系,二十四节气中,许多节气的名称,即透露这方面的信息:如小寒、大寒、雨水、谷雨、小满、小署、大署、处署、白露、霜降、小雪、大雪。还应指出,这里“气”有更深刻的内涵。气的本义是人之气息,古人从人死气息绝体悟到气是生命的本原,并将这种观念推衍到万事万物。天之气形现为云,所以《说文》谓“气,云气也”。地之气形现为风,(今还可见“风气”连用。)《礼记·月令》中就说过:“是月也,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萌动。”可见,“天气”,“气候”、“节气”这些词的构成,都是有深刻的内涵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汉民族的传统时间观,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把时间和农业生产紧密联系起来,把农事的进程作为时间的一种重要尺度,把时间和大自然的生息紧密联系在一起。 汉语中还有一组耐人寻味的词:月令、时令、节令,它们把时间与命令、政令联系在一起,这也是汉民族深植于农耕文化的时间体悟。《吕氏春秋·十二纪》帮我们揭示了时与令的关系,因农事和时间的关系极为密切,农耕社会的一切政令都要围绕着农时来颁行,“不违农时”成为中国古代政治的一条铁律。《十二纪》记载了每月相应的政令,如孟春之月,天子须在立春前三天斋戒。“立春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迎春于东郊”,“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乃择元辰,天子亲载耒耜。”“王命布农事,命田舍东郊,皆修封疆,审端经术,善相丘陵阪险原 ,土地所宜,五谷所殖,以教道民,必躬亲之。田事既饬,先定准直,农乃不惑。”(《吕氏春秋·孟春纪》)农业生产的极强的时间性和收成对气候的依赖性,使人们意识到,任何对季节时序的违背,都会带来极坏的结果。大自然的报应不爽,使古人们坚信,是上帝的意志左右着人类,自然力只不过是上帝意志的体现,在强大的自然力面前,屈服和顺应才是明智的策略。这种认识发展为时间观上的“天人合一”,卜辞中常常可以见到“帝不令雨”等字样,便是“天人合一”时间观的反映。
,土地所宜,五谷所殖,以教道民,必躬亲之。田事既饬,先定准直,农乃不惑。”(《吕氏春秋·孟春纪》)农业生产的极强的时间性和收成对气候的依赖性,使人们意识到,任何对季节时序的违背,都会带来极坏的结果。大自然的报应不爽,使古人们坚信,是上帝的意志左右着人类,自然力只不过是上帝意志的体现,在强大的自然力面前,屈服和顺应才是明智的策略。这种认识发展为时间观上的“天人合一”,卜辞中常常可以见到“帝不令雨”等字样,便是“天人合一”时间观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