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图书馆机构用户,欢迎您!
公共领域在媒介平台化和平台媒介化的互动下出现了新转型,这是平台资本主义挖掘数据、进行数字化生产的结果。作为新历史形态的数字资本主义使平台用户成为流众,流众的数字劳动经过赋形成为流量。在争夺流量的过程中数字媒介平台形塑了数字媒体生态,其显著特征就是具有虚假自主权的用户进入了茧房和回音室。封闭式交往是无效的自我叠加或复制,公共领域对话质量由此下降,损害了公共性与协商政治。身处国家能力弱势和社会科技强势这个双重态势中的哈贝马斯,要求增强国家规制、整合新技术,以修复受损的公共领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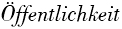 und die deliberative Politik)。著作表达了两个思想:一是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工具的新兴社交媒介正在推动交往范式的转换;二是失控的平台冲击了公共领域,影响了对话的质量,使协商政治面临严峻的挑战。前者是他对经验领域的观察,后者则是他在新技术条件下对公共领域的规范性思考。哈贝马斯的论述仍然存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痕迹:数字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造成了合法化危机和人类精神生活的变化。联系1962年出版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和稍后出版的《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人们不难发现哈贝马斯对公共性的维护矢志不渝。近二十年来,面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形态——“数字资本主义”——的入侵,哈贝马斯用“反公共性”来表达其对公共领域被破坏的不安。这种不安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自我推动和升级的算法已然形成“数据化暴力”,作为新的系统入侵了生活世界;另一方面,标志性的事件——特朗普个人推特账户2020年被封,意味着西方引以为傲的价值观——言论自由——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甚至让人怀疑西方核心价值观只是形式。本文从三个方面回应哈贝马斯:世界已被数据表征;平台—算法是挖掘差异的新权力;加强国家能力,让国家规制失控的技术,从而回归公共性。 一、数字生产的神话 毋庸讳言,人类已处在数字时代,世界将成为数字化的世界。说世界数字化,甚至用“数字本体论”这个词表达技术表征的世界,不是说世界本身就是数字,而是说离开了数字,世界无法呈现自身的意义。笛卡尔以后,人们习惯于把自我与世界对立起来,实际上这是语言出现之后的事,即人以语言把自己与世界区别开来。在通过语言进行反思之前,人在世界中没有凸显为一个事件。马克思强调生产劳动对于人与世界相互生成的重要性。他说:“工业是自然界对人,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因此,如果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1]193马克思从不离开有目的的人的历史性活动(生产劳动)空谈自然界和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1]520海德格尔认为语言开显了世界,而在马克思这里,生产让世界和人统一在人类物质资料生产的历史中,即“正像一切自然物必须形成一样,人也有自己的形成过程即历史,但历史对人来说是被认识到的历史,因而它作为形成过程是一种有意识地扬弃自身的形成过程。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2]107。 亚里士多德把人的活动分为三类:理论、实践和制作。亚里士多德说:“例如,建筑术是一种技艺,是一种与制作相关的、合乎逻各斯的品质……所有的技艺都使某种事物生成。”[3]在马克思这里,更一般的概念——生产——取代了亚里士多德的“制作”。人类生产不同于动物活动,是因为生产未开展之前人就有了某种意向和目的。人的生产是在某种目的的牵引下进行的,承诺了两个人以上的意向及其达成,即生产是社会性的活动。马克思强调的“怎样生产、用什么生产”变成了人类生活的条件,也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2]58“内在的尺度”和“美的规律”就是有意义、合目的的生产,这种生产离不开人类有意义的符号系统。 哈贝马斯对马克思的思想做了进一步发挥。哈贝马斯说:“资本主义是由一种生产方式决定的,这种生产方式不仅提出了统治的合法性问题,而且也解决统治的合法性问题。资本主义统治的合法性,不再是得自于文化传统的天国,而是从社会劳动的根基上获得的。财产私有者赖以交换商品的市场机制(包括那些没有财产的人们把他们的劳动力当作唯一的商品拿去交换的市场在内),确保着交换关系的公平合理和等价交换。”[4]54按照这种逻辑,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但是有效的,还是自由、公正的。符号负载意义,生产按照意义(合理的、美的、公平的)进行。符号一旦被人创造出来之后似乎就具有独立生命,这一点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中得到了空前强化。哈贝马斯之所以担心技术成为新的意识形态,是因为技术就像道德一样代表了合理性,可以遮蔽现实的缺陷,让人们相信所有问题都可以在技术创新的浪潮中解决,技术甚至被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利用,以巩固不平衡的权力关系。哈贝马斯认为:“适用于道德意识和技术意识的东西,也同样适用于理论意识。黑格尔用语言符号表述的辩证法,从根本上说,是针对康德的脱离了一切形成过程的先验意识的综合活动概念的。因为抽象的认识批判是按照亚里士多德采用的手工活动(劳动的主体用手工活动创造物质)的模式来理解范畴和直观形式同经验材料的关系的。”[4]19马克思把康德的先验形式、黑格尔的神秘“精神”直接表述为现实的物质生产,但是,数字资本主义在新的历史形态中又把神秘的“数字”邀请了回来,滥觞为“数字拜物教”。 数字资本主义的核心就是按数据—流量生产。贾森·萨多夫斯基把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称为“数据世界”。他指出:“越来越清晰的是,我们正生活在‘亚马逊’的时期。纵观历史,当生产和分配体系能对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产生重大影响时,我们往往用这些体系的名称来命名一个时代。例如发端于一百年前的那段资本主义时代现在被称为‘福特主义’时期,因为福特汽车的大规模生产和消费彻底改变了当时的经济和社会面貌。因此,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当前所身处的历史阶段未来可能会被称为‘亚马逊’时期。”[5]29“亚马逊”是一个完全由数据驱动的企业,成为数字资本主义的代名词。对与大数据相应的人工智能算法的崇拜形成了新的拜物教,即数字拜物教。日本学者森健、日户浩之把资本主义定义为“通过发现、利用、创造差异来获取利润,追求持续不断积累资本(货币)的体系”[6]30。根据不同时代挖掘差异方式的不同,资本主义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商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与数字资本主义。在他们看来,数字资本主义的基本构成是:“同时伴随着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诸如大规模定制等原本不可能实现的差异创造机制也成为了可能,从这一点上看,又具备了工业资本主义的要素。”[6]35不同于商业资本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数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在原材料、必要劳动时间以及对空间化市场的拓展等方面做文章,而是着力于关注用户数字劳动提供的数据资产及其流量表征出来的精神状态。挖掘数据,在一种新的语言形式——算法——中进行意义制造和流量生成,成了数字资本主义的生命线。用户在移动数字设备上的活动(数字劳动)表征了比现实更加真实的精神数字世界。这一点被亚马逊、淘宝这样的超级平台企业以低成本甚至零成本的方式捕获、抽取、制作、投喂。哈贝马斯揭示过符号语言的秘密:“因此,语言是第一范畴,在语言这个范畴下,精神不是被想象为一种内在的东西(ein Inneres),而是既非内在,又非外在的媒介。在语言的范畴中,精神世界的逻各斯(Logos einer Welt),并不是孤独的自我意识的反思。”[4]16数据是一种新的语言,帮助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蜕皮、续命、换代。因此,蓝江指出:“的确,数字资本主义并不是一个人为缔造的概念,它与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有关,简言之,数字资本主义是一个历史概念,我们只能在作为历史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之下来思考它。”[7]
und die deliberative Politik)。著作表达了两个思想:一是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工具的新兴社交媒介正在推动交往范式的转换;二是失控的平台冲击了公共领域,影响了对话的质量,使协商政治面临严峻的挑战。前者是他对经验领域的观察,后者则是他在新技术条件下对公共领域的规范性思考。哈贝马斯的论述仍然存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痕迹:数字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造成了合法化危机和人类精神生活的变化。联系1962年出版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和稍后出版的《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人们不难发现哈贝马斯对公共性的维护矢志不渝。近二十年来,面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形态——“数字资本主义”——的入侵,哈贝马斯用“反公共性”来表达其对公共领域被破坏的不安。这种不安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自我推动和升级的算法已然形成“数据化暴力”,作为新的系统入侵了生活世界;另一方面,标志性的事件——特朗普个人推特账户2020年被封,意味着西方引以为傲的价值观——言论自由——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甚至让人怀疑西方核心价值观只是形式。本文从三个方面回应哈贝马斯:世界已被数据表征;平台—算法是挖掘差异的新权力;加强国家能力,让国家规制失控的技术,从而回归公共性。 一、数字生产的神话 毋庸讳言,人类已处在数字时代,世界将成为数字化的世界。说世界数字化,甚至用“数字本体论”这个词表达技术表征的世界,不是说世界本身就是数字,而是说离开了数字,世界无法呈现自身的意义。笛卡尔以后,人们习惯于把自我与世界对立起来,实际上这是语言出现之后的事,即人以语言把自己与世界区别开来。在通过语言进行反思之前,人在世界中没有凸显为一个事件。马克思强调生产劳动对于人与世界相互生成的重要性。他说:“工业是自然界对人,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因此,如果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1]193马克思从不离开有目的的人的历史性活动(生产劳动)空谈自然界和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1]520海德格尔认为语言开显了世界,而在马克思这里,生产让世界和人统一在人类物质资料生产的历史中,即“正像一切自然物必须形成一样,人也有自己的形成过程即历史,但历史对人来说是被认识到的历史,因而它作为形成过程是一种有意识地扬弃自身的形成过程。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2]107。 亚里士多德把人的活动分为三类:理论、实践和制作。亚里士多德说:“例如,建筑术是一种技艺,是一种与制作相关的、合乎逻各斯的品质……所有的技艺都使某种事物生成。”[3]在马克思这里,更一般的概念——生产——取代了亚里士多德的“制作”。人类生产不同于动物活动,是因为生产未开展之前人就有了某种意向和目的。人的生产是在某种目的的牵引下进行的,承诺了两个人以上的意向及其达成,即生产是社会性的活动。马克思强调的“怎样生产、用什么生产”变成了人类生活的条件,也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2]58“内在的尺度”和“美的规律”就是有意义、合目的的生产,这种生产离不开人类有意义的符号系统。 哈贝马斯对马克思的思想做了进一步发挥。哈贝马斯说:“资本主义是由一种生产方式决定的,这种生产方式不仅提出了统治的合法性问题,而且也解决统治的合法性问题。资本主义统治的合法性,不再是得自于文化传统的天国,而是从社会劳动的根基上获得的。财产私有者赖以交换商品的市场机制(包括那些没有财产的人们把他们的劳动力当作唯一的商品拿去交换的市场在内),确保着交换关系的公平合理和等价交换。”[4]54按照这种逻辑,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但是有效的,还是自由、公正的。符号负载意义,生产按照意义(合理的、美的、公平的)进行。符号一旦被人创造出来之后似乎就具有独立生命,这一点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中得到了空前强化。哈贝马斯之所以担心技术成为新的意识形态,是因为技术就像道德一样代表了合理性,可以遮蔽现实的缺陷,让人们相信所有问题都可以在技术创新的浪潮中解决,技术甚至被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利用,以巩固不平衡的权力关系。哈贝马斯认为:“适用于道德意识和技术意识的东西,也同样适用于理论意识。黑格尔用语言符号表述的辩证法,从根本上说,是针对康德的脱离了一切形成过程的先验意识的综合活动概念的。因为抽象的认识批判是按照亚里士多德采用的手工活动(劳动的主体用手工活动创造物质)的模式来理解范畴和直观形式同经验材料的关系的。”[4]19马克思把康德的先验形式、黑格尔的神秘“精神”直接表述为现实的物质生产,但是,数字资本主义在新的历史形态中又把神秘的“数字”邀请了回来,滥觞为“数字拜物教”。 数字资本主义的核心就是按数据—流量生产。贾森·萨多夫斯基把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称为“数据世界”。他指出:“越来越清晰的是,我们正生活在‘亚马逊’的时期。纵观历史,当生产和分配体系能对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产生重大影响时,我们往往用这些体系的名称来命名一个时代。例如发端于一百年前的那段资本主义时代现在被称为‘福特主义’时期,因为福特汽车的大规模生产和消费彻底改变了当时的经济和社会面貌。因此,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当前所身处的历史阶段未来可能会被称为‘亚马逊’时期。”[5]29“亚马逊”是一个完全由数据驱动的企业,成为数字资本主义的代名词。对与大数据相应的人工智能算法的崇拜形成了新的拜物教,即数字拜物教。日本学者森健、日户浩之把资本主义定义为“通过发现、利用、创造差异来获取利润,追求持续不断积累资本(货币)的体系”[6]30。根据不同时代挖掘差异方式的不同,资本主义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商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与数字资本主义。在他们看来,数字资本主义的基本构成是:“同时伴随着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诸如大规模定制等原本不可能实现的差异创造机制也成为了可能,从这一点上看,又具备了工业资本主义的要素。”[6]35不同于商业资本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数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在原材料、必要劳动时间以及对空间化市场的拓展等方面做文章,而是着力于关注用户数字劳动提供的数据资产及其流量表征出来的精神状态。挖掘数据,在一种新的语言形式——算法——中进行意义制造和流量生成,成了数字资本主义的生命线。用户在移动数字设备上的活动(数字劳动)表征了比现实更加真实的精神数字世界。这一点被亚马逊、淘宝这样的超级平台企业以低成本甚至零成本的方式捕获、抽取、制作、投喂。哈贝马斯揭示过符号语言的秘密:“因此,语言是第一范畴,在语言这个范畴下,精神不是被想象为一种内在的东西(ein Inneres),而是既非内在,又非外在的媒介。在语言的范畴中,精神世界的逻各斯(Logos einer Welt),并不是孤独的自我意识的反思。”[4]16数据是一种新的语言,帮助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蜕皮、续命、换代。因此,蓝江指出:“的确,数字资本主义并不是一个人为缔造的概念,它与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有关,简言之,数字资本主义是一个历史概念,我们只能在作为历史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之下来思考它。”[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