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图书馆机构用户,欢迎您!
王元化“九十年代反思”的酿成,就其初始机缘而言,涉及元化晚年栖居的庆余别墅这一思想客厅及围绕着这一地理空间而展开的“学案人际”。关于“反思五四”,为何元化1988年无计直面的思想史“症结”,1993年后就能给出较系统的自我解惑?此处连接着许纪霖请元化序《杜亚泉文选》及1993年元化读林毓生著《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这两重“契机”。围绕元化“反思五四”,将“文献—发生学”这一学案研究方法,运用于“城市地理百年文脉与城市精神”框架,“学案对象”从“百年文脉”人格环节之“在场”,升华为“城市精神”角色亲证之“体认”,既觉知其事实性“在场”,又深邃地涵泳其价值性“体认”,由此,庆余别墅成为见证这一“反思”事件的思想史旧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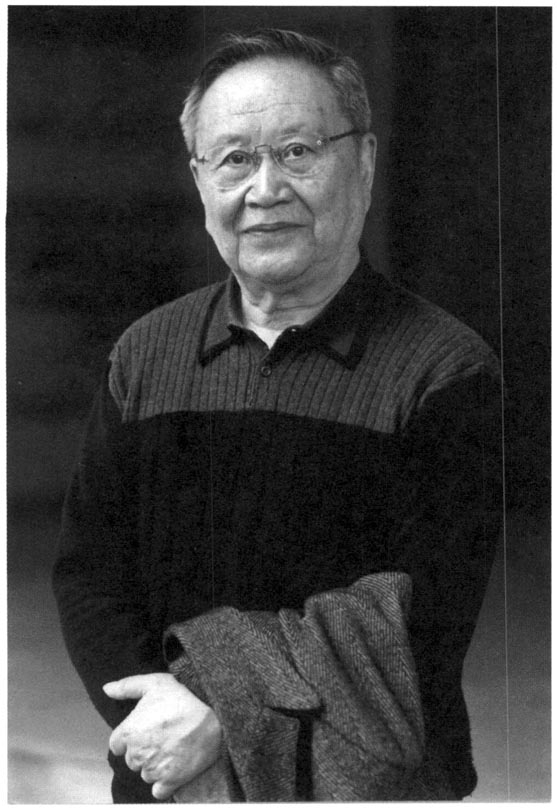 王元化个人照(蓝云女士提供) 比元化晚生的后学有理由庆幸,不仅庆幸自己与元化同饮一江水,且庆幸自己竟有缘不时出入庆余“客厅”,那是元化向其同好、门下吐露其学思的即兴讲坛,也是他从后学的激情喧哗中听取时潮的创意前沿。史实表明,后来酿成“九十年代反思”的那对著名命题(“反思《社会契约论》”与“反思五四”),就其初始机缘而言,本是心仪元化的两位青年才俊一前一后令其碰上的。前者有涉朱学勤。1992年5月,元化被邀主持复旦大学博士生朱学勤学位论文《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之答辩。该论文旨在研究罗伯斯庇尔而兼及卢梭《社会契约论》。元化追忆如下: 学勤的论文引证了为我陌生的一些观点,对我的思想发生了剧烈冲撞,促使我去找书来看,认真地加以思考和探索。其结果则是轰毁了我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一些既定看法,对于我从那些教科书式的著作中所读到而并未深究就当做深信不疑的结论而接受下来的东西产生了怀疑。从这时起,我对卢梭的国家学说、对法国大革命的认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开始去寻找极“左”思潮的根源,纠正了原来对于激进主义思潮的看法。我的反思虽然进入九十年代就开始了,但到了这时候我才真正进入了角色。所以可以说,主持朱学勤的论文答辩这件事,是导致我在九十年代进行反思的重要诱因。他的论文引发了我对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思考。这一思考延续到本世纪末,直到一九九九年我才以通信形式写了长篇论文《与友人谈社约论书》,作为自己对这一问题探讨的思想小结。② “反思五四”则有涉许纪霖。1993年夏,许纪霖承华东师大出版社编审施亚西(杜亚泉儿媳)委托,诚邀元化撰《杜亚泉文选序》,以为纪念——恰逢杜亚泉诞辰120周年,逝世60周年。杜亚泉(1873-1933),浙江绍兴上虞人,新文化运动初年尚主编《东方杂志》,因与《新青年》陈独秀(1879-1942)等展开“东西文化问题论战”而成思想史人物。 元化日记对其执笔《杜亚泉与东西文化论战》实录甚勤甚细,大致是从1993年8月1日始读杜亚泉资料,俟后“读得越多,就越感到杜未被当时以至后代所理解,更未被注意”。③如此不辞酷暑地苦读40天,至9月11日上午起草此稿,连轴伏案疾书十日,终在9月21日“完成第二稿。五百字稿纸三十五张,共一万七千余言,为近年所撰最长之文。连日撰写不辍,实觉筋疲力尽”。④ 元化年逾古稀仍壮怀不已,因为他读杜愈深,愈直觉此即“反思五四”之滥觞。请细味其“夫子自道”: 过去我对五四的认识是基于长期所吸取的大量既定观念,这些既定观念已被我当作不可动摇的信念,深深扎根在我的头脑中,过去所读到的那些资料的汇编,理论的阐释以及史的著述等等,几乎都是在这些既定观念的导引下编写而成的……所以不能使人看到历史事实的全貌和真相。当我着手要写有关杜亚泉的文章时,我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去阅读过去资料汇编等所没有收录的第一手资料。经过阅读和思考,我认为五四精神当然要继承,但五四的一些缺陷(如意图伦理、功利主义、激进情绪、庸俗进化观点等)是不应该继承的。我们要继承的是它好的方面。⑤
王元化个人照(蓝云女士提供) 比元化晚生的后学有理由庆幸,不仅庆幸自己与元化同饮一江水,且庆幸自己竟有缘不时出入庆余“客厅”,那是元化向其同好、门下吐露其学思的即兴讲坛,也是他从后学的激情喧哗中听取时潮的创意前沿。史实表明,后来酿成“九十年代反思”的那对著名命题(“反思《社会契约论》”与“反思五四”),就其初始机缘而言,本是心仪元化的两位青年才俊一前一后令其碰上的。前者有涉朱学勤。1992年5月,元化被邀主持复旦大学博士生朱学勤学位论文《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之答辩。该论文旨在研究罗伯斯庇尔而兼及卢梭《社会契约论》。元化追忆如下: 学勤的论文引证了为我陌生的一些观点,对我的思想发生了剧烈冲撞,促使我去找书来看,认真地加以思考和探索。其结果则是轰毁了我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一些既定看法,对于我从那些教科书式的著作中所读到而并未深究就当做深信不疑的结论而接受下来的东西产生了怀疑。从这时起,我对卢梭的国家学说、对法国大革命的认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开始去寻找极“左”思潮的根源,纠正了原来对于激进主义思潮的看法。我的反思虽然进入九十年代就开始了,但到了这时候我才真正进入了角色。所以可以说,主持朱学勤的论文答辩这件事,是导致我在九十年代进行反思的重要诱因。他的论文引发了我对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思考。这一思考延续到本世纪末,直到一九九九年我才以通信形式写了长篇论文《与友人谈社约论书》,作为自己对这一问题探讨的思想小结。② “反思五四”则有涉许纪霖。1993年夏,许纪霖承华东师大出版社编审施亚西(杜亚泉儿媳)委托,诚邀元化撰《杜亚泉文选序》,以为纪念——恰逢杜亚泉诞辰120周年,逝世60周年。杜亚泉(1873-1933),浙江绍兴上虞人,新文化运动初年尚主编《东方杂志》,因与《新青年》陈独秀(1879-1942)等展开“东西文化问题论战”而成思想史人物。 元化日记对其执笔《杜亚泉与东西文化论战》实录甚勤甚细,大致是从1993年8月1日始读杜亚泉资料,俟后“读得越多,就越感到杜未被当时以至后代所理解,更未被注意”。③如此不辞酷暑地苦读40天,至9月11日上午起草此稿,连轴伏案疾书十日,终在9月21日“完成第二稿。五百字稿纸三十五张,共一万七千余言,为近年所撰最长之文。连日撰写不辍,实觉筋疲力尽”。④ 元化年逾古稀仍壮怀不已,因为他读杜愈深,愈直觉此即“反思五四”之滥觞。请细味其“夫子自道”: 过去我对五四的认识是基于长期所吸取的大量既定观念,这些既定观念已被我当作不可动摇的信念,深深扎根在我的头脑中,过去所读到的那些资料的汇编,理论的阐释以及史的著述等等,几乎都是在这些既定观念的导引下编写而成的……所以不能使人看到历史事实的全貌和真相。当我着手要写有关杜亚泉的文章时,我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去阅读过去资料汇编等所没有收录的第一手资料。经过阅读和思考,我认为五四精神当然要继承,但五四的一些缺陷(如意图伦理、功利主义、激进情绪、庸俗进化观点等)是不应该继承的。我们要继承的是它好的方面。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