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图书馆机构用户,欢迎您!
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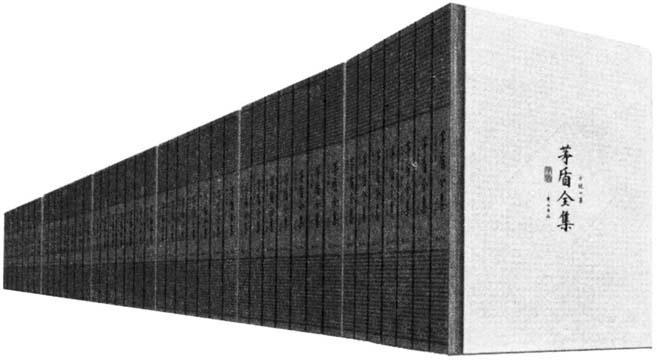 茅盾与宋云彬是现代中国两位文化名家。他们的友情从亲密到冷淡终至隔膜,其间有太多的隐情。茅盾于1896年7月4日生于浙江桐乡乌镇,宋云彬于1897年8月16日生于浙江海宁硖石镇(今硖石街道)。乌镇距海宁很近,同属吴越文化圈。茅盾与宋云彬几近于同乡,年纪相仿,而且两人兼有年少丧父、编辑入职、追求革命等共同经历,在素未谋面之时已具备诸多的相似性,这犹如在冥冥之中为两人的友情做好了准备。1926年,两人在上海相识。1927年的武汉至庐山时期,他们在革命工作以及编辑、创作活动乃至日常生活中保持了密切的关联。宋云彬回上海后,孔德沚为了给宋云彬挂蚊帐而流产的事件让两人关系陷入尴尬,但茅盾当时毕竟没有为此反目。此后,茅盾东渡日本,蛰居租界,远赴新疆,辗转延安,南下香港,其间两人偶有公私事务往来。比如,1937年,茅盾为宋云彬的历史故事集《玄武门之变》作序;1938年,两人与叶圣陶、楼适夷共同创刊《少年先锋》。茅盾与宋云彬友情的逆转发生在桂林。1942年,他们在桂林重逢,且再度接续武汉时期的“近邻”之缘。但不久,坊间传闻“茅公现在不跟云彬交谈了”,宋云彬也渐渐发觉茅盾对自己的冷淡,后来竟发展到公开翻脸、割席而坐的程度。桂林分别后,茅盾与宋云彬曾在重庆见面,“握手互道辛苦”。宋云彬以为“过去的事情大家都忘了”,“朋友毕竟是朋友”①。然而,时间并没有弥合两人友谊的巨大裂缝,事隔多年后,茅盾依然耿耿于怀,不断著文书愤。 沿着茅盾与宋云彬友情嬗变的轨迹,我们很自然地会产生两个问题:一是桂林时期茅盾与宋云彬何以隔膜至此?二是茅盾与宋云彬之间的分歧到底孰是孰非?要对这些问题做出考辨,首先要从两人对彼此友情的言说文字入手。关于茅盾和宋云彬之间的友情以及矛盾纠葛,两人都留下了相关的文字,但是,数量反差极大。在整个过程中,宋云彬仅在1946年写了一篇回忆性散文《沈雁冰(茅盾)》②(以下作《沈雁冰》),之后几乎一言不发。而茅盾对宋云彬及两人关系的书写却长达半个多世纪之久,从1927年创作的《云少爷与草帽》等文学作品,到桂林时期的《雨天杂写之四》,再到1950年代《霜叶红似二月花》和《劫后拾遗》的新版后记,以及晚年的《沉痛哀悼邵荃麟同志》《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桂林春秋》等文章,都有宋云彬的身影。两人对彼此的书写,不仅在数量上不对等,在情感基调上也显得不对称。宋云彬的《沈雁冰》以敬慕、坦诚和忧伤为情感主调。宋云彬介绍了茅盾的文学成就,也介绍了他与茅盾从相识、相知、相伴到产生矛盾的过程。宋云彬指出:“雁冰最大的成就就是创作。他有高深的文学修养,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而观察深刻,态度严肃,这才使他在创作方面有这样大的成就。”③同时,宋云彬也坦率地承认他并不认可茅盾所有的作品,比如一些散文、杂感和历史小说成就并不高。该文还对两人产生矛盾的事情做出了很节制的解释,并且对两人友谊的结局表现出感伤和惋惜。相较而言,茅盾对两人关系的书写则充满复杂的变奏。在早期关于牯岭经历的书写中,茅盾毫不掩饰对那位洒脱的“云少爷”的欣赏与喜爱。到了桂林时期和1950年代,茅盾的笔下开始出现对宋云彬的暗示性嘲讽。到了晚年,茅盾的文章在对宋云彬指名道姓的指责、挖苦之外又增添了一些怨气。显然,在茅盾半个多世纪的书写中存在巨大的情感反差,也存在自相矛盾。另外,对于不少事件,茅盾与宋云彬更是各执一词、说法相异。结合相关的史料,潜入这些文本的缝隙,或许可以有助于我们窥测隐情,接近真相。 茅盾和宋云彬对关键性事件的分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是关于早年友谊的书写。宋云彬的《沈雁冰》追述了两人从武汉到牯岭时期过从甚密、相得甚欢的友谊。宋云彬回忆与茅盾一起编辑《汉口民国日报》,因为武汉天气热,他们白天睡觉,晚上工作,“我们在稿子发齐,大样看过以后,总是聊天,一直聊到天快亮,才疲倦地入睡”。他们戏称每夜的聊天为“天方夜谈”④。宋云彬得知汪精卫即将实施破坏革命行动的消息后,和茅盾一起离开汉口,乘船到九江,同上庐山,暂居牯岭。牯岭是茅盾在精神上经历幻灭、动摇继而追求的重要地理坐标。正是由于在牯岭与世隔绝般的深入思考,作家“茅盾”才得以诞生。根据宋云彬的回忆可以看出,在牯岭的时空下,他是与茅盾一起切磋文艺、静观时局、摸索前行的战友。关于这段经历,茅盾写了不少作品,其中散文《云少爷与草帽》《上牯岭去》和短篇小说《牯岭之秋》中都出现了“云少爷”,这个人物写的就是宋云彬⑤。茅盾书写牯岭经历的作品明显渗透着苦涩、孤寂的情绪和幻灭、迷茫的体验。而“云少爷”却是这些作品灰暗底色中跳出的一抹灵动的光亮。《云少爷与草帽》穿插了数件宋云彬的趣事,豪爽、洒脱、可爱的“云少爷”跃然纸上。到了《牯岭之秋》,潇洒地摇着白纸扇的“云少爷”一直伴随老明(显然有茅盾的影子),缓解他旅程中的苦闷、疲倦。在这些作品中,“云少爷”是陪主人公一起熬过幻灭、孤寂并能给他带来慰藉的密友,而且作品中的不少细节也与宋云彬的回忆相吻合。可以说,茅盾的这些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宋云彬对两人亲密友谊的描述。但茅盾晚年回顾这段经历时,把两人的友谊写得很冷淡,宋云彬成了可有可无的同行者。茅盾这样写到达南昌之后的心情:“我决定上庐山。宋云彬他们听说我要去庐山定要跟着去游玩,我也不便说明,只好同意。”似乎他并不欢迎宋云彬加入,只是不好意思拒绝,甩不掉,才勉强同行。关于在庐山的居住时间,宋云彬的回忆是陪茅盾在牯岭住了大约二十天,但茅盾的回忆却是宋云彬三五天就下山了:“宋云彬见我三五天内尚不能行动,而庐山名胜他们又已游完,就向我告辞先回上海去了。”⑥在茅盾对牯岭的回忆中,宋云彬只为游山而来,兴尽即返,与他并没有多少交集。这种情感态度不仅迥异于宋云彬的认知,也与他本人早年的相关作品自相矛盾。那么,到底是茅盾早年的文学作品虚情假意,还是晚年的回忆录改写了事实?其实,牯岭时期的茅盾认可创作的文学质地与生活实感之间切近的关系,这种观点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牯岭系列写作具有一定纪实性。茅盾在牯岭经历之后紧接着写的论文《从牯岭到东京》中这样表述这种密切联系:“我是真实地去生活,经验了动乱中国的最复杂的人生的一幕,终于感得了幻灭的悲哀,人生的矛盾,在消沉的心情下,孤寂的生活中,而尚受生活执着的支配,想要以我的生命力的余烬从别方面在这迷乱灰色的人生内发一星微光,于是我就开始创作了,我不是为的要做小说,然后去经验人生。”⑦宋云彬回到上海住进了茅盾的家,《沈雁冰》中这样写道:“雁冰本来和我约定,一到上海就住在他家里,可是他不把他家里的地沚开给我,深恐被检查时出什么乱子,他只写了一封介绍信,要我先去商务印书馆找叶圣陶,他说叶圣陶跟他比邻而居,只要找到了圣陶,他就会带我到他家里。”⑧这段文字说明,宋云彬是应茅盾的邀请到他家暂住。但茅盾却在回忆录中给出事情的另一种版本:“母亲告诉我,宋云彬回到上海,硬要住在我家。”⑨宋云彬俨然成了死皮赖脸要住到茅盾家里的人,这似乎不太可能。宋云彬住进茅盾家里之后,他们关系中最大的不可弥补的遗憾发生了。宋云彬记录如下:“有一桩事情,我到现在还觉得抱歉。德沚因为替我挂蚊帐,她那时已怀了孕,太累了,当天就小产,住进了福民医院。”⑩这段文字讲述了孔德沚为了给宋云彬挂蚊帐而流产的事实,宋云彬一直为此感到愧疚,但并不能说明是否宋云彬主动要求挂蚊帐以及挂蚊帐时宋云彬是否在场。半个世纪之后,茅盾回忆录对这一事件的记录细节清楚:“(宋云彬)每天还要喝酒,有蚊子,要挂帐子,他自己不动手,德沚就腆着个大肚子给他挂,因此摔了一跤,小产了。母亲对宋云彬说:‘从来没有见过你这样的共产党,你让一个大肚子的孕妇给你挂蚊帐,你却坐在旁边看!你家里很有钱(宋家有“宋半城”之称),你为什么不自己找个房子住?’这才把他赶走了。”(11)在这些文字中,宋云彬的形象相当不堪,他懒惰、自私、无赖,是被茅盾母亲逐出家门。流产事件的确会给茅盾及家人带来伤痛,宋云彬也为此愧疚不已。但茅盾描述的细节是否属实,宋云彬是否有直接责任都已无法考证。
茅盾与宋云彬是现代中国两位文化名家。他们的友情从亲密到冷淡终至隔膜,其间有太多的隐情。茅盾于1896年7月4日生于浙江桐乡乌镇,宋云彬于1897年8月16日生于浙江海宁硖石镇(今硖石街道)。乌镇距海宁很近,同属吴越文化圈。茅盾与宋云彬几近于同乡,年纪相仿,而且两人兼有年少丧父、编辑入职、追求革命等共同经历,在素未谋面之时已具备诸多的相似性,这犹如在冥冥之中为两人的友情做好了准备。1926年,两人在上海相识。1927年的武汉至庐山时期,他们在革命工作以及编辑、创作活动乃至日常生活中保持了密切的关联。宋云彬回上海后,孔德沚为了给宋云彬挂蚊帐而流产的事件让两人关系陷入尴尬,但茅盾当时毕竟没有为此反目。此后,茅盾东渡日本,蛰居租界,远赴新疆,辗转延安,南下香港,其间两人偶有公私事务往来。比如,1937年,茅盾为宋云彬的历史故事集《玄武门之变》作序;1938年,两人与叶圣陶、楼适夷共同创刊《少年先锋》。茅盾与宋云彬友情的逆转发生在桂林。1942年,他们在桂林重逢,且再度接续武汉时期的“近邻”之缘。但不久,坊间传闻“茅公现在不跟云彬交谈了”,宋云彬也渐渐发觉茅盾对自己的冷淡,后来竟发展到公开翻脸、割席而坐的程度。桂林分别后,茅盾与宋云彬曾在重庆见面,“握手互道辛苦”。宋云彬以为“过去的事情大家都忘了”,“朋友毕竟是朋友”①。然而,时间并没有弥合两人友谊的巨大裂缝,事隔多年后,茅盾依然耿耿于怀,不断著文书愤。 沿着茅盾与宋云彬友情嬗变的轨迹,我们很自然地会产生两个问题:一是桂林时期茅盾与宋云彬何以隔膜至此?二是茅盾与宋云彬之间的分歧到底孰是孰非?要对这些问题做出考辨,首先要从两人对彼此友情的言说文字入手。关于茅盾和宋云彬之间的友情以及矛盾纠葛,两人都留下了相关的文字,但是,数量反差极大。在整个过程中,宋云彬仅在1946年写了一篇回忆性散文《沈雁冰(茅盾)》②(以下作《沈雁冰》),之后几乎一言不发。而茅盾对宋云彬及两人关系的书写却长达半个多世纪之久,从1927年创作的《云少爷与草帽》等文学作品,到桂林时期的《雨天杂写之四》,再到1950年代《霜叶红似二月花》和《劫后拾遗》的新版后记,以及晚年的《沉痛哀悼邵荃麟同志》《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桂林春秋》等文章,都有宋云彬的身影。两人对彼此的书写,不仅在数量上不对等,在情感基调上也显得不对称。宋云彬的《沈雁冰》以敬慕、坦诚和忧伤为情感主调。宋云彬介绍了茅盾的文学成就,也介绍了他与茅盾从相识、相知、相伴到产生矛盾的过程。宋云彬指出:“雁冰最大的成就就是创作。他有高深的文学修养,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而观察深刻,态度严肃,这才使他在创作方面有这样大的成就。”③同时,宋云彬也坦率地承认他并不认可茅盾所有的作品,比如一些散文、杂感和历史小说成就并不高。该文还对两人产生矛盾的事情做出了很节制的解释,并且对两人友谊的结局表现出感伤和惋惜。相较而言,茅盾对两人关系的书写则充满复杂的变奏。在早期关于牯岭经历的书写中,茅盾毫不掩饰对那位洒脱的“云少爷”的欣赏与喜爱。到了桂林时期和1950年代,茅盾的笔下开始出现对宋云彬的暗示性嘲讽。到了晚年,茅盾的文章在对宋云彬指名道姓的指责、挖苦之外又增添了一些怨气。显然,在茅盾半个多世纪的书写中存在巨大的情感反差,也存在自相矛盾。另外,对于不少事件,茅盾与宋云彬更是各执一词、说法相异。结合相关的史料,潜入这些文本的缝隙,或许可以有助于我们窥测隐情,接近真相。 茅盾和宋云彬对关键性事件的分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是关于早年友谊的书写。宋云彬的《沈雁冰》追述了两人从武汉到牯岭时期过从甚密、相得甚欢的友谊。宋云彬回忆与茅盾一起编辑《汉口民国日报》,因为武汉天气热,他们白天睡觉,晚上工作,“我们在稿子发齐,大样看过以后,总是聊天,一直聊到天快亮,才疲倦地入睡”。他们戏称每夜的聊天为“天方夜谈”④。宋云彬得知汪精卫即将实施破坏革命行动的消息后,和茅盾一起离开汉口,乘船到九江,同上庐山,暂居牯岭。牯岭是茅盾在精神上经历幻灭、动摇继而追求的重要地理坐标。正是由于在牯岭与世隔绝般的深入思考,作家“茅盾”才得以诞生。根据宋云彬的回忆可以看出,在牯岭的时空下,他是与茅盾一起切磋文艺、静观时局、摸索前行的战友。关于这段经历,茅盾写了不少作品,其中散文《云少爷与草帽》《上牯岭去》和短篇小说《牯岭之秋》中都出现了“云少爷”,这个人物写的就是宋云彬⑤。茅盾书写牯岭经历的作品明显渗透着苦涩、孤寂的情绪和幻灭、迷茫的体验。而“云少爷”却是这些作品灰暗底色中跳出的一抹灵动的光亮。《云少爷与草帽》穿插了数件宋云彬的趣事,豪爽、洒脱、可爱的“云少爷”跃然纸上。到了《牯岭之秋》,潇洒地摇着白纸扇的“云少爷”一直伴随老明(显然有茅盾的影子),缓解他旅程中的苦闷、疲倦。在这些作品中,“云少爷”是陪主人公一起熬过幻灭、孤寂并能给他带来慰藉的密友,而且作品中的不少细节也与宋云彬的回忆相吻合。可以说,茅盾的这些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宋云彬对两人亲密友谊的描述。但茅盾晚年回顾这段经历时,把两人的友谊写得很冷淡,宋云彬成了可有可无的同行者。茅盾这样写到达南昌之后的心情:“我决定上庐山。宋云彬他们听说我要去庐山定要跟着去游玩,我也不便说明,只好同意。”似乎他并不欢迎宋云彬加入,只是不好意思拒绝,甩不掉,才勉强同行。关于在庐山的居住时间,宋云彬的回忆是陪茅盾在牯岭住了大约二十天,但茅盾的回忆却是宋云彬三五天就下山了:“宋云彬见我三五天内尚不能行动,而庐山名胜他们又已游完,就向我告辞先回上海去了。”⑥在茅盾对牯岭的回忆中,宋云彬只为游山而来,兴尽即返,与他并没有多少交集。这种情感态度不仅迥异于宋云彬的认知,也与他本人早年的相关作品自相矛盾。那么,到底是茅盾早年的文学作品虚情假意,还是晚年的回忆录改写了事实?其实,牯岭时期的茅盾认可创作的文学质地与生活实感之间切近的关系,这种观点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牯岭系列写作具有一定纪实性。茅盾在牯岭经历之后紧接着写的论文《从牯岭到东京》中这样表述这种密切联系:“我是真实地去生活,经验了动乱中国的最复杂的人生的一幕,终于感得了幻灭的悲哀,人生的矛盾,在消沉的心情下,孤寂的生活中,而尚受生活执着的支配,想要以我的生命力的余烬从别方面在这迷乱灰色的人生内发一星微光,于是我就开始创作了,我不是为的要做小说,然后去经验人生。”⑦宋云彬回到上海住进了茅盾的家,《沈雁冰》中这样写道:“雁冰本来和我约定,一到上海就住在他家里,可是他不把他家里的地沚开给我,深恐被检查时出什么乱子,他只写了一封介绍信,要我先去商务印书馆找叶圣陶,他说叶圣陶跟他比邻而居,只要找到了圣陶,他就会带我到他家里。”⑧这段文字说明,宋云彬是应茅盾的邀请到他家暂住。但茅盾却在回忆录中给出事情的另一种版本:“母亲告诉我,宋云彬回到上海,硬要住在我家。”⑨宋云彬俨然成了死皮赖脸要住到茅盾家里的人,这似乎不太可能。宋云彬住进茅盾家里之后,他们关系中最大的不可弥补的遗憾发生了。宋云彬记录如下:“有一桩事情,我到现在还觉得抱歉。德沚因为替我挂蚊帐,她那时已怀了孕,太累了,当天就小产,住进了福民医院。”⑩这段文字讲述了孔德沚为了给宋云彬挂蚊帐而流产的事实,宋云彬一直为此感到愧疚,但并不能说明是否宋云彬主动要求挂蚊帐以及挂蚊帐时宋云彬是否在场。半个世纪之后,茅盾回忆录对这一事件的记录细节清楚:“(宋云彬)每天还要喝酒,有蚊子,要挂帐子,他自己不动手,德沚就腆着个大肚子给他挂,因此摔了一跤,小产了。母亲对宋云彬说:‘从来没有见过你这样的共产党,你让一个大肚子的孕妇给你挂蚊帐,你却坐在旁边看!你家里很有钱(宋家有“宋半城”之称),你为什么不自己找个房子住?’这才把他赶走了。”(11)在这些文字中,宋云彬的形象相当不堪,他懒惰、自私、无赖,是被茅盾母亲逐出家门。流产事件的确会给茅盾及家人带来伤痛,宋云彬也为此愧疚不已。但茅盾描述的细节是否属实,宋云彬是否有直接责任都已无法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