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图书馆机构用户,欢迎您!
骆一禾与存在主义思想的遭遇对他的诗学建构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其诗论充满存在主义因素,但对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的相关思想进行了创造性转化。“诗乃是‘创世’的‘是’”则将希腊哲学传统与希伯来宗教传统结合了起来,是借西方传统而完成的诗学思想。以海德格尔为中介,骆一禾进入了荷尔德林浪漫诗学的核心,最终形成了一种中国式的充满人道主义关怀的新浪漫主义诗学。骆一禾诗歌创作表现出了诗歌隐喻与哲学概念之间的张力,这一经由1960年代的“内部读物”《存在主义哲学》而完成的诗学转化也具有一定的思想史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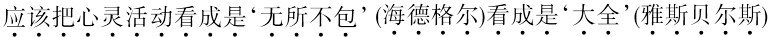 。”(1984年10月9日)④这一美学批判不仅表露出他的批评天才、尤其是方法论思考已开始成熟,而且也流露了他个人的诗学观念和未来的诗学路径。在信的结尾部分他仍借温庭筠说:“当问题被视为心灵活动的不足时,词人温庭筠艺术人格,艺术气质和艺术内形式的匮乏也就进入了视野……温庭筠是一个东方词人,他的艺术得失不在于他的观相,而在于这种观相本身不是一种与心灵活动浑一的观相,这是远远低于东方诗词伟大作品的所在。”⑤这些观点无疑都体现了骆一禾的批评独创性。然而,他援引的存在主义概念就出自《存在主义哲学》这本书: ……对我们来说,存在永远没有尽头,永远是没封闭的;它把我们引向四面八方,而四面八方都是无边无际。它永远让我们发现还另有新的有规定的存在。 这就是我们的前进不已的认识进程。当我们在这个进程中反思的时候,我们就不免要追问什么是存在自身,因为它在一切逐步显现的东西都显现了以后似乎永远只往后退,远离我们。
。”(1984年10月9日)④这一美学批判不仅表露出他的批评天才、尤其是方法论思考已开始成熟,而且也流露了他个人的诗学观念和未来的诗学路径。在信的结尾部分他仍借温庭筠说:“当问题被视为心灵活动的不足时,词人温庭筠艺术人格,艺术气质和艺术内形式的匮乏也就进入了视野……温庭筠是一个东方词人,他的艺术得失不在于他的观相,而在于这种观相本身不是一种与心灵活动浑一的观相,这是远远低于东方诗词伟大作品的所在。”⑤这些观点无疑都体现了骆一禾的批评独创性。然而,他援引的存在主义概念就出自《存在主义哲学》这本书: ……对我们来说,存在永远没有尽头,永远是没封闭的;它把我们引向四面八方,而四面八方都是无边无际。它永远让我们发现还另有新的有规定的存在。 这就是我们的前进不已的认识进程。当我们在这个进程中反思的时候,我们就不免要追问什么是存在自身,因为它在一切逐步显现的东西都显现了以后似乎永远只往后退,远离我们。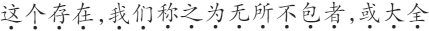 (das Umgreifende);它不是我们某一时候的知识所达到的视野边际,而是一种永远看也看不见的视野边际,却倒一切新的视野边际又都是从它那里产生出来。⑥ “无所不包者”和“大全”同时出现在一句话中,和骆一禾那句话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字面上都非常相似。显然,骆一禾半年后记忆有误,才把“无所不包”当成了海德格尔的概念。但这些援引或误引无伤大雅,它们都表明了骆一禾对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等存在主义思想家的熟悉,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直接影响了骆一禾的诗学批评和诗学观点,使之表现出一种以“心灵”接近“大全”的特征。 骆一禾的其他概念或论断也与存在主义哲学有关,诸如诗是“‘它在’的蛮貊之音”、“它在的语言”、“它在的显示”以及“诗是‘创世’的‘是’字”等。它们与存在主义哲学的联系不是特别明显,骆一禾诗学思想对之所做的转化,是需要我们细致辨析的。 二 骆一禾诗学中的存在主义因素 诚然,众多思想家在骆一禾诗学形成中发挥了作用,诸如斯宾格勒、荣格、汤因比。⑦然而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的影响却被忽略。实际上,在骆一禾的诗论和诗歌批评中常能够看到存在主义的思想因素。其中,雅斯贝尔斯的核心概念“大全”显然是骆一禾钟情的思想,甚至直接促成了骆一禾“诗歌共时体”“诗歌心象学”概念的产生。骆一禾在《火光》中如是论述: 世代合唱的伟大诗歌共时体不仅是一个诗学的范畴,它意味着创作活动所具有的一个更为丰富和渊广的潜在的精神层面,在这个层面自我的价值隆起绝非自我中心主义、唯我论的隆起,从这个精神层面里,生命的放射席卷着来自幽深的声音,有另外的黑暗之中的手臂将它的语言交响于本于我的语言之中,这是一种“它在”的显现……并非只是某种知识渊博的结果,而是生命潜层、它在的语言,一种自身的未竟追蹑未竟之地的探求之声留下的痕迹。这时候,那些容格称为阴影、阿尼姆斯、阿尼玛和自性的层面进入了生命之中,不可说的进入了可说的。我想,所谓“生命自身”乃是一个“生命构造”,诗人所看到和触及的是这个大全,它是“世界”这个词汇里所蕴含的本义……诗人触及了大全、生命构造而不可化学式地“还原为人”……诗歌心象将同一因素的静态解放为活的动势,从而诗学属性里深植着有人的和众神的诗学成分。⑧
(das Umgreifende);它不是我们某一时候的知识所达到的视野边际,而是一种永远看也看不见的视野边际,却倒一切新的视野边际又都是从它那里产生出来。⑥ “无所不包者”和“大全”同时出现在一句话中,和骆一禾那句话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字面上都非常相似。显然,骆一禾半年后记忆有误,才把“无所不包”当成了海德格尔的概念。但这些援引或误引无伤大雅,它们都表明了骆一禾对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等存在主义思想家的熟悉,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直接影响了骆一禾的诗学批评和诗学观点,使之表现出一种以“心灵”接近“大全”的特征。 骆一禾的其他概念或论断也与存在主义哲学有关,诸如诗是“‘它在’的蛮貊之音”、“它在的语言”、“它在的显示”以及“诗是‘创世’的‘是’字”等。它们与存在主义哲学的联系不是特别明显,骆一禾诗学思想对之所做的转化,是需要我们细致辨析的。 二 骆一禾诗学中的存在主义因素 诚然,众多思想家在骆一禾诗学形成中发挥了作用,诸如斯宾格勒、荣格、汤因比。⑦然而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的影响却被忽略。实际上,在骆一禾的诗论和诗歌批评中常能够看到存在主义的思想因素。其中,雅斯贝尔斯的核心概念“大全”显然是骆一禾钟情的思想,甚至直接促成了骆一禾“诗歌共时体”“诗歌心象学”概念的产生。骆一禾在《火光》中如是论述: 世代合唱的伟大诗歌共时体不仅是一个诗学的范畴,它意味着创作活动所具有的一个更为丰富和渊广的潜在的精神层面,在这个层面自我的价值隆起绝非自我中心主义、唯我论的隆起,从这个精神层面里,生命的放射席卷着来自幽深的声音,有另外的黑暗之中的手臂将它的语言交响于本于我的语言之中,这是一种“它在”的显现……并非只是某种知识渊博的结果,而是生命潜层、它在的语言,一种自身的未竟追蹑未竟之地的探求之声留下的痕迹。这时候,那些容格称为阴影、阿尼姆斯、阿尼玛和自性的层面进入了生命之中,不可说的进入了可说的。我想,所谓“生命自身”乃是一个“生命构造”,诗人所看到和触及的是这个大全,它是“世界”这个词汇里所蕴含的本义……诗人触及了大全、生命构造而不可化学式地“还原为人”……诗歌心象将同一因素的静态解放为活的动势,从而诗学属性里深植着有人的和众神的诗学成分。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