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图书馆机构用户,欢迎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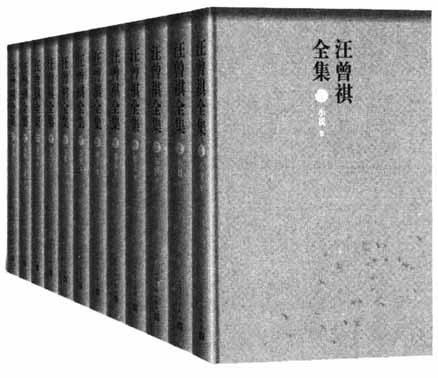 汪曾祺写过《〈职业〉自赏》①,其中提到:“有不少人问我:‘你自己最满意的小说是哪几篇?’这倒很难回答!。只能老实说:大部分都比较满意。‘哪一篇最满意?’一般都以为《受戒》《大淖记事》是我的代表作,似乎已有定评,但我的回答出乎一些人的意外:《职业》。” 不过,要探讨汪曾祺前后期风格的延续与变化,或许《异秉》比《职业》更合适。相对于篇幅短小精干的《职业》,《异秉》的体量更大,结构、语言、风格变化更显明,也更能体现汪曾祺从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的创作探索历程。 汪曾祺曾经在1989年接受采访时说:“我恢复了自己在四十年代曾经追求的创作道路,就是说,我在八十年代前后的创作,跟四十年代衔接起来。”②这种“衔接”最好的体现,便是对四十年代作品的改写与重写。像《复仇》③《鸡鸭名家》④《职业》⑤,前后两版比较,都有大量的异文,但主体结构未变。《受戒》⑥前半段化自《庙与僧》⑦。而《异秉》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与《鸡鸭名家》《受戒》一样,都是写作者最熟悉最怀念的高邮生活,但前后版本写作风格变化之大,在汪曾祺“衔接”1940年代作品中,首屈一指。 从1941年到1980年,汪曾祺将《异秉》这个题材写过三次,第一次的题目叫《灯下》,当时汪曾祺还是西南联大中文系二年级的学生;第二次发表于1948年(由于写作时间存在疑问,本文依据发表时间,称为“1948年版”),标题叫《异秉》;第三次是1980年,汪曾祺刚重拾小说之笔,笔下流出的第一篇小说,既不是一出即震惊文坛的《受戒》,也不是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的《大淖记事》,而是这篇旧作重写的《异秉》。⑧ 受教于沈从文:“要贴到人物写” 汪曾祺的写作之路,是在沈从文的引领下开启的。 1937年,因为日军占领江南各地,汪曾祺在家闲居,身边的新文学书,外国的只有屠格涅夫《猎人日记》,中国的只有上海一家野鸡书店盗印的《沈从文小说选》。“两年中,我反反复复地看着的,就是这两本书。所以反复地看,一方面是因为没有别的好书看,一方面也因为这两本书和我的气质比较接近。我觉得这两本书某些地方很相似。这两本书甚至形成了我对文学、对小说的概念……我在中学时并未有志于文学。在昆明参加大学联合招生,在报名书上填写‘志愿’时,提笔写下了‘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是和读了《沈从文小说选》有关系的。”⑨ 汪曾祺在西南联大就读期间,沈从文开了三门选修课:“中国小说史”“创作实习”“各体文习作”。前一门课,沈从文在上海中国公学时就开过了,后面两门,则与沈从文知名作家身份有关。除此之外,沈从文还担任全校通选课“大一国文”的部分讲授。汪曾祺在1939年秋季入学,他又是奔着沈从文才考的西南联大中文系,所以,汪曾祺应该一年级即已开始受教于沈从文⑩。 比他高一年级的外文系学长许渊冲说汪曾祺“一看就知道是中国文学系才华横溢的未来作家。他在联大生活自由散漫,甚至吊儿郎当,高兴时就上课,不高兴就睡觉,晚上泡茶馆或上图书馆,把黑夜当白天”(11),这也是很多人对汪曾祺的印象。但是,沈从文的每门课,汪曾祺都会选,都认真上,与他对其它课的态度大不相同。 也是借助汪曾祺后来的回忆,旁人才能了解沈从文在西南联大上课的方式: 沈先生是凤凰人,说话湘西口音很重,声音又小,简直听不清他说的是什么。他讲课可以说是毫无系统。没有课本,也不发讲义。只是每星期让学生写一篇习作,第二星期上课时就学生的习作讲一些有关的问题。《创作实习》由学生随便写什么都可以,《各体文习作》有时会出一点题目。我记得他给我的上一班出过一个题目:《我们的小庭院有什么》。有几个同学写的散文很不错,都由沈先生介绍在报刊上发表了。他给我的下一班出过一个题目,这题目有点怪:“记一间屋子的空气”。我那一班他出过什么题目,我倒记不得了。 ……沈先生教写作,用笔的时候比用口的时候多。他常常在学生的习作后面写很长的读后感(有时比原作还长)。或谈这篇作品,或由此生发开去,谈有关的创作问题。这些读后感都写得很精彩,集中在一起,会是一本很漂亮的文论集。可惜一篇也没有保存下来,都失散了。(12) 沈从文把《我们的小庭院有什么》《记一间屋子的空气》这一类的题目习作叫“车零件”,说:“先得学会车零件,然后才能学组装。”“零件”车得少了,基本功不够。写的东西就不耐读,不吸引人。这种方式汪曾祺很赞同,他自己早期的作品,大多是“车零件”,不追求鸿篇巨制,甚至不是完整的故事——这其实也是鲁迅说的“宁可将可作小说的材料缩成Sketch(速写),决不将Sketch材料拉成小说”(13)。 沈从文还有一句话,翻来覆去地讲,汪曾祺也记了一辈子,那就是“要贴到人物写”。汪曾祺自己行文有时用的是“贴着人物写”,其实是将湘西话翻译成了普通话。“贴到人物写”,这句话看上去很简单,但能听懂的人不多。汪曾祺回忆说“我们有的同学不懂这话是什么意思”,当时班上,能理解、接受沈从文这一文学观念的,恐怕只是少数。
汪曾祺写过《〈职业〉自赏》①,其中提到:“有不少人问我:‘你自己最满意的小说是哪几篇?’这倒很难回答!。只能老实说:大部分都比较满意。‘哪一篇最满意?’一般都以为《受戒》《大淖记事》是我的代表作,似乎已有定评,但我的回答出乎一些人的意外:《职业》。” 不过,要探讨汪曾祺前后期风格的延续与变化,或许《异秉》比《职业》更合适。相对于篇幅短小精干的《职业》,《异秉》的体量更大,结构、语言、风格变化更显明,也更能体现汪曾祺从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的创作探索历程。 汪曾祺曾经在1989年接受采访时说:“我恢复了自己在四十年代曾经追求的创作道路,就是说,我在八十年代前后的创作,跟四十年代衔接起来。”②这种“衔接”最好的体现,便是对四十年代作品的改写与重写。像《复仇》③《鸡鸭名家》④《职业》⑤,前后两版比较,都有大量的异文,但主体结构未变。《受戒》⑥前半段化自《庙与僧》⑦。而《异秉》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与《鸡鸭名家》《受戒》一样,都是写作者最熟悉最怀念的高邮生活,但前后版本写作风格变化之大,在汪曾祺“衔接”1940年代作品中,首屈一指。 从1941年到1980年,汪曾祺将《异秉》这个题材写过三次,第一次的题目叫《灯下》,当时汪曾祺还是西南联大中文系二年级的学生;第二次发表于1948年(由于写作时间存在疑问,本文依据发表时间,称为“1948年版”),标题叫《异秉》;第三次是1980年,汪曾祺刚重拾小说之笔,笔下流出的第一篇小说,既不是一出即震惊文坛的《受戒》,也不是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的《大淖记事》,而是这篇旧作重写的《异秉》。⑧ 受教于沈从文:“要贴到人物写” 汪曾祺的写作之路,是在沈从文的引领下开启的。 1937年,因为日军占领江南各地,汪曾祺在家闲居,身边的新文学书,外国的只有屠格涅夫《猎人日记》,中国的只有上海一家野鸡书店盗印的《沈从文小说选》。“两年中,我反反复复地看着的,就是这两本书。所以反复地看,一方面是因为没有别的好书看,一方面也因为这两本书和我的气质比较接近。我觉得这两本书某些地方很相似。这两本书甚至形成了我对文学、对小说的概念……我在中学时并未有志于文学。在昆明参加大学联合招生,在报名书上填写‘志愿’时,提笔写下了‘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是和读了《沈从文小说选》有关系的。”⑨ 汪曾祺在西南联大就读期间,沈从文开了三门选修课:“中国小说史”“创作实习”“各体文习作”。前一门课,沈从文在上海中国公学时就开过了,后面两门,则与沈从文知名作家身份有关。除此之外,沈从文还担任全校通选课“大一国文”的部分讲授。汪曾祺在1939年秋季入学,他又是奔着沈从文才考的西南联大中文系,所以,汪曾祺应该一年级即已开始受教于沈从文⑩。 比他高一年级的外文系学长许渊冲说汪曾祺“一看就知道是中国文学系才华横溢的未来作家。他在联大生活自由散漫,甚至吊儿郎当,高兴时就上课,不高兴就睡觉,晚上泡茶馆或上图书馆,把黑夜当白天”(11),这也是很多人对汪曾祺的印象。但是,沈从文的每门课,汪曾祺都会选,都认真上,与他对其它课的态度大不相同。 也是借助汪曾祺后来的回忆,旁人才能了解沈从文在西南联大上课的方式: 沈先生是凤凰人,说话湘西口音很重,声音又小,简直听不清他说的是什么。他讲课可以说是毫无系统。没有课本,也不发讲义。只是每星期让学生写一篇习作,第二星期上课时就学生的习作讲一些有关的问题。《创作实习》由学生随便写什么都可以,《各体文习作》有时会出一点题目。我记得他给我的上一班出过一个题目:《我们的小庭院有什么》。有几个同学写的散文很不错,都由沈先生介绍在报刊上发表了。他给我的下一班出过一个题目,这题目有点怪:“记一间屋子的空气”。我那一班他出过什么题目,我倒记不得了。 ……沈先生教写作,用笔的时候比用口的时候多。他常常在学生的习作后面写很长的读后感(有时比原作还长)。或谈这篇作品,或由此生发开去,谈有关的创作问题。这些读后感都写得很精彩,集中在一起,会是一本很漂亮的文论集。可惜一篇也没有保存下来,都失散了。(12) 沈从文把《我们的小庭院有什么》《记一间屋子的空气》这一类的题目习作叫“车零件”,说:“先得学会车零件,然后才能学组装。”“零件”车得少了,基本功不够。写的东西就不耐读,不吸引人。这种方式汪曾祺很赞同,他自己早期的作品,大多是“车零件”,不追求鸿篇巨制,甚至不是完整的故事——这其实也是鲁迅说的“宁可将可作小说的材料缩成Sketch(速写),决不将Sketch材料拉成小说”(13)。 沈从文还有一句话,翻来覆去地讲,汪曾祺也记了一辈子,那就是“要贴到人物写”。汪曾祺自己行文有时用的是“贴着人物写”,其实是将湘西话翻译成了普通话。“贴到人物写”,这句话看上去很简单,但能听懂的人不多。汪曾祺回忆说“我们有的同学不懂这话是什么意思”,当时班上,能理解、接受沈从文这一文学观念的,恐怕只是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