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韦伯的思想整体里,宗教社会学占据了极其关键的位置,甚至可以说,它是其中最有精神魅力的遗产。对此,同时代与后世哲学家们首先看到的,乃是韦伯的新教人格所反映出的现代个体的命运,他的禁欲主义要求自我时刻保持理智和道德的真诚,但悖谬的是,越出乎天职观的自我控制,世界的无意义性和价值的多神论困境越发凸显出来。在哲学家们看来,韦伯的宗教社会学孕育出生存主义、虚无主义等现代哲学母题(雅斯培,1992;施特劳斯,2003)。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韦伯的关于新教伦理与现代资本主义的亲和性命题,以及由此展开的世界诸宗教文明比较研究的宏大理论格局,启发了后世社会学家们全盘地思考现代“理性化”的动力及其机制。二十世纪下半叶主流的社会理论范式,无论是哈贝马斯强调主体间互动的沟通行动理论,还是帕森斯强调社会整合的系统理论,实际上都共享了一个信念,即韦伯的比较宗教学研究旨在厘清西方理性化的独特进路,但更重要地,他们认为,经理性祛魅的历程,过去新教为现代社会提供的合理性注定要被克服。哈贝马斯认为超越韦伯的落脚点,在于语言在主体间起到的规范作用(哈贝马斯,2004:260-261),帕森斯则认为在于社会或文化系统的整合。 从表面上看,哲学的解读着力凸显现代人格的尊严与困境,社会学的解读则强调系统的形式与规范,两者角度各异。但在关乎“世俗化”(secularization)等现代性核心特征的判断上,它们之间始终争执不息,直到今天,这一分歧仍然关系到当下西方宗教与社会危机的要害(Joas,2009)。说到底,无论哪方都不免遭遇一种危险,即个体、社会与世界间的意义关联消解了,剩下的要么是没有社会的个体,要么是没有意义的系统。 如果追溯源头,那么我们会发现,两者可以归结到韦伯宗教社会学里的文明①和社会间的张力。受新教传统影响,从一开始,韦伯就有意识地保留了宗教、文明和社会之间的矛盾,在他看来,由宗教形成的文明结构,需要用社会的要素来解释,但文明结构及其背后的宗教情感,又是超越社会的,具有“逃离现世”的救赎的追求(韦伯,2016:352,420-423),问题在于:社会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同宗教文明协调?这是韦伯宗教社会学的核心问题,也是更进一步澄清后世争论的要害。 为此,本文试图将韦伯的宗教社会学置于世纪末德国路德教神学运动的背景,考察他怎样发现“宗教社会”,怎样呈现它及其伦理的意涵。首先,我们将从德意志帝国成立前后的路德教和政治的关系、路德教的社会观两个方面探讨德国宗教社会学的源起和基础,以此作为理解韦伯的宗教社会观的参照;其次,我们将从韦伯的神义论反思,从其世界宗教视野审视他对于基督教价值的总体判断;再次,我们将考察由基督教的神义论而来的实践立场和生活态度问题,揭示基督教伦理背后的诸社会要素及其关系;最后,我们将立足于韦伯对“教权制支配”的论述,从早期教会、中世纪和新教改革以来的近代,考察韦伯笔下每个时期基督教社会的性质、社会与文明的矛盾以及社会逻辑的限度。 二、世纪末德国路德教神学的趋向 韦伯的传记作者们都没有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韦伯的精神成长,和他的虔诚的母系亲属,和他终生密切交往的新教神学家圈子紧密相关(玛丽安妮,2014;Radkau,2009)。韦伯时代的基督教神学发展的趋势,更准确地说,他所直接面对的路德教的神学语境,乃是神学的自由化和历史化的趋向,这对于传统神学世界观,不啻一场颠覆性的变革。 (一)神学的政治 除了学理的方面,另一决定神学历史化之内在精神和价值的因素是德国的现实政治,而且这一因素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就像一些学者指出的,当时的教义学和圣经学的争论,实际上关乎为政治、文化或文化价值观的发展确立规范性原则这一任务(格拉夫,2001:7)。作为终身“以政治作为志业”的学者,韦伯关心着这场争论,也投身其中。他的宗教研究不啻在讲述一个当代的“德国寓言”(Liebersohn,1990)。 宗教的争论,紧紧关联着各个宗教派别的政治立场,随着普鲁士统一德意志的进程,路德教的责任就是要确立新帝国的合法性,因而同时要和南方的天主教势力、西欧的加尔文派、东欧的东正教、土耳其的伊斯兰教势力对抗,最后还要抵抗国内的无神论政党。在帝国建立不久,大卫·施特劳斯(David Strauss)影响深远的宣言性著作《旧信仰与新信仰》(1872)就提出要建立德意志帝国的民族宗教,随即,俾斯麦开展的打击国内外天主教势力的“文化斗争”,鼓舞着路德派的发声。 这一时期,里敕尔的《基督教关于称义与和解的学说》(Die Christliche Lehre von der Rechtfertigung u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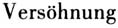
,1870-1874)就是路德派政治纲领的结晶,它延续了施特劳斯的思路,把矛头指向天主教,努力调和路德派教义和现实政治,在里敕尔看来,和解意味着人类生活的完满,它是称义的结果,和天主教教导人们摆脱尘世相反,路德教的“称义”强调通过现实的劳动、并且确认自己的劳动,通过忠诚于职业,履行宗教的献身义务;不仅如此,在劳动中,邻人之爱与共同体关系被激发出来,也只有通过共同体,个体才可能体认恩宠的确定性。说到底,里敕尔张扬的是德意志帝国作为“文化国家”(Kulturstaat)的优越感,他的方案可以说是帝国时代以来,路德教第一次建构宗教社会的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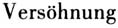 ,1870-1874)就是路德派政治纲领的结晶,它延续了施特劳斯的思路,把矛头指向天主教,努力调和路德派教义和现实政治,在里敕尔看来,和解意味着人类生活的完满,它是称义的结果,和天主教教导人们摆脱尘世相反,路德教的“称义”强调通过现实的劳动、并且确认自己的劳动,通过忠诚于职业,履行宗教的献身义务;不仅如此,在劳动中,邻人之爱与共同体关系被激发出来,也只有通过共同体,个体才可能体认恩宠的确定性。说到底,里敕尔张扬的是德意志帝国作为“文化国家”(Kulturstaat)的优越感,他的方案可以说是帝国时代以来,路德教第一次建构宗教社会的努力。
,1870-1874)就是路德派政治纲领的结晶,它延续了施特劳斯的思路,把矛头指向天主教,努力调和路德派教义和现实政治,在里敕尔看来,和解意味着人类生活的完满,它是称义的结果,和天主教教导人们摆脱尘世相反,路德教的“称义”强调通过现实的劳动、并且确认自己的劳动,通过忠诚于职业,履行宗教的献身义务;不仅如此,在劳动中,邻人之爱与共同体关系被激发出来,也只有通过共同体,个体才可能体认恩宠的确定性。说到底,里敕尔张扬的是德意志帝国作为“文化国家”(Kulturstaat)的优越感,他的方案可以说是帝国时代以来,路德教第一次建构宗教社会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