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图书馆机构用户,欢迎您!
柏拉图将法定义为意图发现实在,法与哲学显得密切相关。柏拉图的探究表明,立法不应着眼于战争的胜利和财富,亦即基于勇敢这一最低的和片面的德性。真正的立法应以完整的德性特别是以理智为目标,将哲学作为立法的基础,以使立法朝向德政。哲学的鉴照可彰显现实法律和政制的缺陷,不断提升其趋向完善。指向德政的立法要求,立法者须明瞭各种德性的自然秩序和人的自然本性,以此为依据给公民们安排恰切的生活方式及相应的法律。
 )是什么,由此对立法的目的提出何种不同的见解,进而指出,立法如何基于追寻完整德性的哲学而朝向德政。 在《米诺斯》(Minos)这部被视为《法义》导言的对话中,柏拉图讨论过一个根本性问题:“法(
)是什么,由此对立法的目的提出何种不同的见解,进而指出,立法如何基于追寻完整德性的哲学而朝向德政。 在《米诺斯》(Minos)这部被视为《法义》导言的对话中,柏拉图讨论过一个根本性问题:“法( )是什么”(林志猛,2010:13)。②柏拉图提到关于
)是什么”(林志猛,2010:13)。②柏拉图提到关于 的三种定义。其一,法是“人们视为合法的东西(
的三种定义。其一,法是“人们视为合法的东西(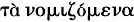 )”(林志猛,2010:14)。这相当于说,法是认可某些东西为合法的过程,类似于言说、观看的过程。不过,过程与结果不能相等同。要理解过程本身,必须从该过程的目的而非结果着手(cf.Best,1980:103)。 由此修正的第二个定义是,法是“公共意见和投票通过的法令”,法整体而言是“城邦的公共意见”(林志猛,2010:16;参见色诺芬,1986:15)。将法看作投票通过的法令,说明法是民众通过一套程序制定出来的。这样的理解基于民主的视角。在民主城邦里,法律是意见的产物,并非由某些睿智者的特殊技艺(立法术)制定。但意见有好坏之别,甚至相互冲突,坏的意见会严重损害城邦。法作为善物,应源于智慧而非意见。 如果法是意见,至少应该说不是有害的意见,而是有用的或真实的意见。真实的意见接近对实在(
)”(林志猛,2010:14)。这相当于说,法是认可某些东西为合法的过程,类似于言说、观看的过程。不过,过程与结果不能相等同。要理解过程本身,必须从该过程的目的而非结果着手(cf.Best,1980:103)。 由此修正的第二个定义是,法是“公共意见和投票通过的法令”,法整体而言是“城邦的公共意见”(林志猛,2010:16;参见色诺芬,1986:15)。将法看作投票通过的法令,说明法是民众通过一套程序制定出来的。这样的理解基于民主的视角。在民主城邦里,法律是意见的产物,并非由某些睿智者的特殊技艺(立法术)制定。但意见有好坏之别,甚至相互冲突,坏的意见会严重损害城邦。法作为善物,应源于智慧而非意见。 如果法是意见,至少应该说不是有害的意见,而是有用的或真实的意见。真实的意见接近对实在( )③的发现,柏拉图由此得出第三个法的定义:“法意图(
)③的发现,柏拉图由此得出第三个法的定义:“法意图( )成为对实在的发现”(林志猛,2010:19)。发现实在,认清事物的本质,乃是哲学的意图之一。从应然的角度看,法应当是好东西,不仅有助于维护共同利益,而且有利于人的完善。应然意义上的法稳定不变,但现实中的立法者未必能制定出善法,实然意义上的法频繁多变。在应然的层面上,治理城邦的正确法律出自那些在如何统治城邦上“有知识的人”(林志猛,2010:25)。这意味着,法本身难以就“是”对实在的发现,而仅仅“意图”发现实在——法处于走向哲学的“路上”。 不过,由于真正的法应秉有哲学的“意图”,超越意见而迈向知识,柏拉图在《法义》中进一步指出,法是关于痛苦、快乐、恐惧、大胆等情感的良好“推理”。在个体灵魂中,各种情感就像肌腱或绳索一样拉扯着人,使人在美德与邪恶之间挣扎。个人应获得关于这些绳索(情感)的“真正推理”,并据此生活。城邦则应采用“有识之士”的推理,设定为“公法”(644c-645c)。因此,法最终可定义为“理智规定的分配”(714a)。恰如牧羊人要给羊群“分配”好牧场,立法者应给人们分配适合其自然本性的工作,以照料好人的灵魂。显然,能作出这种分配的人是有智慧的人(哲人)。在此意义上,立法者应成为立法哲人。 一、立法的目的 《法义》的对话发生在一位雅典的立法哲人与两位克里特和斯巴达的立法者之间。一开始,柏拉图就检审了克里特和斯巴达的立法旨归。这两个城邦都非常好战,其法律制度上的安排着眼于战争的胜利。在克里特立法者看来,战争是一种自然状态,和平不过是空名,“一切城邦对一切城邦的不宣而战(
)成为对实在的发现”(林志猛,2010:19)。发现实在,认清事物的本质,乃是哲学的意图之一。从应然的角度看,法应当是好东西,不仅有助于维护共同利益,而且有利于人的完善。应然意义上的法稳定不变,但现实中的立法者未必能制定出善法,实然意义上的法频繁多变。在应然的层面上,治理城邦的正确法律出自那些在如何统治城邦上“有知识的人”(林志猛,2010:25)。这意味着,法本身难以就“是”对实在的发现,而仅仅“意图”发现实在——法处于走向哲学的“路上”。 不过,由于真正的法应秉有哲学的“意图”,超越意见而迈向知识,柏拉图在《法义》中进一步指出,法是关于痛苦、快乐、恐惧、大胆等情感的良好“推理”。在个体灵魂中,各种情感就像肌腱或绳索一样拉扯着人,使人在美德与邪恶之间挣扎。个人应获得关于这些绳索(情感)的“真正推理”,并据此生活。城邦则应采用“有识之士”的推理,设定为“公法”(644c-645c)。因此,法最终可定义为“理智规定的分配”(714a)。恰如牧羊人要给羊群“分配”好牧场,立法者应给人们分配适合其自然本性的工作,以照料好人的灵魂。显然,能作出这种分配的人是有智慧的人(哲人)。在此意义上,立法者应成为立法哲人。 一、立法的目的 《法义》的对话发生在一位雅典的立法哲人与两位克里特和斯巴达的立法者之间。一开始,柏拉图就检审了克里特和斯巴达的立法旨归。这两个城邦都非常好战,其法律制度上的安排着眼于战争的胜利。在克里特立法者看来,战争是一种自然状态,和平不过是空名,“一切城邦对一切城邦的不宣而战(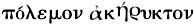 ),天然就一直存在”(626a)。因此,克里特制定的一切公私制度(如公餐、体育训练)皆针对战争。 克里特立法者从战时公餐的必要性,推导出公餐在和平时期也有必要实行。既然源于战争的公餐在各个时期都存在,反过来就可以说,战争是永恒的。有论者尖锐地指出,克里特立法者将“永无休止的战争”与始终有效的合法习俗结合起来,而形成对战争本质的看法。公餐这个习俗的意义源于其一时的必要性,但在获得意义后,公餐又会通过习俗本身的常态性去时间化,变成一种自然事实。从公餐习俗的暂时性推导出战争的永恒性,这是用个人的习俗经验扭曲实在而产生的相关变种,并不表明克里特的制度指向永恒的实在(cf.Benardete,2000:9-10)。克里特立法者通过将公餐这一“习俗”转变为“自然”,战争的非常态化、暂时性也转变为普遍、永恒和自然的状态。 在探讨立法的目的时,柏拉图为何独出心裁,从立法与战争的关系入手?如果说立法旨在维护正义,岂不更显而易见?无疑,战争或帝国问题是柏拉图有意引导我们思考的重大问题。一旦将战争的胜利和获取作为第一原则,就会滋生帝国的观念。一个城邦若专注于对外战争和对外扩张,势必对内部的政制、法律、教育和公民德性产生重大影响。立法又如何协调对外与对内两种关系?或许,尚武观念应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仅限于一来保护自己,以免受外人奴役;二来取得统治地位,但不企图树立普遍奴役的体系,而仅旨在维持被统治者的利益。(参见亚里士多德,1996:1334a1-4)克里特、斯巴达和雅典都曾试图通过战争不断扩展帝国的版图,但结果均遭致覆灭。因此,立法若仅着眼于从胜利中获取财富、领土等“好东西”,未必能确保城邦的长盛不衰,这对我们现时代仍不失为深刻的启示。
),天然就一直存在”(626a)。因此,克里特制定的一切公私制度(如公餐、体育训练)皆针对战争。 克里特立法者从战时公餐的必要性,推导出公餐在和平时期也有必要实行。既然源于战争的公餐在各个时期都存在,反过来就可以说,战争是永恒的。有论者尖锐地指出,克里特立法者将“永无休止的战争”与始终有效的合法习俗结合起来,而形成对战争本质的看法。公餐这个习俗的意义源于其一时的必要性,但在获得意义后,公餐又会通过习俗本身的常态性去时间化,变成一种自然事实。从公餐习俗的暂时性推导出战争的永恒性,这是用个人的习俗经验扭曲实在而产生的相关变种,并不表明克里特的制度指向永恒的实在(cf.Benardete,2000:9-10)。克里特立法者通过将公餐这一“习俗”转变为“自然”,战争的非常态化、暂时性也转变为普遍、永恒和自然的状态。 在探讨立法的目的时,柏拉图为何独出心裁,从立法与战争的关系入手?如果说立法旨在维护正义,岂不更显而易见?无疑,战争或帝国问题是柏拉图有意引导我们思考的重大问题。一旦将战争的胜利和获取作为第一原则,就会滋生帝国的观念。一个城邦若专注于对外战争和对外扩张,势必对内部的政制、法律、教育和公民德性产生重大影响。立法又如何协调对外与对内两种关系?或许,尚武观念应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仅限于一来保护自己,以免受外人奴役;二来取得统治地位,但不企图树立普遍奴役的体系,而仅旨在维持被统治者的利益。(参见亚里士多德,1996:1334a1-4)克里特、斯巴达和雅典都曾试图通过战争不断扩展帝国的版图,但结果均遭致覆灭。因此,立法若仅着眼于从胜利中获取财富、领土等“好东西”,未必能确保城邦的长盛不衰,这对我们现时代仍不失为深刻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