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图书馆机构用户,欢迎您!
如同很多文化现象一样,游戏在历史进程中,被不同的观察视角理解、界定、阐释。游戏或被看作是严肃的对立面,或被理解为有别于劳作的消遣或教育的手段。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游戏或因迎合社会秩序的运作机制而被推崇,或因其非生产性所具有的颠覆性而遭到排斥。在文学领域,它不仅限于文字游戏,同时也被视为生成自由空间、获得审美经验的可能。随着生存的符号化、数码化的不断加剧,游戏波及、占据生活领域的范围更加扩大,对人的生存、感知与交往方式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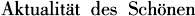 ” 126)。 在中世纪,以教育为目的宗教戏剧与源自非宗教的民间游戏形式构成了杂糅的游戏态势。原始的、怪诞的、异质的形式与出自文明的真善美的形式并存,以致巴赫金(Michail M.Bachtin)可以说“意识狂欢化”(318)。 随着文艺复兴的开始,占主导地位的宗教戏剧逐步让位于获得理性主体地位的人所生成的游戏世界。所谓“世界剧场”概念所表现的一方面是基于游戏特点之一的“装扮”,即通过化妆、面具掩饰自己的真实身份,通过表演在无限世界中为自身定位,尝试对应展现于游戏中的偶然性。无论是莎士比亚式的戏剧还是意大利的情景剧所表现的矛盾性、多样性都构成了颠覆中世纪一统秩序的因素,这种游戏特点为摆脱宫廷戏剧的规范约束、结合民间戏剧特点尝试超越等级界限、协调正在兴起的市民阶层提供了可能。 如果说角色扮演是戏剧的传统特征,那么将角色扮演引入叙事作品则为人文主义对教会机构与世俗的讽刺批判提供了良好的庇护。荷兰人文主义神学家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发表于1509年的《愚人颂》,正是借助游戏的特点,展开了对其所处时代的辛辣讽刺。他并不像后来《少年维特之烦恼》(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s)的作者歌德和《狂人日记》的作者鲁迅那样,通过一个编者的介入来保证所讲故事的“客观性”,而是直接让拟人化的愚笨登场开始她的论说。如此,面具与“真实面目”相互交错,瓦解了安全可靠的叙事与接受视角(Matuschek 54)。对此,游戏因素起了重要作用,角色伪装下的愚笨承接了愚人的传统,以轻率、诙谐、讽刺的笔调援引古希腊罗马与圣经的严肃话题,以致愚人的论说与严肃的真理混杂在一起,难解难分。作为该书的前言,伊拉斯谟把写给莫尔(Thomas More)的信放在了正文之前,他写道:“我发誓,我一生中乐莫大于与你交往。也正因为这样,我以为自己在这方面能做点什么,无奈时不我与,难以对问题做认真严肃的思考,所以我写《愚人颂》以自娱”(1)。而这里的“自娱”在拉丁语原文中正是ludere(游戏)一词。如此,将他的这种写作策略称为“首个明确的文学游戏理论”(Matuschek 56)不无道理。而真正将游戏作为审美的潜力将在18世纪得到重视。
” 126)。 在中世纪,以教育为目的宗教戏剧与源自非宗教的民间游戏形式构成了杂糅的游戏态势。原始的、怪诞的、异质的形式与出自文明的真善美的形式并存,以致巴赫金(Michail M.Bachtin)可以说“意识狂欢化”(318)。 随着文艺复兴的开始,占主导地位的宗教戏剧逐步让位于获得理性主体地位的人所生成的游戏世界。所谓“世界剧场”概念所表现的一方面是基于游戏特点之一的“装扮”,即通过化妆、面具掩饰自己的真实身份,通过表演在无限世界中为自身定位,尝试对应展现于游戏中的偶然性。无论是莎士比亚式的戏剧还是意大利的情景剧所表现的矛盾性、多样性都构成了颠覆中世纪一统秩序的因素,这种游戏特点为摆脱宫廷戏剧的规范约束、结合民间戏剧特点尝试超越等级界限、协调正在兴起的市民阶层提供了可能。 如果说角色扮演是戏剧的传统特征,那么将角色扮演引入叙事作品则为人文主义对教会机构与世俗的讽刺批判提供了良好的庇护。荷兰人文主义神学家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发表于1509年的《愚人颂》,正是借助游戏的特点,展开了对其所处时代的辛辣讽刺。他并不像后来《少年维特之烦恼》(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s)的作者歌德和《狂人日记》的作者鲁迅那样,通过一个编者的介入来保证所讲故事的“客观性”,而是直接让拟人化的愚笨登场开始她的论说。如此,面具与“真实面目”相互交错,瓦解了安全可靠的叙事与接受视角(Matuschek 54)。对此,游戏因素起了重要作用,角色伪装下的愚笨承接了愚人的传统,以轻率、诙谐、讽刺的笔调援引古希腊罗马与圣经的严肃话题,以致愚人的论说与严肃的真理混杂在一起,难解难分。作为该书的前言,伊拉斯谟把写给莫尔(Thomas More)的信放在了正文之前,他写道:“我发誓,我一生中乐莫大于与你交往。也正因为这样,我以为自己在这方面能做点什么,无奈时不我与,难以对问题做认真严肃的思考,所以我写《愚人颂》以自娱”(1)。而这里的“自娱”在拉丁语原文中正是ludere(游戏)一词。如此,将他的这种写作策略称为“首个明确的文学游戏理论”(Matuschek 56)不无道理。而真正将游戏作为审美的潜力将在18世纪得到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