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图书馆机构用户,欢迎您!
黑格尔批评卢梭用契约论来处理国家政治问题是把国家公权力错置于私人财产关系的基础上,以“众意”来充当“公意”或“普遍意志”,认为这是导致法国大革命悲剧的理论上的原因。但黑格尔误解了卢梭的公意,卢梭的公意有其哲学基础,他对公意和众意做了区分,并清醒地认识到由公意所建立起来的完美的民主制只能是一个理想的乌托邦,只是用来促使现实国家政治生活在众意的行使中日益趋向接近的标准,但这一点并没有被法国革命的理论家和黑格尔所理解,卢梭并不能为法国革命的失败承担责任。卢梭的公意除了有理性的根源外,还有公民宗教及其所形成的社会风尚和习惯的根源,在现实生活中公意只有凭借理性和信仰的双管齐下才能对公民社会的建立和运行产生有效的影响。厘清卢梭的这一套以公意为核心的社会契约论,对于我们今天建设法治社会的理论建构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显然,以上契约的三环节是立足于私有财产关系之上的,即:一个是任意(Willkür);一个是“共同意志”(der gemeinsamer Wille),而不是“普遍意志”(der allgemeiner Wille);再一个是出让的财物。②黑格尔指出,在“伦理”(Sittlichkeit)的三大部分即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三者中,契约只适合于市民社会,而不适用于家庭和国家原则。这里的主要矛头是指向契约论的国家学说的,他说:
显然,以上契约的三环节是立足于私有财产关系之上的,即:一个是任意(Willkür);一个是“共同意志”(der gemeinsamer Wille),而不是“普遍意志”(der allgemeiner Wille);再一个是出让的财物。②黑格尔指出,在“伦理”(Sittlichkeit)的三大部分即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三者中,契约只适合于市民社会,而不适用于家庭和国家原则。这里的主要矛头是指向契约论的国家学说的,他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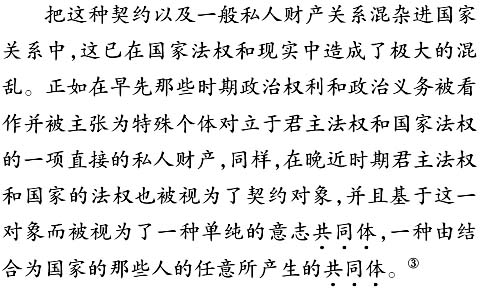 可以看出,这里所讲的“早先那些时期”是指英国“光荣革命”前后霍布斯、洛克等人提出社会契约理论的时期,这些社会契约理论承认君主和国家的法权,却使这种法权基于每个个体的同意之上,但又置于公民立法权的对立面,最终则形成了洛克(及法国的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理论。而所谓“晚近时期”则特指刚刚过去的法国大革命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这时君主和政府本身也被视为公民立法的产物,每个公民通过自己的自由意志而和全体订立的契约成了新型国家的基础。按照黑格尔的意思,这些社会契约在这种理解中都类似于一种财产关系的转让契约,是不恰当地“把私有财产的规定搬到了一个在性质上完全不同而且更高的领域”。④因此黑格尔补充道: 但在国家那里,情况却另是一样,因为不能由于个体的任意而脱离国家,一个人按照其自然方面来说就已经是国家的公民了。人的理性规定就是要在国家中生活,并且当国家还不存在时,理性对建立国家的要求就现成地存在了。……所以这决非依赖于个别人的任意,因而国家并非基于以任意为前提的契约之上。……毋宁说,处于国家之中对于每个人来说是绝对必要的。现代国家的一大进步就是自在自为地保持这同一个目的,而不能每个人在与这一目的相关时都像在中世纪那样按照自己的私人约定来行事。⑤ 换言之,在私有财产关系中起作用的是“共同意志”,即缔约各方的各自任意(
可以看出,这里所讲的“早先那些时期”是指英国“光荣革命”前后霍布斯、洛克等人提出社会契约理论的时期,这些社会契约理论承认君主和国家的法权,却使这种法权基于每个个体的同意之上,但又置于公民立法权的对立面,最终则形成了洛克(及法国的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理论。而所谓“晚近时期”则特指刚刚过去的法国大革命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这时君主和政府本身也被视为公民立法的产物,每个公民通过自己的自由意志而和全体订立的契约成了新型国家的基础。按照黑格尔的意思,这些社会契约在这种理解中都类似于一种财产关系的转让契约,是不恰当地“把私有财产的规定搬到了一个在性质上完全不同而且更高的领域”。④因此黑格尔补充道: 但在国家那里,情况却另是一样,因为不能由于个体的任意而脱离国家,一个人按照其自然方面来说就已经是国家的公民了。人的理性规定就是要在国家中生活,并且当国家还不存在时,理性对建立国家的要求就现成地存在了。……所以这决非依赖于个别人的任意,因而国家并非基于以任意为前提的契约之上。……毋宁说,处于国家之中对于每个人来说是绝对必要的。现代国家的一大进步就是自在自为地保持这同一个目的,而不能每个人在与这一目的相关时都像在中世纪那样按照自己的私人约定来行事。⑤ 换言之,在私有财产关系中起作用的是“共同意志”,即缔约各方的各自任意( )所达成的共同性;相反,在国家中所贯彻的则是“普遍意志”,它不是通过每个人投票所确定的,而是人之为人的一种理性本性,有理性的人生来就是要在国家中过政治生活的,没有人真正愿意和能够遗世独立。所以,普遍意志作为国家的原则是一种更高的伦理原则,而不是一种人为建立的契约关系。它是不能用来做交易的。高兆明先生指出,黑格尔在这里犯了一个“逻辑错误”,即他“以公民必须生活在国家中混淆、代替了公民对于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中、对于国家本身合理性根据的追问”⑥。而契约论的最深刻之处在于,“国家公权的合理性,必须从私权中寻求,必须从私权中获得自身存在的合理性辩护”⑦。这是很有见地的。黑格尔把契约仅仅限定为人与人之间的财物的交易,这一开始就走错了方向。且不说基督教的《旧约》《新约》就不是什么财产关系,而是精神信仰的契约;而且即使是世俗的契约关系,也不全是针对“单个的外在事物”。例如,知识产权就不是对物的拥有和交换,而是对思想观念的拥有和交换,所以黑格尔无法从法律上解决知识产权的侵权问题,只好把它归结为一个“面子”问题,“并依靠面子来制止它”。⑧至于像美国立国时那样通过约定宪法来规定政体形式(更不用说美国宪法的前身、1620年的《五月花号公约》了),黑格尔连提都不提。其实,只要不把“契约”的内涵规定得那么狭窄,则婚姻关系和国家法律以至于宗教信仰都可以看作是一种契约。 黑格尔在这里还没有直接点卢梭的名字,而在后面谈国家的部分,他就明确指出他所针对的主要就是卢梭的“公意”学说。他首先承认,卢梭在国家问题的“内在方面”有其卓越的贡献,即在卢梭眼里,以往把国家的产生归结到人类的社会性本能或神的权威,这只是外部的形式,它的内容其实是“思想”或“思维本身”,也就是“意志”;但卢梭这里所理解的意志就其层次来说似乎还不足以达到成为国家原则的高度:
)所达成的共同性;相反,在国家中所贯彻的则是“普遍意志”,它不是通过每个人投票所确定的,而是人之为人的一种理性本性,有理性的人生来就是要在国家中过政治生活的,没有人真正愿意和能够遗世独立。所以,普遍意志作为国家的原则是一种更高的伦理原则,而不是一种人为建立的契约关系。它是不能用来做交易的。高兆明先生指出,黑格尔在这里犯了一个“逻辑错误”,即他“以公民必须生活在国家中混淆、代替了公民对于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中、对于国家本身合理性根据的追问”⑥。而契约论的最深刻之处在于,“国家公权的合理性,必须从私权中寻求,必须从私权中获得自身存在的合理性辩护”⑦。这是很有见地的。黑格尔把契约仅仅限定为人与人之间的财物的交易,这一开始就走错了方向。且不说基督教的《旧约》《新约》就不是什么财产关系,而是精神信仰的契约;而且即使是世俗的契约关系,也不全是针对“单个的外在事物”。例如,知识产权就不是对物的拥有和交换,而是对思想观念的拥有和交换,所以黑格尔无法从法律上解决知识产权的侵权问题,只好把它归结为一个“面子”问题,“并依靠面子来制止它”。⑧至于像美国立国时那样通过约定宪法来规定政体形式(更不用说美国宪法的前身、1620年的《五月花号公约》了),黑格尔连提都不提。其实,只要不把“契约”的内涵规定得那么狭窄,则婚姻关系和国家法律以至于宗教信仰都可以看作是一种契约。 黑格尔在这里还没有直接点卢梭的名字,而在后面谈国家的部分,他就明确指出他所针对的主要就是卢梭的“公意”学说。他首先承认,卢梭在国家问题的“内在方面”有其卓越的贡献,即在卢梭眼里,以往把国家的产生归结到人类的社会性本能或神的权威,这只是外部的形式,它的内容其实是“思想”或“思维本身”,也就是“意志”;但卢梭这里所理解的意志就其层次来说似乎还不足以达到成为国家原则的高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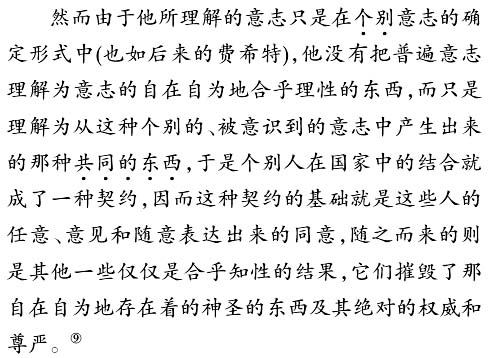 而这样一来,就导致了法国大革命这场“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不可思议的惊人场面”,就是一方面试图砸烂一切现行的制度而仅凭思想来从头建立一个国家,想要给这个国家一个建立在被以为是合乎理性的基础上的宪法,而另一方面由于这只是些缺乏理念的抽象,于是就把这场试验变成了极恐怖极残忍的一场事变。⑩这就是黑格尔对法国大革命的总结,即归咎于卢梭的“公意”,这种公意由于只被理解为“共同的东西”,即共同意志,因而就下降为一种临时性的契约,从“合乎理性的东西”(Vern
而这样一来,就导致了法国大革命这场“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不可思议的惊人场面”,就是一方面试图砸烂一切现行的制度而仅凭思想来从头建立一个国家,想要给这个国家一个建立在被以为是合乎理性的基础上的宪法,而另一方面由于这只是些缺乏理念的抽象,于是就把这场试验变成了极恐怖极残忍的一场事变。⑩这就是黑格尔对法国大革命的总结,即归咎于卢梭的“公意”,这种公意由于只被理解为“共同的东西”,即共同意志,因而就下降为一种临时性的契约,从“合乎理性的东西”(Vern nftige)降低成了“仅仅是合乎知性的(verst
nftige)降低成了“仅仅是合乎知性的(verst ndig)结果”。简言之,在黑格尔看来,卢梭的错误就在于把“公意”仅仅理解为“共同意志”而不是“普遍意志”,理解为具体可操作的任意的契约,而不是神圣的伦理原则。(11)而正确的理解则应当把国家建立在理性的理念之上,这样就可以看出:
ndig)结果”。简言之,在黑格尔看来,卢梭的错误就在于把“公意”仅仅理解为“共同意志”而不是“普遍意志”,理解为具体可操作的任意的契约,而不是神圣的伦理原则。(11)而正确的理解则应当把国家建立在理性的理念之上,这样就可以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