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图书馆机构用户,欢迎您!
西安事变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关键事件,也是国民党在大陆最终溃败的远因之一。国民党作为一个“失败的政府”,在播迁台湾后需要对民众和友邦作出一个有关“丢失大陆”的历史交代,于是其文宣系统运作出台了《苏俄在中国》一书。在其成书过程中,由于西安事变不能绕过,蒋介石亲笔写下了有关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八页意见。将蒋氏手稿与成书后的《苏俄在中国》进行比较,结合蒋氏希图用文字彰道、明德的成贤作圣心态,我们可以鉴知,当面对以蒋氏第一人称来落笔的文本时,为何国民党文宣尤需用“曲释”操作。探研陈布雷、陶希圣等蒋氏文胆的个人生平,我们亦可窥见他们身为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在文宣“曲释”生涯面前的选择困境。对照德国文化历史学家沃尔夫冈·施伊费尔布什所构建的有关失败文化的范式,我们在此以蒋氏及其政府文宣系统的历史书写——既包括“丢失大陆”这样的致命失败,亦包括西安事变这样的重大失败——为例,揭橥失败者在生产历史纪录过程中的种种复杂诉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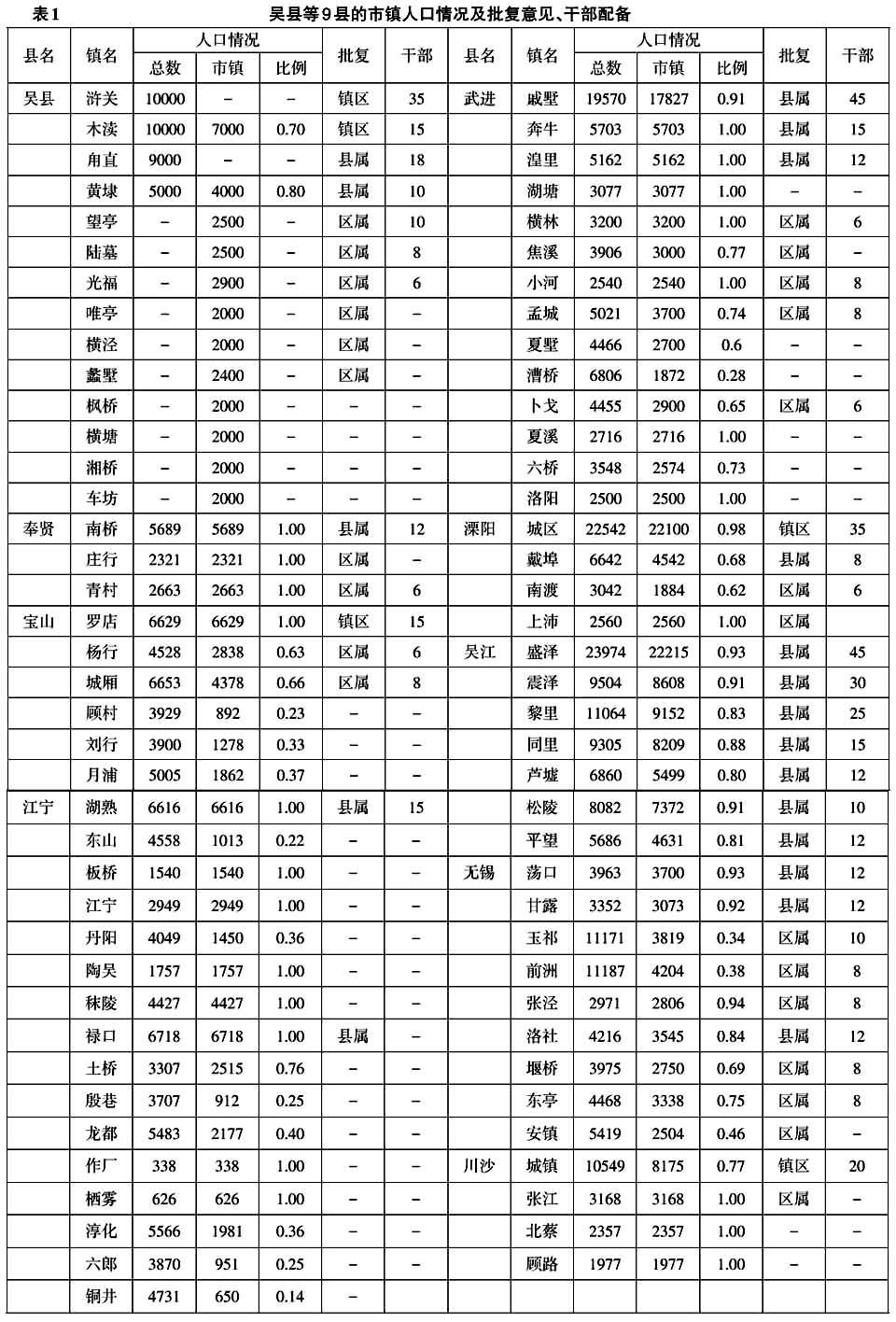 ring)的“我们要么在历史上被当作世界最伟大的政治家,要么被当作最可耻的恶棍”⑦,如果这种说法是真的,那么该格言就以极为吊诡的方式自证其非了。失败者当然参与历史书写,这是毋庸置疑的。有的时候,在一些极端的例子下,人类流传下来的历史,反而是以失败者的叙述为主流的、甚至是仅存的版本。如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后,拜占庭帝国的一批希腊学者出逃到了西方,留下了大批有关奥托曼帝国残暴史的记录。“奥托曼残暴论”时至19世纪二三十年代希腊独立战争前,还被“希腊启蒙运动”(Greek Enlightenment)的知识分子使用作推翻土耳其人统治的宣传工具⑧。 失败者的历史书写,分为个体的(Individual)、集体的(Collective)和政府的(Governmental)三种。个体的如前面所提及的戈林,他在临自杀前曾写给丘吉尔一封信,但直到很久之后才被披露⑨;又如明清鼎革后大批反清汉族知识分子写下的回忆录《扬州十日录》、《明季南略》、《江阴城守纪》、《扬州城守纪略》等,它们中的大部分直到清末排满运动兴起时才重见天日。集体的情况比较复杂。美国南北内战后,原属南部邦联(Confederacy)的南方白人——不仅仅是前奴隶主阶层——普遍感到一种失败情绪和对战前“旧日南方”(ante-bellum South)世风和光景的怀念,这种广泛存在的社会心态被表达为“败局命定”(Lost Cause),它在南方人身上的具体外在表现为:对南方价值的固守,对南方精英人物的赞美,将蓄奴导致战争的起因尽量轻描淡写,希望其子孙后代能够阅读到与联邦版本不同的南方史和内战史等等。在这样的集体社会心态下,美国南方兴起了一场“败局命定”内战史写作运动。“南方历史学会”(Southern Historical Society)由原南军少将Dabney H.Maury于1868年赞助成立,它的刊物专门发表从南方民众、士兵、政治家视角出发的历史回忆文章,事实上,就连“Lost Cause”这个名词,最早虽是由历史学家Edward A.Pollard研究南方战后社会的同名书籍提出的⑩,却是被南军将军Jubal A.Early发表在“南方历史学会”上的数篇回忆文章叫响,并最终被铸造成切中几代南方人集体心理的一个风行词汇。而1889年成立的“邦联退伍老兵联合会”(United Confederate Veterans)也在几年后开始拥有自己的月刊《邦联退伍兵》(Confederate Veteran),它的发行量和刊物质量都非常高。这两则例子可以代表失败者历史书写的“集体”模式。 失败政府的历史书写更为复杂,这是因为失败的政府可以存在有多种形态和模式。粗略划分一下的话,它们可归为三种:一、失败后换届的政府,如在林登·约翰逊任上,越战败局已定,但彻底的停战和撤军要到尼克松任上才发生;中国历史上在不更替朝代的前提下产生的皇权易手,不管是由于皇族内部的杀戮如唐太宗之代唐高祖、朱棣之代建文,还是外族入侵如宋高宗之重续宋祚于临安、晋元帝之重续晋祚于建康,都可归入这一类。二、失败后更换政体/政权的政府,如普法战争导致法兰西第二帝国下台,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登场;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导致德皇威廉二世退位,魏玛共和国成立;如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改朝换代的情形。三、失败后不更换国家首领和政体的政府,如英国在疯王乔治三世手里“失去美洲”(11),日本在昭和天皇手里打输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但英国、日本的君主立宪国体并未改变(12),故此国家首领仍然为原来的君主。无论是换届还是更换政体/政权,新的当权者/胜利者/既得利益者不会、也不需要为过去政权的失败而背负历史包袱,通常的情况下,现政权正好可以藉历史书写把此前造成本国积弱的大灾难或大失败都归罪于前政权。国民党政府的情况比较特殊,以大陆易手的性质而论,它应该被归为第二类;以它自身在播迁台湾后仍保持有政体的完整性和政府首领统治的持续性而论,它又可以被归入第三类。 在现实政治的运作中,政治家们总是需要使用职业公关人员来帮助他们推出自己的观点、政策,有时候,他们会求助于公关业为他们刻意打造亲民的形象(13)。在西方民主语境中所称为“公共关系”(Public Relations)者,在中国政治语境中往往称为“宣传”(Propaganda)。蒋介石无论在大陆阶段还是在台湾阶段,都一向会在宣传领域启用素有人文修养和文字能力的高级幕僚为他撰写重要的文告、自传、政治理论和国际关系论著。借用今天在人文体系内已经成为一门学科研究的“公共关系学”的专业术语,我们不妨说,蒋氏的代笔文胆们颇类于今日欧美政坛专门应对公关信息发布的一类政治顾问,贬义的英文叫法为Spin Doctors。Spin原义为“纺纱”或“旋转”,但用作棒球术语时,专指投球手掷出意图骗过对方击球手的曲线球。在美国俚语中,Spin有欺骗的意思。用在以文字发布为主的政府公关领域上,Spin这个词的中文可以译作“曲释”。 以一个长期政权的失败经历而言,它在致命失败之前往往还会有若干重大失败,这些重大失败又往往是导致它致命失败的远因。对国民党政府来说,“丢失大陆”是它的致命失败,“西安事变”是它的重大失败之一,则它在进行历史书写的时候,这两大事件是无论如何不能绕开的。
ring)的“我们要么在历史上被当作世界最伟大的政治家,要么被当作最可耻的恶棍”⑦,如果这种说法是真的,那么该格言就以极为吊诡的方式自证其非了。失败者当然参与历史书写,这是毋庸置疑的。有的时候,在一些极端的例子下,人类流传下来的历史,反而是以失败者的叙述为主流的、甚至是仅存的版本。如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后,拜占庭帝国的一批希腊学者出逃到了西方,留下了大批有关奥托曼帝国残暴史的记录。“奥托曼残暴论”时至19世纪二三十年代希腊独立战争前,还被“希腊启蒙运动”(Greek Enlightenment)的知识分子使用作推翻土耳其人统治的宣传工具⑧。 失败者的历史书写,分为个体的(Individual)、集体的(Collective)和政府的(Governmental)三种。个体的如前面所提及的戈林,他在临自杀前曾写给丘吉尔一封信,但直到很久之后才被披露⑨;又如明清鼎革后大批反清汉族知识分子写下的回忆录《扬州十日录》、《明季南略》、《江阴城守纪》、《扬州城守纪略》等,它们中的大部分直到清末排满运动兴起时才重见天日。集体的情况比较复杂。美国南北内战后,原属南部邦联(Confederacy)的南方白人——不仅仅是前奴隶主阶层——普遍感到一种失败情绪和对战前“旧日南方”(ante-bellum South)世风和光景的怀念,这种广泛存在的社会心态被表达为“败局命定”(Lost Cause),它在南方人身上的具体外在表现为:对南方价值的固守,对南方精英人物的赞美,将蓄奴导致战争的起因尽量轻描淡写,希望其子孙后代能够阅读到与联邦版本不同的南方史和内战史等等。在这样的集体社会心态下,美国南方兴起了一场“败局命定”内战史写作运动。“南方历史学会”(Southern Historical Society)由原南军少将Dabney H.Maury于1868年赞助成立,它的刊物专门发表从南方民众、士兵、政治家视角出发的历史回忆文章,事实上,就连“Lost Cause”这个名词,最早虽是由历史学家Edward A.Pollard研究南方战后社会的同名书籍提出的⑩,却是被南军将军Jubal A.Early发表在“南方历史学会”上的数篇回忆文章叫响,并最终被铸造成切中几代南方人集体心理的一个风行词汇。而1889年成立的“邦联退伍老兵联合会”(United Confederate Veterans)也在几年后开始拥有自己的月刊《邦联退伍兵》(Confederate Veteran),它的发行量和刊物质量都非常高。这两则例子可以代表失败者历史书写的“集体”模式。 失败政府的历史书写更为复杂,这是因为失败的政府可以存在有多种形态和模式。粗略划分一下的话,它们可归为三种:一、失败后换届的政府,如在林登·约翰逊任上,越战败局已定,但彻底的停战和撤军要到尼克松任上才发生;中国历史上在不更替朝代的前提下产生的皇权易手,不管是由于皇族内部的杀戮如唐太宗之代唐高祖、朱棣之代建文,还是外族入侵如宋高宗之重续宋祚于临安、晋元帝之重续晋祚于建康,都可归入这一类。二、失败后更换政体/政权的政府,如普法战争导致法兰西第二帝国下台,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登场;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导致德皇威廉二世退位,魏玛共和国成立;如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改朝换代的情形。三、失败后不更换国家首领和政体的政府,如英国在疯王乔治三世手里“失去美洲”(11),日本在昭和天皇手里打输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但英国、日本的君主立宪国体并未改变(12),故此国家首领仍然为原来的君主。无论是换届还是更换政体/政权,新的当权者/胜利者/既得利益者不会、也不需要为过去政权的失败而背负历史包袱,通常的情况下,现政权正好可以藉历史书写把此前造成本国积弱的大灾难或大失败都归罪于前政权。国民党政府的情况比较特殊,以大陆易手的性质而论,它应该被归为第二类;以它自身在播迁台湾后仍保持有政体的完整性和政府首领统治的持续性而论,它又可以被归入第三类。 在现实政治的运作中,政治家们总是需要使用职业公关人员来帮助他们推出自己的观点、政策,有时候,他们会求助于公关业为他们刻意打造亲民的形象(13)。在西方民主语境中所称为“公共关系”(Public Relations)者,在中国政治语境中往往称为“宣传”(Propaganda)。蒋介石无论在大陆阶段还是在台湾阶段,都一向会在宣传领域启用素有人文修养和文字能力的高级幕僚为他撰写重要的文告、自传、政治理论和国际关系论著。借用今天在人文体系内已经成为一门学科研究的“公共关系学”的专业术语,我们不妨说,蒋氏的代笔文胆们颇类于今日欧美政坛专门应对公关信息发布的一类政治顾问,贬义的英文叫法为Spin Doctors。Spin原义为“纺纱”或“旋转”,但用作棒球术语时,专指投球手掷出意图骗过对方击球手的曲线球。在美国俚语中,Spin有欺骗的意思。用在以文字发布为主的政府公关领域上,Spin这个词的中文可以译作“曲释”。 以一个长期政权的失败经历而言,它在致命失败之前往往还会有若干重大失败,这些重大失败又往往是导致它致命失败的远因。对国民党政府来说,“丢失大陆”是它的致命失败,“西安事变”是它的重大失败之一,则它在进行历史书写的时候,这两大事件是无论如何不能绕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