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作为“开端”的“历史现场” 法国历史学家傅勒在谈到法国大革命时说,“大革命的得失主要还不在于原因和结果如何,而在于一个社会向着它的所有可能性敞开了。它发明了一种政治话语和政治实践,从此我们不断地生活于其中。”① “新文化运动”是否也为现代中国“发明”了一种奠基性的“政治话语和政治实践”?我们今天的生活在何种程度上还保持着与“新文化运动”的精神联系?近一两年来,新文化运动百年纪念的帷幕已经缓缓拉开,但对这样基础性问题的回应却极为少见。相反,在“去政治化”的政治议程中,“新文化运动”已被“还原”为可“触摸”的一些琐碎“细节”,人们似乎更热衷谈论“五四”那天的天气、花草和日常生活,更看重历史当事人的“具体印象”。不错,这种叙事策略有其可以理解的缘起,甚至也符合历史学的当下潮流,只在这种“历史还原”中,“新文化”失去了“精神”,“运动”也大抵成了一部分人的“诡计”和“忽悠”。 “重返历史现场”,是近些年来比较流行的修辞。从史学研究的角度说,它表达的是对日渐趋同和固化的“新文化运动”研究范式的不满,希望“亲临其境”,以便弄清楚“新文化运动”的本源和本相。近百年来,“文化危机和文化认同在中国相伴而生,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相互激荡。”②在这个过程中,“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叙事确实常常陷入“纪念性史学的怪圈”,它几乎成为了一种“身份话语”或“认同的历史”,以至于“为奠基者歌功颂德或对离经叛道者大加挞伐”③,正因为如此,“那些为之唱颂歌的人唯恐与它靠得还不够近;而那些与之保持一定距离的人则唯恐离得还不够远。”④若是考虑到新文化运动研究中普遍存在的“历史对象概念化”的趋向,考虑到各种政治力量、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对历史对象改窜和涂饰,这种“重返历史现场”的研究诉求显然具有不容低估的意义。 然而,也应该认识到,“重返历史现场”这一修辞所蕴含的合理诉求只有在另一种思想逻辑的调节之下才能获得其有效性,这就是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叙事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的历史认知问题。作为现代中国的“起源叙事”,它不仅是政客之间的一笔争议迭出的历史遗产,它也同时参与塑造了我们对“当代”的理解和对“未来”的想象,正如傅勒在谈及法国大革命史的研究时所说的那样,这是一笔远未耗尽的思想遗产,它不仅维续着“起源叙事”的“社会职能”,“事实上,这种遗产仍在继续主导着未来的表现,就像一种古老的地层被后来的沉积物层层覆盖之后,在不断地塑造地势和风景。”⑤因此,它的“历史现场”不只存在于过去的某一段时间,也存在于被不断拉长和延伸的情境之中,说它“‘解释’了我们当代的历史是不够的。它就是我们的当代史”⑥。 在《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一文中,现代史学者王奇生通过对《新青年》杂志“发迹史”的详细考察来揭示“新文化”的“运动”特性,作者指出,“《新青年》并非一创刊就名扬天下,景从如流;‘新文化’亦非一开始就声势浩然,应者云集。”⑦它们最终能够名扬天下、汇成时代潮流,所仰赖的便是呼风唤雨的“运动”手段。因此,该文把视线从人们一向关注的思想言论方面移开,转而关注新文化的“传播策略”及其与社会环境的互动过程。在这一视角下,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青年》同人充分显现了作为“运动家”的本相。作为一代新式文人,他们能够娴熟地运用现代媒体技术来推动舆论、制造声势,以达致自己的目标,如借鉴《甲寅》以真假莫辨的“通信”招徕读者、自编自导“双簧戏”以引发新旧文学论战、攻击《东方杂志》以夺取媒体优势等,正是通过这些手段,才使得《新青年》从一本无人问津的“普通刊物”逐渐变成了“时代号角”,使得“新文化”由涓涓细流渐次汇成洪波大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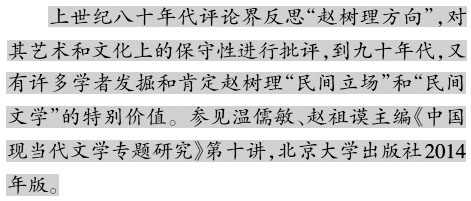
这里的所谓“运动”,固然也包含社会动员的意思,但它主要还是指新文化倡导者的宣传和鼓动,用时下的话来说,就是“运作”或“造势”。因此,在具体描述新文化的“运动”特征以及“运动家”们的鼓动能力时,王奇生使用了“虚张声势”、“夸张的笔法,过激的言词”、“故作危言,以耸国民”,以及“炒作”、“表演”、“忽悠”等不无贬义的语词。这种措辞无疑严重偏离了有关新文化运动的经典表述,它所传达出来的是对这段历史的“近距离”的观感,而不是一种对于原始教义的思想膜拜。作者的初衷自然不是要贬损“新文化运动”,而是为了尽可能接近“历史现场”。 就史学研究来说,从关注“思想”、“意义”到关注过程,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研究由思想史向社会史的范式转换,与这一转变相伴的是研究者问题意识与研究旨趣的变化,他们不但不再从新文化运动的“历史统一性”中分享意义,相反,他们在学界公认的“经典表述”中发现了无法弥合的裂痕。王奇生指出,“新文化运动以1915年《新青年》(首卷名《青年杂志》)创刊为开端,以‘民主’、‘科学’为旗帜。这一说法,早已成为学界一致认同的经典表述。然而,在‘新文化运动’这一概念最初流传之际,时人心目中的‘新文化运动’多以‘五四’为端绪,而且身历者所认知的‘新文化’、‘新思潮’,其精神内涵既不一致,与后来史家的惯常说法亦有相当的出入。后来史家所推崇、所眷顾的一些思想主张,在当时并未形成多大反响,而当时人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却早已淡出了史家的视野。”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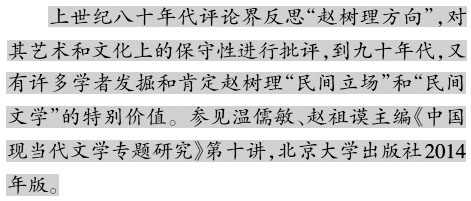 这里的所谓“运动”,固然也包含社会动员的意思,但它主要还是指新文化倡导者的宣传和鼓动,用时下的话来说,就是“运作”或“造势”。因此,在具体描述新文化的“运动”特征以及“运动家”们的鼓动能力时,王奇生使用了“虚张声势”、“夸张的笔法,过激的言词”、“故作危言,以耸国民”,以及“炒作”、“表演”、“忽悠”等不无贬义的语词。这种措辞无疑严重偏离了有关新文化运动的经典表述,它所传达出来的是对这段历史的“近距离”的观感,而不是一种对于原始教义的思想膜拜。作者的初衷自然不是要贬损“新文化运动”,而是为了尽可能接近“历史现场”。 就史学研究来说,从关注“思想”、“意义”到关注过程,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研究由思想史向社会史的范式转换,与这一转变相伴的是研究者问题意识与研究旨趣的变化,他们不但不再从新文化运动的“历史统一性”中分享意义,相反,他们在学界公认的“经典表述”中发现了无法弥合的裂痕。王奇生指出,“新文化运动以1915年《新青年》(首卷名《青年杂志》)创刊为开端,以‘民主’、‘科学’为旗帜。这一说法,早已成为学界一致认同的经典表述。然而,在‘新文化运动’这一概念最初流传之际,时人心目中的‘新文化运动’多以‘五四’为端绪,而且身历者所认知的‘新文化’、‘新思潮’,其精神内涵既不一致,与后来史家的惯常说法亦有相当的出入。后来史家所推崇、所眷顾的一些思想主张,在当时并未形成多大反响,而当时人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却早已淡出了史家的视野。”⑧
这里的所谓“运动”,固然也包含社会动员的意思,但它主要还是指新文化倡导者的宣传和鼓动,用时下的话来说,就是“运作”或“造势”。因此,在具体描述新文化的“运动”特征以及“运动家”们的鼓动能力时,王奇生使用了“虚张声势”、“夸张的笔法,过激的言词”、“故作危言,以耸国民”,以及“炒作”、“表演”、“忽悠”等不无贬义的语词。这种措辞无疑严重偏离了有关新文化运动的经典表述,它所传达出来的是对这段历史的“近距离”的观感,而不是一种对于原始教义的思想膜拜。作者的初衷自然不是要贬损“新文化运动”,而是为了尽可能接近“历史现场”。 就史学研究来说,从关注“思想”、“意义”到关注过程,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研究由思想史向社会史的范式转换,与这一转变相伴的是研究者问题意识与研究旨趣的变化,他们不但不再从新文化运动的“历史统一性”中分享意义,相反,他们在学界公认的“经典表述”中发现了无法弥合的裂痕。王奇生指出,“新文化运动以1915年《新青年》(首卷名《青年杂志》)创刊为开端,以‘民主’、‘科学’为旗帜。这一说法,早已成为学界一致认同的经典表述。然而,在‘新文化运动’这一概念最初流传之际,时人心目中的‘新文化运动’多以‘五四’为端绪,而且身历者所认知的‘新文化’、‘新思潮’,其精神内涵既不一致,与后来史家的惯常说法亦有相当的出入。后来史家所推崇、所眷顾的一些思想主张,在当时并未形成多大反响,而当时人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却早已淡出了史家的视野。”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