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图书馆机构用户,欢迎您!
《兄弟》在中法两国批评界第一时间的接受中呈现出巨大的差异,反映出两国批评家不同的审美习惯与思维方法。本文试图从法国批评界对《兄弟》的评论出发,以“真实”与“诙谐”两个角度切入,梳理与分析其中的关键内容,探讨其中所蕴含的思维逻辑与文学传统,并将其与本土的批评状况作出比较,从而思考在何种意义上异域之眼的观照能够对中国的审美范式与批评话语予以启示和补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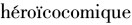 )般的“长河小说”②(le roman-fleuve)是对从文革到当下中国的“极度写实”③(L'extrême réalisme)。2008年末,《兄弟》荣获法国《国际信使报》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可以说,《兄弟》在法国一经推出,就受到了法语批评界的一致好评,而这与其在中国的遭遇恰成鲜明对照。《兄弟》下部在大陆出版后的半年内,批评界对这部小说几乎一片骂声,质疑其“混乱”、“粗鄙”、“诡异”、“失实”,一直到2006年11月30日陈思和在复旦大学组织座谈会力挺《兄弟》,正面的声音才渐渐多了起来,但批判之声始终不绝。会后余华风趣地说道,“人们告诉我《兄弟》被批评得很多,今天下午复旦这里给我开了一个座谈会,终于有几个说好话的人出来了,我已经等了几个月了”。④ 一部小说在中法两国批评界第一时间的接受呈现出如此巨大的差别甚至导向完全相反的判断,这不能不让人感到诧异。而在这背后所隐藏的批评家本身的审美习惯与文学背景的差别更使得这样一场批评“奇观”成为了值得思考的对象,这便是本文的出发点。2010年杭零、许钧在《文艺争鸣》上发表《〈兄弟〉的不同诠释与接受——余华在法兰西文化语境中的译介》一文,着重分析了何碧玉与安必诺的翻译态度与过程,认为他们“在翻译过程中能够充分重视原作中特有的文学因素和其中裹挟的文化因素的传递,因此也就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译文在语言和风格上的忠实性”,并以此为契机讨论了“翻译现象”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与影响。对于法国批评界究竟如何评论《兄弟》并非其关注的重心。⑤2013年王侃在《文学评论》上发表《翻译和阅读的政治——漫议“西方”、“现代”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体系的调整》一文,其中也探讨了《兄弟》的英、法译本在各自母语国的接受,但主要关注点在于英语译本对原作的“改写”以及由此而来的一整套批评机制问题。他的文章立足于对英文语境的反思与批评,对于翻译相对忠实准确的法国只稍有触及。⑥因此,面对一个相对忠实的译本,法国批评界究竟在说什么,为什么那么说?他们的评论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对中国的批评话语予以补全?本文的目的即在于对以上问题进行细致梳理和分析。 一 《兄弟》,一本真实的小说 《兄弟》在中国大陆一经推出,就立刻被“细节失实”、“言辞粗野”的批评声所笼罩,直到几年之后才渐渐被发掘出小说中对现实的观照。可以说《兄弟》在中国批评界经历了一个从“失实”到“写实”的接受过程。而在法国,“真实”却是法国批评界第一时间不约而同对《兄弟》所做出的判断。2008年3月28日,在《兄弟》法译本正式发行前几天,《每周书评》便率先推出评论,认为读者可以在这本书中读出“关于中国历史的真实主义(vériste)的呈现,从文化大革命直到今天”⑦。“真实主义”本是19世纪末意大利的一个受左拉自然主义影响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流派,通过对社会底层人物的描写进而展开对人性和社会的反思,属于“现实主义”的一个分支。书评作者Jean-Claude Perrier没有使用在法语中更常用的“现实主义”(réaliste)而选择了“真实主义”一词,显然是有意为之:他试图在此突出《兄弟》“真实主义”式的底层视角和批判态度。从中我们也可以读出他对《兄弟》的判断:在李光头、宋刚、林红、童铁匠、余拔牙等等底层小人物身上上演的所有那些时而粗俗时而淫秽时而疯狂时而英勇时而温情的光怪陆离的故事中,包含着余华对于中国整个当代社会进程的思虑和批评。换句话说,Perrier无疑不认为余华的这种“粗鄙修辞”将导致作家批评意识的消解或者说作家与社会现状的妥协,李光头的“成功”与宋刚的“失败”这一让人看似无法接受的结局恰恰是对中国社会一次“真实主义”的解剖。这个判断也成为了日后法国各大报刊所登载书评的一致基调。 不过相比于“真实主义”,更多的报刊选择了“流浪汉小说”(Roman picaresque)一词。比如《国际信使报》在对《兄弟》的授奖词中就说到:“从血腥的文化大革命到野蛮的资本主义,中国四十年的混乱在余华粗犷的笔锋下鱼贯而过。一本伟大的流浪汉小说。”⑧另一篇书评则说,“从文化大革命的残酷与荒诞到红色资本主义的粗暴转型:余华冲刷着近在咫尺的历史,并通过一段段粗犷而疯癫的插曲,使那些后果始终可见的事件一一复活。长河般的叙述,出色的操控,融流浪汉小说、历史传奇与癫狂的诙谐文学为一体”。⑨除此之外,比利时的《自由比利时报》、瑞士的《时间报》等等也纷纷采用了“流浪汉小说”的提法。“流浪汉小说”本是16世纪西班牙流行的一种特殊的文学体裁,西班牙语叫做“La novela picaresca”。“picaresca”一词的词源“pícaro”的意思是“无赖”、“恶棍”,而这种小说的内容也正是通过社会底层的“无赖”、“恶棍”(而且常常是少年)的眼光去观看社会下层的生活,小说的主人公们通常没有明确的道德意识,他们在围困着他们的腐败社会中随遇而安,为了生存下去不择手段地阿谀、钻营、撒谎、诈骗,最终成长为社会的同类,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获得“成功”——一种以放弃道德为代价的成功。此类小说也正是通过描写这些“无赖”与“恶棍”们的堕落生活,折射整个社会的粗野、淫秽和虚伪,从而形成一种揭露。在中国最有名的一部西班牙流浪汉小说便是杨绛翻译的《小癞子》,描写一个离家出走的流浪少年如何在不断更换主人的过程中历经炎凉世态,并最终成为了一个老练的骗子混迹于世,成家立业。在这类小说中,我们能够发现与《兄弟》精神气质上的暗合。虽然李光头并不像“流浪汉小说”惯用的主人公那样在世界上来回游荡,但他在生活中的投机与冒险可谓毫无间断。也正是因为这种“流浪汉小说”文学传统的存在,当欧洲大陆的批评家拿起《兄弟》,看到李光头这个“混世魔王”如何坑蒙拐骗,既被权力倾轧又倾轧权力,最终一步步成为亿万富翁的故事时,他们在小说范式的层面上便毫无接受困难并且自然地认可了其中的叙事方式。在《兄弟》与“流浪汉小说”之间确实存在着可资比较的巨大空间。⑩“流浪汉小说”与“真实主义”小说在欧洲文学传统中的存在,使得余华在中国大陆备受争议的“粗鄙修辞”在法国没有引起任何问题,因为此类修辞在这几类小说中几乎无处不在,“粗鄙”本身并不会引起法国人的惊叹或愤慨,他们也因此更容易穿透表层的粗鄙进入叙事核心。对法国批评家与读者而言这种写作方式的合法性也不言自明,他们从自身已有的文学传统出发,自然地认定这种对现实毫不掩饰的描写本身绝不代表任何作家本人的道德混乱或沦丧,而恰恰意味着一种良心,行文中所有粗俗、荒诞、残酷的写法本身就能够成为对社会现状的反思和批评,因为它恰恰意味着一个作家对现实生活的毫不掩饰与毫不妥协,他要打破一切道德或传统的禁忌把那些正在阴暗角落中发生的事书写下来,大白于世。《自由报》登载了法国记者与余华的一次访谈,其中记录了这样一则对话:
)般的“长河小说”②(le roman-fleuve)是对从文革到当下中国的“极度写实”③(L'extrême réalisme)。2008年末,《兄弟》荣获法国《国际信使报》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可以说,《兄弟》在法国一经推出,就受到了法语批评界的一致好评,而这与其在中国的遭遇恰成鲜明对照。《兄弟》下部在大陆出版后的半年内,批评界对这部小说几乎一片骂声,质疑其“混乱”、“粗鄙”、“诡异”、“失实”,一直到2006年11月30日陈思和在复旦大学组织座谈会力挺《兄弟》,正面的声音才渐渐多了起来,但批判之声始终不绝。会后余华风趣地说道,“人们告诉我《兄弟》被批评得很多,今天下午复旦这里给我开了一个座谈会,终于有几个说好话的人出来了,我已经等了几个月了”。④ 一部小说在中法两国批评界第一时间的接受呈现出如此巨大的差别甚至导向完全相反的判断,这不能不让人感到诧异。而在这背后所隐藏的批评家本身的审美习惯与文学背景的差别更使得这样一场批评“奇观”成为了值得思考的对象,这便是本文的出发点。2010年杭零、许钧在《文艺争鸣》上发表《〈兄弟〉的不同诠释与接受——余华在法兰西文化语境中的译介》一文,着重分析了何碧玉与安必诺的翻译态度与过程,认为他们“在翻译过程中能够充分重视原作中特有的文学因素和其中裹挟的文化因素的传递,因此也就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译文在语言和风格上的忠实性”,并以此为契机讨论了“翻译现象”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与影响。对于法国批评界究竟如何评论《兄弟》并非其关注的重心。⑤2013年王侃在《文学评论》上发表《翻译和阅读的政治——漫议“西方”、“现代”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体系的调整》一文,其中也探讨了《兄弟》的英、法译本在各自母语国的接受,但主要关注点在于英语译本对原作的“改写”以及由此而来的一整套批评机制问题。他的文章立足于对英文语境的反思与批评,对于翻译相对忠实准确的法国只稍有触及。⑥因此,面对一个相对忠实的译本,法国批评界究竟在说什么,为什么那么说?他们的评论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对中国的批评话语予以补全?本文的目的即在于对以上问题进行细致梳理和分析。 一 《兄弟》,一本真实的小说 《兄弟》在中国大陆一经推出,就立刻被“细节失实”、“言辞粗野”的批评声所笼罩,直到几年之后才渐渐被发掘出小说中对现实的观照。可以说《兄弟》在中国批评界经历了一个从“失实”到“写实”的接受过程。而在法国,“真实”却是法国批评界第一时间不约而同对《兄弟》所做出的判断。2008年3月28日,在《兄弟》法译本正式发行前几天,《每周书评》便率先推出评论,认为读者可以在这本书中读出“关于中国历史的真实主义(vériste)的呈现,从文化大革命直到今天”⑦。“真实主义”本是19世纪末意大利的一个受左拉自然主义影响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流派,通过对社会底层人物的描写进而展开对人性和社会的反思,属于“现实主义”的一个分支。书评作者Jean-Claude Perrier没有使用在法语中更常用的“现实主义”(réaliste)而选择了“真实主义”一词,显然是有意为之:他试图在此突出《兄弟》“真实主义”式的底层视角和批判态度。从中我们也可以读出他对《兄弟》的判断:在李光头、宋刚、林红、童铁匠、余拔牙等等底层小人物身上上演的所有那些时而粗俗时而淫秽时而疯狂时而英勇时而温情的光怪陆离的故事中,包含着余华对于中国整个当代社会进程的思虑和批评。换句话说,Perrier无疑不认为余华的这种“粗鄙修辞”将导致作家批评意识的消解或者说作家与社会现状的妥协,李光头的“成功”与宋刚的“失败”这一让人看似无法接受的结局恰恰是对中国社会一次“真实主义”的解剖。这个判断也成为了日后法国各大报刊所登载书评的一致基调。 不过相比于“真实主义”,更多的报刊选择了“流浪汉小说”(Roman picaresque)一词。比如《国际信使报》在对《兄弟》的授奖词中就说到:“从血腥的文化大革命到野蛮的资本主义,中国四十年的混乱在余华粗犷的笔锋下鱼贯而过。一本伟大的流浪汉小说。”⑧另一篇书评则说,“从文化大革命的残酷与荒诞到红色资本主义的粗暴转型:余华冲刷着近在咫尺的历史,并通过一段段粗犷而疯癫的插曲,使那些后果始终可见的事件一一复活。长河般的叙述,出色的操控,融流浪汉小说、历史传奇与癫狂的诙谐文学为一体”。⑨除此之外,比利时的《自由比利时报》、瑞士的《时间报》等等也纷纷采用了“流浪汉小说”的提法。“流浪汉小说”本是16世纪西班牙流行的一种特殊的文学体裁,西班牙语叫做“La novela picaresca”。“picaresca”一词的词源“pícaro”的意思是“无赖”、“恶棍”,而这种小说的内容也正是通过社会底层的“无赖”、“恶棍”(而且常常是少年)的眼光去观看社会下层的生活,小说的主人公们通常没有明确的道德意识,他们在围困着他们的腐败社会中随遇而安,为了生存下去不择手段地阿谀、钻营、撒谎、诈骗,最终成长为社会的同类,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获得“成功”——一种以放弃道德为代价的成功。此类小说也正是通过描写这些“无赖”与“恶棍”们的堕落生活,折射整个社会的粗野、淫秽和虚伪,从而形成一种揭露。在中国最有名的一部西班牙流浪汉小说便是杨绛翻译的《小癞子》,描写一个离家出走的流浪少年如何在不断更换主人的过程中历经炎凉世态,并最终成为了一个老练的骗子混迹于世,成家立业。在这类小说中,我们能够发现与《兄弟》精神气质上的暗合。虽然李光头并不像“流浪汉小说”惯用的主人公那样在世界上来回游荡,但他在生活中的投机与冒险可谓毫无间断。也正是因为这种“流浪汉小说”文学传统的存在,当欧洲大陆的批评家拿起《兄弟》,看到李光头这个“混世魔王”如何坑蒙拐骗,既被权力倾轧又倾轧权力,最终一步步成为亿万富翁的故事时,他们在小说范式的层面上便毫无接受困难并且自然地认可了其中的叙事方式。在《兄弟》与“流浪汉小说”之间确实存在着可资比较的巨大空间。⑩“流浪汉小说”与“真实主义”小说在欧洲文学传统中的存在,使得余华在中国大陆备受争议的“粗鄙修辞”在法国没有引起任何问题,因为此类修辞在这几类小说中几乎无处不在,“粗鄙”本身并不会引起法国人的惊叹或愤慨,他们也因此更容易穿透表层的粗鄙进入叙事核心。对法国批评家与读者而言这种写作方式的合法性也不言自明,他们从自身已有的文学传统出发,自然地认定这种对现实毫不掩饰的描写本身绝不代表任何作家本人的道德混乱或沦丧,而恰恰意味着一种良心,行文中所有粗俗、荒诞、残酷的写法本身就能够成为对社会现状的反思和批评,因为它恰恰意味着一个作家对现实生活的毫不掩饰与毫不妥协,他要打破一切道德或传统的禁忌把那些正在阴暗角落中发生的事书写下来,大白于世。《自由报》登载了法国记者与余华的一次访谈,其中记录了这样一则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