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图书馆机构用户,欢迎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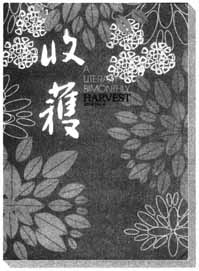
 城市与乡村之间的错位始终都是这个时代难以消化的命题。城市的扩张,城乡之间的人员流动,特别是经由学校完成的面向城市的年轻人的转移,使城乡之间产生了新的书写可能。对于一批进入城市的年轻人来说,能否融入其中,能否找到自己在城市存在的理由和证据,如同一声声尖锐的、伴着刺痛的提问,是一个时代的话题,更是一个群体的日常生活。 甫跃辉的《秋天的声音》和他之前的《走失在秋天的夜晚》放在一起,故事才变得完整起来。两篇小说像齿轮一样镶嵌在一起,互相带动着,把李绳的秋天和甫跃辉的青年们绞得粉碎。 初中毕业的李绳决定离开家乡,“大学都不包分配了,还不如趁早找份活干。”李绳的远走让曹英心里空得很,“不读书了?不读了。”两个做出同样选择的年轻人,却被城市和乡村生生地拉开。两篇小说分别呈现了走进城市的李绳和留在家乡的曹英各自的生活。打工仔李绳谎称自己是名校大学生,获取了一个城市女孩的心。但好景不长,李绳的谎言很快就被揭穿,面对自己试图由此融入城市的努力的惨败,他陷入了一种歇斯底里的疯狂和贯穿脊骨的凄凉。他一面给那个城市女孩发着诅咒的短信,一面发现自己在这座城市里没有一个可以一起喝酒、说一说失恋痛苦的人。不读书了的曹英很快在家门口开起一家杂货店,守着杂货店的她每天面对的就是一包盐、一瓶醋,直到屠元犀出现在她面前。开始的时候,曹英还在心里不停地张望,张望着李绳所在的大城市,但没过多久,她便投入了屠元犀的怀抱。然而,曹英很快就发现屠元犀还跟其他的女人搅在一起:“骗子!都是骗子!”当两个人同时陷入生活崩坏的时候,他们如何再次发现存在的证据?甫跃辉用一架红色的电话机又将两个被强行分离的人连在了一起,一边是长时间的沉默,一边是由谩骂到好奇到依赖到毫无保留的诉说。小说最后的凶案其实并不重要,它只是一个悲剧的象征,而将两篇小说紧紧扣在一起并互相证明的关键在于长时间不平衡的对话。虽然我们不能说它是一个刻意的隐喻,但这不平衡却在无意中形成了两种场域对话的艰难。 甫跃辉的写作常常游走于城市和乡村之间,《走失在秋天的夜晚》《巨象》《晚宴》《动物园》《秋天的声音》等都在讲述青年在城市面前的惨败。它有时是生于城市的某个女孩,有时是藏在城市某个角落的一间房屋的所有权,有时是“毕业时你能有二十万吗”的质问,归根结底是无法在城市找到归属感和存在感的灵魂挫伤。在小说将人们引向同情和忧虑的时候,房产、二十万、意味着城市的种种,这到底是谁在提问?城市不会提问,它只是一个冰冷的存在。或者,是哪个姑娘?其实一切都来自李绳、李生、顾零洲们的自问自答。他们是城市的闯入者,是乡村的背叛者,同时又是一群看上去最无辜的受害者。在他们身上,我们找不到安分守己,又找不到抵抗与侵犯的力量,他们既贪婪又可怜,与其说城乡之间的距离制造了他们的悲剧,不如说他们的失败让城乡之间的对立愈显激烈。人们经常泛泛地谈论时代令人扭曲、时代出了问题,却忘了是谁制造了这个时代;一边忧虑着、同情着、甚至诅咒着,却又很快露出谄媚的笑容,拒绝问责。于是我们看到了比李绳、顾零洲的窘相更大的悲剧:这是一个悉心培养起来的陷阱,人们排着队跌入其中,却在里面奋力地把它越挖越深,越挖越大。在这里不禁想起网络上流传的某个段子:当别人炫耀他百万豪车的时候,你能不能跷起脚,瞧,这双鞋才二十块。这是一个并不简单的选择题,它事关如何抵抗诱惑,如何面对欲望,如何在一个时代建立起属于个体的尊严。 在这里,时代与作家的矛盾变得越来越尖锐起来,时代、作家、小说三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异常纠结的三角关系。一个作家应该如何面对时代,是置身其中还是超越其外;是身陷其中呈现并默默接受一切规则,还是努力突围,留下一个挑战者悲壮的身影?而在作家和小说之间,是同情还是批判,是仅仅止于人物的贪婪与可悲,止于一摊双手的无可奈何,还是向前一步,在一个扮演着吞噬者的时代里,剖出可怜人被蛀空的心。这一切都将是青年写作者们需要面对的问题。甫跃辉的城乡系列不但精准地抓住了一个时代的难题,抓住了一批年轻人生存和心理的困境,而且塑造出顾零洲等一系列在当下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在当今青年作家中实属难能可贵。他以同代人的声音讲述着同代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而问题在于如何从这种对时代的敏锐和对生活的忠诚下,在趋于“伟大”的道路上,推进一公里,再推进一公里。 在前辈作家那里,时代更倾向于被阐释为国家、民族、政治、历史,大视野与大叙述几乎成为一种专属的方式和习惯。而在青年作家们眼中,时代更具体,更平易近人,它更多地被看成日常生活,或者说,被削减为日常生活。然而,日常生活相比对国家、民族的讲述并不逊色,何况任何一种脱离了常识、脱离了生活细节的宏大叙事非但是虚无的,还极易成为某些特别企图的寄居处。当然,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日常生活将被怎样讲述。
城市与乡村之间的错位始终都是这个时代难以消化的命题。城市的扩张,城乡之间的人员流动,特别是经由学校完成的面向城市的年轻人的转移,使城乡之间产生了新的书写可能。对于一批进入城市的年轻人来说,能否融入其中,能否找到自己在城市存在的理由和证据,如同一声声尖锐的、伴着刺痛的提问,是一个时代的话题,更是一个群体的日常生活。 甫跃辉的《秋天的声音》和他之前的《走失在秋天的夜晚》放在一起,故事才变得完整起来。两篇小说像齿轮一样镶嵌在一起,互相带动着,把李绳的秋天和甫跃辉的青年们绞得粉碎。 初中毕业的李绳决定离开家乡,“大学都不包分配了,还不如趁早找份活干。”李绳的远走让曹英心里空得很,“不读书了?不读了。”两个做出同样选择的年轻人,却被城市和乡村生生地拉开。两篇小说分别呈现了走进城市的李绳和留在家乡的曹英各自的生活。打工仔李绳谎称自己是名校大学生,获取了一个城市女孩的心。但好景不长,李绳的谎言很快就被揭穿,面对自己试图由此融入城市的努力的惨败,他陷入了一种歇斯底里的疯狂和贯穿脊骨的凄凉。他一面给那个城市女孩发着诅咒的短信,一面发现自己在这座城市里没有一个可以一起喝酒、说一说失恋痛苦的人。不读书了的曹英很快在家门口开起一家杂货店,守着杂货店的她每天面对的就是一包盐、一瓶醋,直到屠元犀出现在她面前。开始的时候,曹英还在心里不停地张望,张望着李绳所在的大城市,但没过多久,她便投入了屠元犀的怀抱。然而,曹英很快就发现屠元犀还跟其他的女人搅在一起:“骗子!都是骗子!”当两个人同时陷入生活崩坏的时候,他们如何再次发现存在的证据?甫跃辉用一架红色的电话机又将两个被强行分离的人连在了一起,一边是长时间的沉默,一边是由谩骂到好奇到依赖到毫无保留的诉说。小说最后的凶案其实并不重要,它只是一个悲剧的象征,而将两篇小说紧紧扣在一起并互相证明的关键在于长时间不平衡的对话。虽然我们不能说它是一个刻意的隐喻,但这不平衡却在无意中形成了两种场域对话的艰难。 甫跃辉的写作常常游走于城市和乡村之间,《走失在秋天的夜晚》《巨象》《晚宴》《动物园》《秋天的声音》等都在讲述青年在城市面前的惨败。它有时是生于城市的某个女孩,有时是藏在城市某个角落的一间房屋的所有权,有时是“毕业时你能有二十万吗”的质问,归根结底是无法在城市找到归属感和存在感的灵魂挫伤。在小说将人们引向同情和忧虑的时候,房产、二十万、意味着城市的种种,这到底是谁在提问?城市不会提问,它只是一个冰冷的存在。或者,是哪个姑娘?其实一切都来自李绳、李生、顾零洲们的自问自答。他们是城市的闯入者,是乡村的背叛者,同时又是一群看上去最无辜的受害者。在他们身上,我们找不到安分守己,又找不到抵抗与侵犯的力量,他们既贪婪又可怜,与其说城乡之间的距离制造了他们的悲剧,不如说他们的失败让城乡之间的对立愈显激烈。人们经常泛泛地谈论时代令人扭曲、时代出了问题,却忘了是谁制造了这个时代;一边忧虑着、同情着、甚至诅咒着,却又很快露出谄媚的笑容,拒绝问责。于是我们看到了比李绳、顾零洲的窘相更大的悲剧:这是一个悉心培养起来的陷阱,人们排着队跌入其中,却在里面奋力地把它越挖越深,越挖越大。在这里不禁想起网络上流传的某个段子:当别人炫耀他百万豪车的时候,你能不能跷起脚,瞧,这双鞋才二十块。这是一个并不简单的选择题,它事关如何抵抗诱惑,如何面对欲望,如何在一个时代建立起属于个体的尊严。 在这里,时代与作家的矛盾变得越来越尖锐起来,时代、作家、小说三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异常纠结的三角关系。一个作家应该如何面对时代,是置身其中还是超越其外;是身陷其中呈现并默默接受一切规则,还是努力突围,留下一个挑战者悲壮的身影?而在作家和小说之间,是同情还是批判,是仅仅止于人物的贪婪与可悲,止于一摊双手的无可奈何,还是向前一步,在一个扮演着吞噬者的时代里,剖出可怜人被蛀空的心。这一切都将是青年写作者们需要面对的问题。甫跃辉的城乡系列不但精准地抓住了一个时代的难题,抓住了一批年轻人生存和心理的困境,而且塑造出顾零洲等一系列在当下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在当今青年作家中实属难能可贵。他以同代人的声音讲述着同代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而问题在于如何从这种对时代的敏锐和对生活的忠诚下,在趋于“伟大”的道路上,推进一公里,再推进一公里。 在前辈作家那里,时代更倾向于被阐释为国家、民族、政治、历史,大视野与大叙述几乎成为一种专属的方式和习惯。而在青年作家们眼中,时代更具体,更平易近人,它更多地被看成日常生活,或者说,被削减为日常生活。然而,日常生活相比对国家、民族的讲述并不逊色,何况任何一种脱离了常识、脱离了生活细节的宏大叙事非但是虚无的,还极易成为某些特别企图的寄居处。当然,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日常生活将被怎样讲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