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图书馆机构用户,欢迎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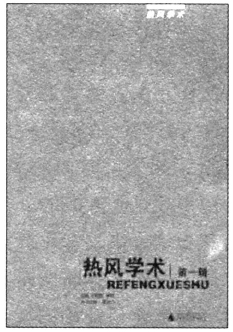 反对的杂语 在新时期漂洋过海来到中国的各种西方理论或者思潮中,文化研究可谓姗姗来迟;直到大众文化已然大行其道地在中国发挥着意识形态书写功能的20世纪90年代,人文学者们才发现唯一在欧美已经成为显学而国内尚无系统介绍的文化研究,认识到无论对于学院知识生产,还是对于谋取话语权的学术政治,它都非常重要。也就是说,文化研究在1995年前后的被引进,不仅关乎我们旨在从学理上对新时期的新现象、新问题做出解释、分析和批判,或许更重要的是,联系着已然遭遇边缘化的人文学者的这样一种希冀:借助文化研究形塑一种“别样”未来,夺回自己的中国文化启蒙者或者建构者地位。所以,被引进的文化研究旋即获得了大批拥趸,不期然间引发了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文化研究通过对“日常生活”的强调,有效地拓展了文学批评家、理论家的研究视野,尤其是在文艺学和当代文学领域;之前被忽视甚至边缘化的东西渐次登上了文学研究、文学批评的殿堂,改变了文学研究、文学理论的既有格局。借用华勒斯坦的话来讲,对文学研究者而言,“文化研究使对于当前的社会和政治舞台的关注具有了合法性”。③文化研究因此获得了准学科地位,但同时遭到了“大而不当”的诟病:“不少文学理论研究者投身文化研究,关注大众文化,研究影视、音乐、广告、传媒以及时装、波鞋之类日常生活文化现象……这种越界出走,作为个体的选择,难以厚非;但若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显然已是谋求文化霸权的病态或变态发作。”④对此,著名文学理论家童庆炳教授不无忧虑地指出:“文化研究并不总是以文学为研究对象,甚至完全不以文学为研究对象。可以(说)在更多的情况下,文化研究或者文化批评往往是一种社会学的、政治学的批评,其对象与文学无关,纯粹在那里讲阶级斗争、性别冲突和种族矛盾。”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前文提到的“文化研究的可能性”研讨会收获了不少质疑和反对之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包括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薛毅所言——“从外围来做的研究更有意思。如果是我的孩子,我更愿意把他送到文学系里面,而不是专门学文化研究”,以及复旦大学教授吕新雨所言——“文学不能放,文学中,我们已经放掉了很多”。⑥ 纵观文化研究的历史,批评或反对之声的出现与存在可谓不足为奇,或许是因为误读,或许是为了抢夺资源;在中国尤其如此。在一些中国学者看来,“虽然它(文化研究)与人们曾经耳熟能详或纯熟操练过的文学的社会历史批评(研究)或曰意识形态批评(研究)在功能上没有太大差异,却免不了如同高档球鞋因为有了一个‘波鞋’的洋名儿而身价倍增那样,令人感觉迥异,爱恨莫名。……这一思潮已迫不及待地在文学理论界流行了起来,时尚的荣辱风险,不免如影随形。”⑦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是一篇题为“走出‘文化研究’的困境”的文章。一如其标题所暗示的,文章旨在为中国文化研究的困境——文化理论研究与文化批评实践的脱节——把脉献策,因此颇具眼缘,但令人遗憾的是,文章作者显然是在以非学理的口吻谈论文化研究,一如这样的观念所暗示的:“因为现在看来,文化研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理论深度。”“其实,伯明翰学派的立论和方法不就那么几个点吗?”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文章作者在论及“带有距离感的审视”时,不但没有“带有距离感”地审视“著名的西方学者”特里·伊格尔顿,而且有意识地将其所使用的“culturalism”一词译为“文化至上论”,拒绝采用已然约定俗成的汉译“文化主义”。⑨这恐怕很难说仅仅是翻译表达的问题;我们不妨借用文章作者所使用的“揣摩”一词,“揣摩”其所指:“不能保持一定的距离对外来学术动向加以审视、客观公允地做出评价,恐怕是最重要的原因。”⑩即是说,文化研究所遭遇到的批评很可能关乎批评者在对文化研究及其播散缺乏基本认知的情况下,仅仅基于自己的“揣摩”对文化研究进行抨击,一如文章作者在谈到霍尔主编的《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时所坦陈的:“恕我孤陋寡闻,迄今为止我只看到国内有两三份硕士论文对此著给予了关注。”(11)事实上,早在商务印书馆推出《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中译本的2003年,该书便已成为多所高校文艺学、媒体研究等专业研究生的案头必备读物,所以,我们难以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迄今为止我只看到国内有两三份硕士论文对此著给予了关注”这一认知;“孤陋寡闻”可能是无害的。但基于“孤陋寡闻”的“揣摩”则必定有害。
反对的杂语 在新时期漂洋过海来到中国的各种西方理论或者思潮中,文化研究可谓姗姗来迟;直到大众文化已然大行其道地在中国发挥着意识形态书写功能的20世纪90年代,人文学者们才发现唯一在欧美已经成为显学而国内尚无系统介绍的文化研究,认识到无论对于学院知识生产,还是对于谋取话语权的学术政治,它都非常重要。也就是说,文化研究在1995年前后的被引进,不仅关乎我们旨在从学理上对新时期的新现象、新问题做出解释、分析和批判,或许更重要的是,联系着已然遭遇边缘化的人文学者的这样一种希冀:借助文化研究形塑一种“别样”未来,夺回自己的中国文化启蒙者或者建构者地位。所以,被引进的文化研究旋即获得了大批拥趸,不期然间引发了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文化研究通过对“日常生活”的强调,有效地拓展了文学批评家、理论家的研究视野,尤其是在文艺学和当代文学领域;之前被忽视甚至边缘化的东西渐次登上了文学研究、文学批评的殿堂,改变了文学研究、文学理论的既有格局。借用华勒斯坦的话来讲,对文学研究者而言,“文化研究使对于当前的社会和政治舞台的关注具有了合法性”。③文化研究因此获得了准学科地位,但同时遭到了“大而不当”的诟病:“不少文学理论研究者投身文化研究,关注大众文化,研究影视、音乐、广告、传媒以及时装、波鞋之类日常生活文化现象……这种越界出走,作为个体的选择,难以厚非;但若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显然已是谋求文化霸权的病态或变态发作。”④对此,著名文学理论家童庆炳教授不无忧虑地指出:“文化研究并不总是以文学为研究对象,甚至完全不以文学为研究对象。可以(说)在更多的情况下,文化研究或者文化批评往往是一种社会学的、政治学的批评,其对象与文学无关,纯粹在那里讲阶级斗争、性别冲突和种族矛盾。”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前文提到的“文化研究的可能性”研讨会收获了不少质疑和反对之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包括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薛毅所言——“从外围来做的研究更有意思。如果是我的孩子,我更愿意把他送到文学系里面,而不是专门学文化研究”,以及复旦大学教授吕新雨所言——“文学不能放,文学中,我们已经放掉了很多”。⑥ 纵观文化研究的历史,批评或反对之声的出现与存在可谓不足为奇,或许是因为误读,或许是为了抢夺资源;在中国尤其如此。在一些中国学者看来,“虽然它(文化研究)与人们曾经耳熟能详或纯熟操练过的文学的社会历史批评(研究)或曰意识形态批评(研究)在功能上没有太大差异,却免不了如同高档球鞋因为有了一个‘波鞋’的洋名儿而身价倍增那样,令人感觉迥异,爱恨莫名。……这一思潮已迫不及待地在文学理论界流行了起来,时尚的荣辱风险,不免如影随形。”⑦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是一篇题为“走出‘文化研究’的困境”的文章。一如其标题所暗示的,文章旨在为中国文化研究的困境——文化理论研究与文化批评实践的脱节——把脉献策,因此颇具眼缘,但令人遗憾的是,文章作者显然是在以非学理的口吻谈论文化研究,一如这样的观念所暗示的:“因为现在看来,文化研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理论深度。”“其实,伯明翰学派的立论和方法不就那么几个点吗?”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文章作者在论及“带有距离感的审视”时,不但没有“带有距离感”地审视“著名的西方学者”特里·伊格尔顿,而且有意识地将其所使用的“culturalism”一词译为“文化至上论”,拒绝采用已然约定俗成的汉译“文化主义”。⑨这恐怕很难说仅仅是翻译表达的问题;我们不妨借用文章作者所使用的“揣摩”一词,“揣摩”其所指:“不能保持一定的距离对外来学术动向加以审视、客观公允地做出评价,恐怕是最重要的原因。”⑩即是说,文化研究所遭遇到的批评很可能关乎批评者在对文化研究及其播散缺乏基本认知的情况下,仅仅基于自己的“揣摩”对文化研究进行抨击,一如文章作者在谈到霍尔主编的《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时所坦陈的:“恕我孤陋寡闻,迄今为止我只看到国内有两三份硕士论文对此著给予了关注。”(11)事实上,早在商务印书馆推出《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中译本的2003年,该书便已成为多所高校文艺学、媒体研究等专业研究生的案头必备读物,所以,我们难以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迄今为止我只看到国内有两三份硕士论文对此著给予了关注”这一认知;“孤陋寡闻”可能是无害的。但基于“孤陋寡闻”的“揣摩”则必定有害。  相较于“不甚了了者”,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在文化研究及其学科化的疑虑者、反对者中,很多都深知文化研究的功用甚至是文化研究的受益者;他们未必以文化研究为自己的研究命名,但他们的研究中却不乏文化研究的影子。他们批评、反对文化研究及其学科化实际上关乎学科政治和学科资源的争夺。众所周知,当下的学术知识生产已然深刻联系着各种社会权利、利益机制,“一方面框限着知识朝向专业化和日益相分割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也可以促使接受这些学科训练的人,日益以学科内部的严格训练为借口,树立必要的界限,以谋求巩固学科的专业地位”。(12)学科划分的结果是学科制度在“建立完整而融贯的理论传统和严格的方法训练”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导致各学科因为受支配于权力和利益,成为“偏见的生产地,以服务于自己的利益为尚,建立虚假的权威之虞”。(13)所以,当文化研究作为学术界最有活力,最富于创造性的学术思潮闯入中国学界的时候,难免会遭遇文艺学等相邻学科的非难,虽然同时存在的一个事实是,在致力于文化研究的学者中,主要来自文艺学。
相较于“不甚了了者”,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在文化研究及其学科化的疑虑者、反对者中,很多都深知文化研究的功用甚至是文化研究的受益者;他们未必以文化研究为自己的研究命名,但他们的研究中却不乏文化研究的影子。他们批评、反对文化研究及其学科化实际上关乎学科政治和学科资源的争夺。众所周知,当下的学术知识生产已然深刻联系着各种社会权利、利益机制,“一方面框限着知识朝向专业化和日益相分割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也可以促使接受这些学科训练的人,日益以学科内部的严格训练为借口,树立必要的界限,以谋求巩固学科的专业地位”。(12)学科划分的结果是学科制度在“建立完整而融贯的理论传统和严格的方法训练”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导致各学科因为受支配于权力和利益,成为“偏见的生产地,以服务于自己的利益为尚,建立虚假的权威之虞”。(13)所以,当文化研究作为学术界最有活力,最富于创造性的学术思潮闯入中国学界的时候,难免会遭遇文艺学等相邻学科的非难,虽然同时存在的一个事实是,在致力于文化研究的学者中,主要来自文艺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