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图书馆机构用户,欢迎您!
布达佩斯学派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流派之一。20世纪晚期,作为卢卡奇的得意门生和学术伙伴,布达佩斯学派的主要成员在研究主题上经历了一次微观的文化转向。他们从早期对异化、人道主义等青年马克思思想的倚重转变到后期对文化、后现代、科学与艺术等主题的研究,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角关注和分析当代现实问题,形成了体现该学派传统的现代性文化理论。通过简要评述布达佩斯学派现代性文化理论的主要内容,可以揭示该学派为现代性文化寻求多元化发展道路的理论共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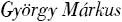 )和米哈里·瓦伊达(Mihaly Vajda)开始将研究的主题转向现代性问题。布达佩斯学派把现代性理解为一种渗透到经济、政治、日常生活等众多社会领域中的深层的文化模式。其核心包含着理性单一化、同质化、总体化和普遍化的思维方式。在布达佩斯学派看来,正是理性这种单一化的发展导致了现代性的危机。这种现代性危机呈现出多种表现方式,例如文化多样性的丧失,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对民主、自由和平等的破坏,道德虚无主义以及对人的需要的专政,等等。由此,布达佩斯学派从文化理论、政治学、伦理学等多个角度对现代性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阐释。其中,马尔库什和赫勒、费赫尔夫妇围绕着现代性文化问题展开了一系列深入的研究。本文试图对布达佩斯学派现代性文化理论的主要内涵进行评述,揭示该学派为现代性文化寻求多元化发展道路的理论共识,并最终对布达佩斯学派现代性文化理论进行简要评析。 一、对文化概念的界定 文化具有极为丰富的内涵,正如许多学者从各自的角度对文化的意义进行了划分一样,布达佩斯学派也对文化的概念进行了界定。马尔库什划分了两种文化概念:广义的、人类学的(anthropological)文化概念与狭义的、价值标示的(value-marked)文化概念。赫勒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第三种文化概念:文化话语。 第一种文化概念具有一种广义的、人类学的意义。布达佩斯学派将这种文化概念理解为一种社会共同体的标志或表意系统。马尔库什认为,这种文化概念的内涵可以从人类学理论的角度得到清晰的阐释。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指的是非生物学固定的人类行为方式,它是一个共同体长久积累下来的,被共同体成员所共享的一种形式。它所规定和影响的生活、行为和思想方式可以与另一个社会或共同体相区别,并且共同体的成员可以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差异的存在。这种文化概念的意义,在人类学的历史上经历了不少特征上的变化,演化到今天,人类学的文化已经成为一个社会的表意系统,是“人类实践的意义承载和意义传递的元素”[1]。因此,“在人类学概念的意义上,所有的人类社会都是文化,因为它们向它们的居民提供规范、法则、叙事、形象、宗教等等”[2]188。在这种文化的表意系统之内,作为个体的成员可以相互了解,用彼此理解的行为方式生活在这个共同体社会中。总的说来,人类学的文化概念是一个社会单位独特的、区别于其他社会单位的一种标志性的体系。 第二种文化概念指的是狭义的、价值标示的、体现一种自律性价值的文化。赫勒把这种文化直接称为高雅文化。在布达佩斯学派看来,这种文化特指一系列特定的人类行为与社会活动,在现代性条件下,这些活动通常被视为是自律的,其本身具有自己的发展模式、评价标准等等,并且独立于政治与经济领域。马尔库什指出,这样的文化主要指的是艺术、科学、哲学、文学等等我们所熟悉的文化实践活动。赫勒指出,这种文化“包括心灵、双手以及想象力的创造物,它们一起被黑格尔称为绝对精神:有代表性的艺术作品、神学、哲学以及——在19世纪——科学”[2]164。这种文化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成立的,前现代社会是不存在“高雅文化”概念的。因此,只有在现代性条件下,这样的文化活动本身才具有原生的、内在的规范和评价标准。因此,也就是所谓价值标示的文化概念。 第三种是赫勒在马尔库什的基础上提出的“文化话语”的文化概念。所谓“文化话语”主要赋予了文化以交流沟通的作用。通过话语交谈,人们不是要达成共识,而是在于在文化的背景下交换观点,呈现自己的意见。赫勒认为,作为话语方式的文化并不一定是哲学、文学、艺术等高雅文化,换句话说文化讨论是跨语境、跨文化的讨论。在赫勒看来,为了避免文化趋同、一体化,文化的话语方式具有积极的意义。它为参与交谈者提供了一种交谈伦理学,在交谈的语境下,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和价值,并且要在承认他人的观点和价值的基础上,交谈才有可能发生。这种伦理学既是现代性的产物、也为现代性提供了动力载体。 二、文化悖论:普遍性与差异性 对于文化的特征问题,布达佩斯学派一致认为,悖论性是文化对现代性最直接的反应和表现。由于启蒙现代性自诞生起就包含着两种悖论冲突的逻辑:肯定性的逻辑与否定性的逻辑。因此,现代性内部始终具有一种悖谬的、矛盾冲突的特征与张力。这种特征集中反映在现代性文化的悖论特征中。布达佩斯学派指出,文化悖论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普遍性与差异性的矛盾。然而,两者之间的张力正在逐渐被消解,现代性单一化、一元化的危机也正在威胁着文化的发展。 以广义的、人类学的文化为例,它本身既是一个普遍性的概念,也是一个差异性的概念。一方面,它指代的是人类共同体各自共享的、必然参与其中的一般属性和普遍化的领域;另一方面,它主要标志着时间和空间上区别不同社会的那些内容,也就是各自特征的复合体。这种特异性体现在区别于其他特殊的社会单位之中。正如赫勒所指出的那样,人类学文化概念的悖论是“通过经验——以及非规范性——普遍来运作的,悖论将会通过对立两极(普遍/差异)的主题化而出现。无需说,这一悖论就像所有其他的悖论一样,是现代性的基本悖论的表现形式”[2]190。
)和米哈里·瓦伊达(Mihaly Vajda)开始将研究的主题转向现代性问题。布达佩斯学派把现代性理解为一种渗透到经济、政治、日常生活等众多社会领域中的深层的文化模式。其核心包含着理性单一化、同质化、总体化和普遍化的思维方式。在布达佩斯学派看来,正是理性这种单一化的发展导致了现代性的危机。这种现代性危机呈现出多种表现方式,例如文化多样性的丧失,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对民主、自由和平等的破坏,道德虚无主义以及对人的需要的专政,等等。由此,布达佩斯学派从文化理论、政治学、伦理学等多个角度对现代性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阐释。其中,马尔库什和赫勒、费赫尔夫妇围绕着现代性文化问题展开了一系列深入的研究。本文试图对布达佩斯学派现代性文化理论的主要内涵进行评述,揭示该学派为现代性文化寻求多元化发展道路的理论共识,并最终对布达佩斯学派现代性文化理论进行简要评析。 一、对文化概念的界定 文化具有极为丰富的内涵,正如许多学者从各自的角度对文化的意义进行了划分一样,布达佩斯学派也对文化的概念进行了界定。马尔库什划分了两种文化概念:广义的、人类学的(anthropological)文化概念与狭义的、价值标示的(value-marked)文化概念。赫勒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第三种文化概念:文化话语。 第一种文化概念具有一种广义的、人类学的意义。布达佩斯学派将这种文化概念理解为一种社会共同体的标志或表意系统。马尔库什认为,这种文化概念的内涵可以从人类学理论的角度得到清晰的阐释。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指的是非生物学固定的人类行为方式,它是一个共同体长久积累下来的,被共同体成员所共享的一种形式。它所规定和影响的生活、行为和思想方式可以与另一个社会或共同体相区别,并且共同体的成员可以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差异的存在。这种文化概念的意义,在人类学的历史上经历了不少特征上的变化,演化到今天,人类学的文化已经成为一个社会的表意系统,是“人类实践的意义承载和意义传递的元素”[1]。因此,“在人类学概念的意义上,所有的人类社会都是文化,因为它们向它们的居民提供规范、法则、叙事、形象、宗教等等”[2]188。在这种文化的表意系统之内,作为个体的成员可以相互了解,用彼此理解的行为方式生活在这个共同体社会中。总的说来,人类学的文化概念是一个社会单位独特的、区别于其他社会单位的一种标志性的体系。 第二种文化概念指的是狭义的、价值标示的、体现一种自律性价值的文化。赫勒把这种文化直接称为高雅文化。在布达佩斯学派看来,这种文化特指一系列特定的人类行为与社会活动,在现代性条件下,这些活动通常被视为是自律的,其本身具有自己的发展模式、评价标准等等,并且独立于政治与经济领域。马尔库什指出,这样的文化主要指的是艺术、科学、哲学、文学等等我们所熟悉的文化实践活动。赫勒指出,这种文化“包括心灵、双手以及想象力的创造物,它们一起被黑格尔称为绝对精神:有代表性的艺术作品、神学、哲学以及——在19世纪——科学”[2]164。这种文化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成立的,前现代社会是不存在“高雅文化”概念的。因此,只有在现代性条件下,这样的文化活动本身才具有原生的、内在的规范和评价标准。因此,也就是所谓价值标示的文化概念。 第三种是赫勒在马尔库什的基础上提出的“文化话语”的文化概念。所谓“文化话语”主要赋予了文化以交流沟通的作用。通过话语交谈,人们不是要达成共识,而是在于在文化的背景下交换观点,呈现自己的意见。赫勒认为,作为话语方式的文化并不一定是哲学、文学、艺术等高雅文化,换句话说文化讨论是跨语境、跨文化的讨论。在赫勒看来,为了避免文化趋同、一体化,文化的话语方式具有积极的意义。它为参与交谈者提供了一种交谈伦理学,在交谈的语境下,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和价值,并且要在承认他人的观点和价值的基础上,交谈才有可能发生。这种伦理学既是现代性的产物、也为现代性提供了动力载体。 二、文化悖论:普遍性与差异性 对于文化的特征问题,布达佩斯学派一致认为,悖论性是文化对现代性最直接的反应和表现。由于启蒙现代性自诞生起就包含着两种悖论冲突的逻辑:肯定性的逻辑与否定性的逻辑。因此,现代性内部始终具有一种悖谬的、矛盾冲突的特征与张力。这种特征集中反映在现代性文化的悖论特征中。布达佩斯学派指出,文化悖论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普遍性与差异性的矛盾。然而,两者之间的张力正在逐渐被消解,现代性单一化、一元化的危机也正在威胁着文化的发展。 以广义的、人类学的文化为例,它本身既是一个普遍性的概念,也是一个差异性的概念。一方面,它指代的是人类共同体各自共享的、必然参与其中的一般属性和普遍化的领域;另一方面,它主要标志着时间和空间上区别不同社会的那些内容,也就是各自特征的复合体。这种特异性体现在区别于其他特殊的社会单位之中。正如赫勒所指出的那样,人类学文化概念的悖论是“通过经验——以及非规范性——普遍来运作的,悖论将会通过对立两极(普遍/差异)的主题化而出现。无需说,这一悖论就像所有其他的悖论一样,是现代性的基本悖论的表现形式”[2]1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