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图书馆机构用户,欢迎您!
二次大战后移入泰国的越南人,既是泰国的新移民,也是泰国众多的少数族群之一。他们首先要面对的是来自泰国社会(包括政治精英、普罗大众等)对其自身的认知,这将影响到政府欲采取的政策,亦将面对泰国越南人本身的认同意识变迁。泰国社会对越南移民的认知又经常受对其祖国(越南)的认识所影响。因此,研究泰国的越南移民的处境,必须将越南移民同时置放在泰国的少数族群政治及国际政治等两大层次来分析,包括泰国的国族主义、边境政治、冷战体制等,才能确实掌握越南移民处境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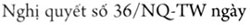 26/3/2004
26/3/20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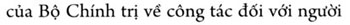
 )指出,海外越南人约有270万,其中80%居住在已开发国家,②超过一半居住在美国,其余依序为法国、中国、澳洲及加拿大;旅居泰国的越南人约有12万,约占总数的5%。③因此,学者对于海外越南人研究的对象选择,主要集中于旅居欧美的越南人,④对泰国越南人的相关研究,数量相对较少。⑤ 近年来,正如越南当局所指出:“多数的海外越南人已经定居且深入整合到居住国的当地社群中,通过其经济和政治地位,在越南与居住国的双边关系中,发挥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力。”⑥因此,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探讨泰国越南人的地位变化。本文认为,泰国越南人的地位变迁,主要受到三大要素的交互影响:一是泰国的国族建构(nation-building)的过程;二是东南亚区域地缘政治局势,特别是冷战体制;三是泰、越两国的双边关系。本文分三个主要部分:第一,本文的分析观点;第二,冷战时期泰国越南人的地位;第三,后冷战时期泰国越南人地位的转变。 本文的分析观点:国族共同体与有意义的他者 建构“共同体”的定义可通过两种方式:一是强调构成份子的共同性(sameness);另一则是强调差异性而予以排除借以达成同一性。同样的,国族(nation)作为一种虚拟的政治共同体,不论是想象或是被发明的,⑦其建构过程(nation-building)同样可分为两种方式。首先,通过“正面识别”(positive identification)的方式,⑧强调群体成员的共同性,比如共同的祖先与族裔起源、共享的历史疆域、共同神话、历史记忆、大众流行文化,以及共同的经济、共同的法律权利、成员责任等,形成一种“归属感”,⑨抑或“同伴情谊”(fellow feeling),⑩在个体与名为国族的集体间建立紧密连结,然后再反复灌输一种国族荣耀与忠诚于国族的国族意识。(11)其次,采取“否定的识别”(negative identification)的方式,(12)通过与“有意义的他者”(significant other)的参照,来强化内群体(ingroup)的认同意识,这是一种可以由内与由外来定义的双重关系。 从内部来定义者,是通过所谓的“内部他者”(other within)来达成,其意指和内群体归属于共同政治实体,而且对内群体的文化、领土等共同性造成破坏的那群人,像是国族国家中的少数族裔(ethnic minority)、移民社群(immigrant community)等。在一个多国族政治实体(multinational political unit)中,“内部他者”有可能是多数族裔或是小的国族。(13) 从外部来定义者,则是通过“外部他者”(external other)来达成。所谓“外部他者”,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与国族形成的初期阶段有关,例如从支配的国族或多国族国家的族群中,寻求解放或区别自身的那些人。第二类是和敌对国族或国族国家有关,亦即内群体的邻国,其欲争夺内群体祖国的某些部分,或正控制内群体宣称固有疆域的某些土地,这类型的“外部他者”可能会导致领土边界的重新定义,或者突显出内群体的领土复国主义倾向,并强调内群体的特定族裔或文化概念来支持这种倾向。第三类,领土与内群体紧邻但不争夺领土边界,反而主张拥有构成国族过去的特定神话、象征或祖先等文化遗产之权利的国族、国族国家或族群,其对内群体的独特性与共同性造成重大威胁,从而使内群体为主张那些争夺中的象征或神话是自身的文化资产,而必须重新定义自身的认同。(14) 简单地说,“内部他者”主要是从内部侵蚀国族的同一性,“外部他者”则是从外部挑战国族的领土或文化完整。当国族国家面临社会、政治或经济危机,使得国族认同被当作问题加以提出时,“有意义的他者”将变得更加突显。因为,为克服危机,必须通过共同的敌人来团结人民;此外,“有意义的他者”也会不断提醒人民“我们是谁”,并强调“我们是不同与独特的”。在国族认同的架构中,“有意义的他者”有助于厘清内群体的边界,以及强化成员的归属感;相对地,当国族国家面临经济、政治与社会危机时,“有意义的他者”会从危机的真正原因中发挥一种分散注意力的功用。(15)因此,在危机时期,统治者大多采取措施激发国族成员对境内的特定族群或是具有冲突的邻国不同族裔的负面意识,使得“有意义他者”经常变成一种代罪羔羊。特别是,当“内部的他者”来自“外部他者”时,这种情形更为显著。普遍而言,开发中国家较常采取负面的方式,理由是要通过寻求共同敌人来达成国族团结。(16) 美国社会学者布鲁巴克(Rogers Brubaker)曾发表《新欧洲的国内少数民族、国族化国家以及外部祖国》(National Minorties,Nationalizing States,and External National Homelands in the New Europe),提出国族化国家(nationalizing state)、国内少数民族(national minority)及外部祖国(external national homeland)的三角关系(triadic nexus),借此分析东欧诸国复杂难解的民族问题及其动态关系。他指出,欧洲的新兴国族国家,由于文化边界与政治边界的差异,导致众多人民居住在其国族疆域之外;虽然他们的公民身份是归属于所居住的新兴国族国家,但是,在族裔国族性(ethnic nationality)上,则是归属于外部祖国。(17)一旦外部祖国被国族化国家视为主要的威胁时。统治当局经常会将少数民族视为威胁国家内部稳定及国家安全的要素,而少数民族群混居的地带,很容易被当作国家之间进行代理人战争的战场,造成一国的少数族群政治经常深受边界政治的影响。在此关系架构中,国内少数民族以及外部祖国,经常被国族化国家视为“有意义的他者”。尽管如此,这三要素都不应该被视为是一种给定的(given)、不可化约的实体,而是要被视为一种有差异性及竞争性的场域,是竞争各方间进行斗争的竞技场;所构成的三角关系,既是内部的,也是构成性的,形成一种相互作用的动态关系。(18)
)指出,海外越南人约有270万,其中80%居住在已开发国家,②超过一半居住在美国,其余依序为法国、中国、澳洲及加拿大;旅居泰国的越南人约有12万,约占总数的5%。③因此,学者对于海外越南人研究的对象选择,主要集中于旅居欧美的越南人,④对泰国越南人的相关研究,数量相对较少。⑤ 近年来,正如越南当局所指出:“多数的海外越南人已经定居且深入整合到居住国的当地社群中,通过其经济和政治地位,在越南与居住国的双边关系中,发挥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力。”⑥因此,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探讨泰国越南人的地位变化。本文认为,泰国越南人的地位变迁,主要受到三大要素的交互影响:一是泰国的国族建构(nation-building)的过程;二是东南亚区域地缘政治局势,特别是冷战体制;三是泰、越两国的双边关系。本文分三个主要部分:第一,本文的分析观点;第二,冷战时期泰国越南人的地位;第三,后冷战时期泰国越南人地位的转变。 本文的分析观点:国族共同体与有意义的他者 建构“共同体”的定义可通过两种方式:一是强调构成份子的共同性(sameness);另一则是强调差异性而予以排除借以达成同一性。同样的,国族(nation)作为一种虚拟的政治共同体,不论是想象或是被发明的,⑦其建构过程(nation-building)同样可分为两种方式。首先,通过“正面识别”(positive identification)的方式,⑧强调群体成员的共同性,比如共同的祖先与族裔起源、共享的历史疆域、共同神话、历史记忆、大众流行文化,以及共同的经济、共同的法律权利、成员责任等,形成一种“归属感”,⑨抑或“同伴情谊”(fellow feeling),⑩在个体与名为国族的集体间建立紧密连结,然后再反复灌输一种国族荣耀与忠诚于国族的国族意识。(11)其次,采取“否定的识别”(negative identification)的方式,(12)通过与“有意义的他者”(significant other)的参照,来强化内群体(ingroup)的认同意识,这是一种可以由内与由外来定义的双重关系。 从内部来定义者,是通过所谓的“内部他者”(other within)来达成,其意指和内群体归属于共同政治实体,而且对内群体的文化、领土等共同性造成破坏的那群人,像是国族国家中的少数族裔(ethnic minority)、移民社群(immigrant community)等。在一个多国族政治实体(multinational political unit)中,“内部他者”有可能是多数族裔或是小的国族。(13) 从外部来定义者,则是通过“外部他者”(external other)来达成。所谓“外部他者”,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与国族形成的初期阶段有关,例如从支配的国族或多国族国家的族群中,寻求解放或区别自身的那些人。第二类是和敌对国族或国族国家有关,亦即内群体的邻国,其欲争夺内群体祖国的某些部分,或正控制内群体宣称固有疆域的某些土地,这类型的“外部他者”可能会导致领土边界的重新定义,或者突显出内群体的领土复国主义倾向,并强调内群体的特定族裔或文化概念来支持这种倾向。第三类,领土与内群体紧邻但不争夺领土边界,反而主张拥有构成国族过去的特定神话、象征或祖先等文化遗产之权利的国族、国族国家或族群,其对内群体的独特性与共同性造成重大威胁,从而使内群体为主张那些争夺中的象征或神话是自身的文化资产,而必须重新定义自身的认同。(14) 简单地说,“内部他者”主要是从内部侵蚀国族的同一性,“外部他者”则是从外部挑战国族的领土或文化完整。当国族国家面临社会、政治或经济危机,使得国族认同被当作问题加以提出时,“有意义的他者”将变得更加突显。因为,为克服危机,必须通过共同的敌人来团结人民;此外,“有意义的他者”也会不断提醒人民“我们是谁”,并强调“我们是不同与独特的”。在国族认同的架构中,“有意义的他者”有助于厘清内群体的边界,以及强化成员的归属感;相对地,当国族国家面临经济、政治与社会危机时,“有意义的他者”会从危机的真正原因中发挥一种分散注意力的功用。(15)因此,在危机时期,统治者大多采取措施激发国族成员对境内的特定族群或是具有冲突的邻国不同族裔的负面意识,使得“有意义他者”经常变成一种代罪羔羊。特别是,当“内部的他者”来自“外部他者”时,这种情形更为显著。普遍而言,开发中国家较常采取负面的方式,理由是要通过寻求共同敌人来达成国族团结。(16) 美国社会学者布鲁巴克(Rogers Brubaker)曾发表《新欧洲的国内少数民族、国族化国家以及外部祖国》(National Minorties,Nationalizing States,and External National Homelands in the New Europe),提出国族化国家(nationalizing state)、国内少数民族(national minority)及外部祖国(external national homeland)的三角关系(triadic nexus),借此分析东欧诸国复杂难解的民族问题及其动态关系。他指出,欧洲的新兴国族国家,由于文化边界与政治边界的差异,导致众多人民居住在其国族疆域之外;虽然他们的公民身份是归属于所居住的新兴国族国家,但是,在族裔国族性(ethnic nationality)上,则是归属于外部祖国。(17)一旦外部祖国被国族化国家视为主要的威胁时。统治当局经常会将少数民族视为威胁国家内部稳定及国家安全的要素,而少数民族群混居的地带,很容易被当作国家之间进行代理人战争的战场,造成一国的少数族群政治经常深受边界政治的影响。在此关系架构中,国内少数民族以及外部祖国,经常被国族化国家视为“有意义的他者”。尽管如此,这三要素都不应该被视为是一种给定的(given)、不可化约的实体,而是要被视为一种有差异性及竞争性的场域,是竞争各方间进行斗争的竞技场;所构成的三角关系,既是内部的,也是构成性的,形成一种相互作用的动态关系。(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