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图书馆机构用户,欢迎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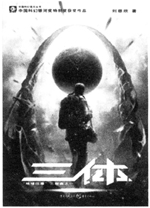 在距地球五万光年的远方,在银河系的中心,一场延续了两万年的星际战争已接近尾声。那里的太空中渐渐隐现出一个方形区域,仿佛灿烂的群星的背景被剪出一个方口,这个区域的边长约十万公里,区域的内部是一种比周围太空更黑的黑暗,让人感到一种虚空中的虚空。从这黑色的正方形中,开始浮现出一些实体,它们形状各异,都有月球大小,呈耀眼的银色。这些物体越来越多,并组成一个整齐的立方体方阵。这银色的方阵庄严地驶出黑色正方形,两者构成了一幅挂在宇宙永恒墙壁上的镶嵌画,这幅画以绝时黑体的正方形天鹅绒为衬底,由纯净的银光耀眼的白银小构件整齐地镶嵌而成。这又仿佛是一首宇宙交响乐的固化。渐渐地,黑色的正方形消溶在星空中,群星填补了它的位置,银色的方阵庄严地悬浮在群星之间。 这后面的转折绝对是大家难以想象的。这个乡村教师的最后一点徒劳而可悲的努力,最终拯救了人类。他那卑微的生命,融入了一个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极为壮阔的太空史诗。而这个教师的意义,也被发挥到了一个广袤的宇宙的尺度,一个在非科幻文学作品中难以企及的尺度。 我们一眼能够看到这其中的启蒙主题。事实上,无论是五四的启蒙运动,还是“文革”后的“新启蒙”,科学都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跨时代的两场启蒙,都遭遇了危机与挫折。对前者而言,是“救亡压倒启蒙”。对后者来说,事情更加复杂:市场经济、消费文化、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乃至西方知识界对启蒙的批判,都扮演了推手的角色。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作品中的启蒙主题,逐渐隐去。在这样的背景下,刘慈欣再回启蒙现场,意义非同寻常。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刘慈欣和那些消解启蒙的人一样,都是企图超越启蒙。不同的是,他的方向恰好相反,因为这不仅仅是老调重弹,更把启蒙的意义超拔到不可思议的高度。2007年中国国际科幻·奇幻大会期间,在女诗人翟永明开办的“白夜”酒吧,刘慈欣和著名科学史家江晓原教授之间有一场十分精彩的论辩。刘慈欣的旗帜很鲜明:“我是一个疯狂的技术主义者,我个人坚信技术能解决一切问题。”①在全世界敢这样直接亮出底牌的人不多,在中国就更少。刘慈欣举了一个例子:假设人类将面临巨大灾难,在这种情况下可否运用某种芯片技术来控制人的思想,从而更有效地组织起来,面对灾难。江晓原则认为脑袋中植入芯片,这本身就是一个灾难,因为这会摧毁人的自由意志,带来人性的泯灭。所以科学不是万能的,不是至高无上的,更不能解决所有的人类问题。
在距地球五万光年的远方,在银河系的中心,一场延续了两万年的星际战争已接近尾声。那里的太空中渐渐隐现出一个方形区域,仿佛灿烂的群星的背景被剪出一个方口,这个区域的边长约十万公里,区域的内部是一种比周围太空更黑的黑暗,让人感到一种虚空中的虚空。从这黑色的正方形中,开始浮现出一些实体,它们形状各异,都有月球大小,呈耀眼的银色。这些物体越来越多,并组成一个整齐的立方体方阵。这银色的方阵庄严地驶出黑色正方形,两者构成了一幅挂在宇宙永恒墙壁上的镶嵌画,这幅画以绝时黑体的正方形天鹅绒为衬底,由纯净的银光耀眼的白银小构件整齐地镶嵌而成。这又仿佛是一首宇宙交响乐的固化。渐渐地,黑色的正方形消溶在星空中,群星填补了它的位置,银色的方阵庄严地悬浮在群星之间。 这后面的转折绝对是大家难以想象的。这个乡村教师的最后一点徒劳而可悲的努力,最终拯救了人类。他那卑微的生命,融入了一个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极为壮阔的太空史诗。而这个教师的意义,也被发挥到了一个广袤的宇宙的尺度,一个在非科幻文学作品中难以企及的尺度。 我们一眼能够看到这其中的启蒙主题。事实上,无论是五四的启蒙运动,还是“文革”后的“新启蒙”,科学都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跨时代的两场启蒙,都遭遇了危机与挫折。对前者而言,是“救亡压倒启蒙”。对后者来说,事情更加复杂:市场经济、消费文化、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乃至西方知识界对启蒙的批判,都扮演了推手的角色。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作品中的启蒙主题,逐渐隐去。在这样的背景下,刘慈欣再回启蒙现场,意义非同寻常。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刘慈欣和那些消解启蒙的人一样,都是企图超越启蒙。不同的是,他的方向恰好相反,因为这不仅仅是老调重弹,更把启蒙的意义超拔到不可思议的高度。2007年中国国际科幻·奇幻大会期间,在女诗人翟永明开办的“白夜”酒吧,刘慈欣和著名科学史家江晓原教授之间有一场十分精彩的论辩。刘慈欣的旗帜很鲜明:“我是一个疯狂的技术主义者,我个人坚信技术能解决一切问题。”①在全世界敢这样直接亮出底牌的人不多,在中国就更少。刘慈欣举了一个例子:假设人类将面临巨大灾难,在这种情况下可否运用某种芯片技术来控制人的思想,从而更有效地组织起来,面对灾难。江晓原则认为脑袋中植入芯片,这本身就是一个灾难,因为这会摧毁人的自由意志,带来人性的泯灭。所以科学不是万能的,不是至高无上的,更不能解决所有的人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