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图书馆机构用户,欢迎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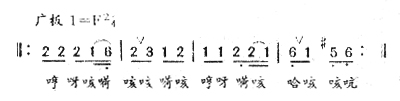 音乐的铿锵节奏同江北大汉的粗壮形象融为一体,并且赋予了这一形象一种动态美。 朦胧诗的这种朦胧显然是受到西方现代派诗歌的影响,其中尤其是受象征主义诗歌的影响。象征主义是19世纪70年代兴起于法国,是20世纪影响最大的西方现代派诗歌流派。象征主义对社会现实强烈不满,即反对自然主义机械地生物性地描摹现实,也不满意印象主义所认为的:感觉便是最高的真实。象征主义者排斥过去的教条、规范、甚至传统。他们认为,客观世界是虚妄的,是不可知的,只有主观世界才是真实的,客观万物不过是主观精神的种种暗示和象征。心灵才是最高的真实。而要表现心灵这一最高的真实,我们既不能通过理性去把握,也不能直抒胸臆,只能借助于有形具像的客观事物来暗示象征,因为世界就是一座象征的森林。扬炼就宣称:“我的诗是生活在我心中的变形。是我按照思维的程序、想象的逻辑重新安排的世界。那里,形象是我的思想在客观世界的对应物。它们的存在、运动和消失完全是由于我的主观调动的结果。”(《福建文学》1981.1)同时,在这座象征的森林里,客观与主观之间、客观事物与主官感受之间是可以互相感应的。而且视觉、听觉、嗅觉、触觉间可以通感。于是,象征主义注重诗歌音乐的流动性和雕塑的凝固性。 朦胧诗看来具备了象征主义上述基本特征。但是,朦胧诗在本质上还不同于象征主义。朦胧诗在思想认识方面还只是“朦胧”而已,并没有因为绝望而走向神秘和不可知论,朦胧诗虽然“费解”,最终却还是可以“解”的。朦胧诗注重诗人的主体意识,但并未堕入唯心主义。他们始终自觉地坚持:在主体意识之上还有时代意识和人民意识,并且,主体意识越鲜明,便越能表现历史和现实生活的真实,越能为祖国和人民立言。主体最终仍然从属于或服从于客体。主客体的这种依从关系使朦胧诗作者不可能认为“世界就是一个象征的森林”,他们至多只是运用了一些象征、暗示、通感手法而已。因此朦胧诗虽然拓宽了诗歌的表现领域,丰富了诗歌的技巧和表现手法,强化了诗歌的暗示意味和思辨精神,在诗歌艺术形态的转变与变形中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但是,这一步仍然是依傍着传统的,并且也不够大胆,不够彻底,不够理直气壮。 1983年后出现的以扬炼为代表的“现代东方诗”仍然循着朦胧诗所开创的道路,进一步实现诗歌艺术形态的转换与变革。1985年后诗坛在一片“打倒北岛”的呼声中,一时诗潮滚滚,诸如“非非诗派”、“咖啡夜诗派”、“大浪漫诗派”、“超感觉诗”、“阐释主义”、“病房意识诗派”、“天体星光派”、“超低空飞行派”、“撒娇派”等等,这便是所谓“后朦胧”诗派。这些更年青的诗人试图对传统的诗歌艺术形态进行最彻底的颠覆与革命。他们宣告:总是试图说点社会的什么和向社会说点什么的沉郁的北岛们已经“过时”了。“别了,舒婷北岛。我们不仅想告别你们的诗意识,而且想告别你们的诗形式。”他们自称“变成了一头野家伙”,嘲笑时代调侃别人也戏弄自己,一路打碎无数偶像地茫然行走,把嘻皮笑脸变形变态的颓丧行为抛向诗界。他们扔掉了因异化而生的朦胧的忧郁,也抽尽了因参与感而生的诗情的焦灼,决意不去写“无病呻吟”的作品。他们要减轻传统诗人们的灵魂负荷,认为在诗里那些“深层的东西,无论从个体性出发,或有意识地从普遍性出发,都是无法达到的。在今天的社会里,那种认为能够获得某种深层的普遍或绝对认识的幻觉应当被抛弃。”(裘小龙、杨小滨《诗歌中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朦胧诗在他们看来已经不再朦胧,它在完成了从传统诗向现代诗的过渡后,便“明白”得可以告别诗坛了。我们不妨比较一下两首均写墙壁的诗。一首是梁小斌的《雪白的墙》,其中有这样两节:
音乐的铿锵节奏同江北大汉的粗壮形象融为一体,并且赋予了这一形象一种动态美。 朦胧诗的这种朦胧显然是受到西方现代派诗歌的影响,其中尤其是受象征主义诗歌的影响。象征主义是19世纪70年代兴起于法国,是20世纪影响最大的西方现代派诗歌流派。象征主义对社会现实强烈不满,即反对自然主义机械地生物性地描摹现实,也不满意印象主义所认为的:感觉便是最高的真实。象征主义者排斥过去的教条、规范、甚至传统。他们认为,客观世界是虚妄的,是不可知的,只有主观世界才是真实的,客观万物不过是主观精神的种种暗示和象征。心灵才是最高的真实。而要表现心灵这一最高的真实,我们既不能通过理性去把握,也不能直抒胸臆,只能借助于有形具像的客观事物来暗示象征,因为世界就是一座象征的森林。扬炼就宣称:“我的诗是生活在我心中的变形。是我按照思维的程序、想象的逻辑重新安排的世界。那里,形象是我的思想在客观世界的对应物。它们的存在、运动和消失完全是由于我的主观调动的结果。”(《福建文学》1981.1)同时,在这座象征的森林里,客观与主观之间、客观事物与主官感受之间是可以互相感应的。而且视觉、听觉、嗅觉、触觉间可以通感。于是,象征主义注重诗歌音乐的流动性和雕塑的凝固性。 朦胧诗看来具备了象征主义上述基本特征。但是,朦胧诗在本质上还不同于象征主义。朦胧诗在思想认识方面还只是“朦胧”而已,并没有因为绝望而走向神秘和不可知论,朦胧诗虽然“费解”,最终却还是可以“解”的。朦胧诗注重诗人的主体意识,但并未堕入唯心主义。他们始终自觉地坚持:在主体意识之上还有时代意识和人民意识,并且,主体意识越鲜明,便越能表现历史和现实生活的真实,越能为祖国和人民立言。主体最终仍然从属于或服从于客体。主客体的这种依从关系使朦胧诗作者不可能认为“世界就是一个象征的森林”,他们至多只是运用了一些象征、暗示、通感手法而已。因此朦胧诗虽然拓宽了诗歌的表现领域,丰富了诗歌的技巧和表现手法,强化了诗歌的暗示意味和思辨精神,在诗歌艺术形态的转变与变形中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但是,这一步仍然是依傍着传统的,并且也不够大胆,不够彻底,不够理直气壮。 1983年后出现的以扬炼为代表的“现代东方诗”仍然循着朦胧诗所开创的道路,进一步实现诗歌艺术形态的转换与变革。1985年后诗坛在一片“打倒北岛”的呼声中,一时诗潮滚滚,诸如“非非诗派”、“咖啡夜诗派”、“大浪漫诗派”、“超感觉诗”、“阐释主义”、“病房意识诗派”、“天体星光派”、“超低空飞行派”、“撒娇派”等等,这便是所谓“后朦胧”诗派。这些更年青的诗人试图对传统的诗歌艺术形态进行最彻底的颠覆与革命。他们宣告:总是试图说点社会的什么和向社会说点什么的沉郁的北岛们已经“过时”了。“别了,舒婷北岛。我们不仅想告别你们的诗意识,而且想告别你们的诗形式。”他们自称“变成了一头野家伙”,嘲笑时代调侃别人也戏弄自己,一路打碎无数偶像地茫然行走,把嘻皮笑脸变形变态的颓丧行为抛向诗界。他们扔掉了因异化而生的朦胧的忧郁,也抽尽了因参与感而生的诗情的焦灼,决意不去写“无病呻吟”的作品。他们要减轻传统诗人们的灵魂负荷,认为在诗里那些“深层的东西,无论从个体性出发,或有意识地从普遍性出发,都是无法达到的。在今天的社会里,那种认为能够获得某种深层的普遍或绝对认识的幻觉应当被抛弃。”(裘小龙、杨小滨《诗歌中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朦胧诗在他们看来已经不再朦胧,它在完成了从传统诗向现代诗的过渡后,便“明白”得可以告别诗坛了。我们不妨比较一下两首均写墙壁的诗。一首是梁小斌的《雪白的墙》,其中有这样两节: